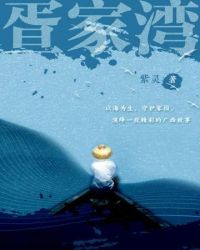七妹走了,初一做了鲨鱼妹家的上门女婿。这样一来,他们就不算外乡人了,有了这层保护,他们也会过得安稳些。鲨鱼妹的父亲对他很满意,她们家老奶奶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鲨鱼妹的父亲和苏喜妹商量,先不给他们举办婚礼,免得生出事来;在他们家住下,看看局势再说。苏喜妹同意了。
鲨鱼妹的父亲诚心诚意邀请苏喜妹以后就长期住在他家,自家人好互相照顾。
苏喜妹客客气气拒绝了,说:“感谢叔叔。初一已经是大人了,跟着叔叔干活最好不过,我很放心。不过我还有一个妹子我想她了,我去她家走走吧。”
“你说的是胡阿甲(黄安)家吗?我们很熟。你想去就去,想回就回,总之这里是你家。”
苏喜妹拉拉老奶奶的手,摸摸鲨鱼妹的头,背上包裹出了门。初一低下头送她走,像一条小尾巴。走一截路又一截路、过一条街又一条街,舍不得分开。
苏喜妹停在路边看他:“快回去吧,干活要紧。”
初一可怜巴巴地说:“你不要我了吗?”
“真是孩子话!你如今是大人了,说这些干什么?”
异国的街头冷冷清清,姐弟俩在路口分手。
苏喜妹的脚一踏进阮凤凰的店,屋子里的人都停下筷子来看她。苏喜妹大大方方找个空地儿坐下,招手笑道:“老板,来碗面!”
胡阿甲赶紧过来招呼:“大姐来了。”并主动说,“她在厨房里忙呢!”
苏喜妹说:“我知道她忙。”向胡阿甲看了一眼,意思是“别的事我也知道”。胡阿甲讪讪地笑了,跑进厨房把阮凤凰替换了出来。
阮凤凰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走到苏喜妹身边轻轻放下。她把苏喜妹的包裹解下来抱在怀里,乖乖地坐在一旁,有些想掉眼泪的样子。
苏喜妹说:“看你这个样子,我怎么吃面?你这老板娘也真是太奇怪了!”
阮凤凰没有心情和她开玩笑,白了她一眼,跺跺脚,把包裹拿上了楼。她把包裹放在床上,人趴在包裹上哭。
苏喜妹吃完面也上了楼,说:“我来投奔你,你却哭起来,是不是想让我走?”
阮凤凰心如刀割,说:“大姐,我是心里难过呀!”
苏喜妹沉默一会儿,坐在床边,把坏人强逼、草棚被烧、七妹跳海的过程简单诉说了一遍。阮凤凰闭上眼睛倾听,眼泪流到床单上,抽搐着问:“人被海浪卷走,包裹还在吗?”
“在。”苏喜妹说,“我听老人说,跳海的会变成鲛鱼,上身是人、下身是鱼,在水里活命。她还记得岸上的事情,只是不能被人看见、更不能上岸,不然会死的,所以七妹定然还活着的。”
阮凤凰叹了口气说:“大姐,那我们把七妹的包裹埋好,立个小坟。姐妹一场,留个念想。”
苏喜妹说:“好!”
阮凤凰说:“谢谢大姐。”
她俩叫上初一,初一又带上鲨鱼妹,四人抬起七妹的包裹,在众人瞩目之下来到海边。大家在望乡台旁边挖了一个坑,把包裹埋了进去。填土时垒起一个小小坟头,但并不明显,也许路过的人并不会留意这个小土包。他们磕完头,起身眺望大海,似乎看见,在那海天交接的纯净处,有一条鲛鱼正在自由自在地游泳。她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鱼,使劲立起身,正在向他们投以无限深情的凝视。
在她俩心中,七妹永远是那个在船上欢笑的京族女孩儿。
苏喜妹在街上租了一幢小楼,一个人住。说是小楼,其实就是两层的小木屋,样式有点像吊脚楼,有个小阳台。这幢小楼是胡阿甲亲戚家的空屋,租下来没花多少钱。苏喜妹和阮凤凰现在成了邻居,站在阳台上就可以望见饼店门面,走两步就到。
苏喜妹依然靠医治人过日子,但她暂时不去山上采草药了。在山上靠的是茶与药两个字,如今靠的是另外两个字:香与水。凡是有人来,就给他一碗水喝,或温、或凉、或烫,因人而定。这水其实是她熬好的去暑解乏的汤药。而苏喜妹定下的规矩是,来的人须自己带一把香,且必须是上好的檀香、沉香;若有安息香,更好。苏喜妹背医书说:“此香辟恶,安息诸邪,故名。状如松脂,新者柔韧,烧之通神。可镇小儿惊邪、男女之症。”用香安神这自古以来便是有了的。
高台教那个老翁打听到苏喜妹搬到了这里,便带一个小和尚前来看望,对她的不幸遭遇表示慰问。高台庙离这里有点远,需要骑马,老翁骑一匹大红马;抱着小和尚来的。老翁和苏喜妹交谈没多久,很客气地起身了,把小和尚留下来服侍并跟着苏喜妹学习药理,说:“三天回一次庙。”说完就翻身骑上大红马离去,动作轻快得很,不像是老人,倒像是年轻人。
从此后,苏喜妹每教小和尚认药,他管苏喜妹叫“药娘”。
久不久苏喜妹、小和尚、阮凤凰、胡阿甲、初一、鲨鱼妹,六个人就会聚在一起。
初一关心地问:“大姐,这段时间那个狗官有没有来找你的麻烦?”
“有你们在背后给我撑腰,他们不敢欺负我。”苏喜妹望着窗外的白云说话,“听老百姓说,他还是一个不错的官。这样看来,我们倒是坏人了?没有遂他心愿,罪该万死。”
胡阿甲解释道:“不说他好话的人都会坐牢,因此无论你问谁都会说他是好官,其实……”
“其实是个畜牲!”鲨鱼妹恨恨地说,“我娘就是他抢走的。抢到西贡,放回来没多久,就死了。我要找他拼命,你去不去?”最后一句她问的是初一。
到这时,大家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鲨鱼妹的娘亲。
初一这时已经是个很沉稳的小伙子了,很认真地回答妻子的话:“你的娘就是我的娘。你去拼命,我走前面。”他对苏喜妹说,“大姐,快想个办法吧!中国人到异国他乡,我只听说不能干坏事,没听说不能报仇。”
苏喜妹回道:“你错了。这不是报仇的事,是为民除害!”
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
阮凤凰靠在胡阿甲的身上说:“阿甲,我好害怕!听说狗官连孕妇都要抢。如今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忍心让我们娘俩去死吗?”
胡阿甲一下子站了起来:“我保护你们。”他做了一个劈砍的动作,“我去把狗官的狗头劈了。”他经常剁猪头、卖猪肉,这个动作用得很熟,此时用在假想的狗官身上,非常适合。他这个动作把大家逗乐了。
小和尚一直在旁侍候大家,这时轻轻地问胡阿甲:“阿甲大哥,拳术你会吗?”
胡阿甲愣住了:“不会。杀猪我会,可舞刀弄枪是另一门手艺,老子还没学呢!”
小和尚问郑初一:“初一先生,拳术你会吗?”
郑初一挠了挠后脑勺:“我不会。”拍拍脑门说,“哎呀,我忘了,竹竿仔一直在学拳,他娘说的。”
小和尚说:“我认识竹竿仔大哥。”看着大家问道,“你们知道竹竿仔大哥是向谁学拳的吗?”然后又看着苏喜妹说,“药娘知道。”
苏喜妹点点头:“我知道了。竹竿仔是在庙里学的拳,想不到老前人精通拳术!”她眼前顿时闪过一个身影:一位老翁翻身骑上大红马,动作轻快。
“一切皆缘定,万事莫强求。”小和尚宣一声佛号,下楼打坐去了。
楼上五人商量好了,找个时间,郑初一和胡阿甲去庙里学拳。待学会拳术,再想下一步。
苏喜妹说:“小师父会带你们去。到了庙里,他不必再回这里,我懂的他也学得差不多了。你们把他当师兄看,人家年纪虽小本领却强。”
初一说:“那竹竿仔也是我的师兄了?”
“就是!”
这天,他们在楼上聊得开心。因为苏喜妹这里不让喝酒,就去阮凤凰店里喝。胡阿甲是老板,平时不喝酒的,这天也喝了。他举起大碗和初一碰,和鲨鱼妹碰;又看一眼身边已怀孕的老板娘,喜悦的心情就像是在天上。
四月初三,这是他们定下上山学艺的日子。初一起早赶到苏喜妹的小楼下,胡阿甲已经在那里等他了。小和尚解下新买的小黑马走到街边,一步跨上去,回头笑问:“你们骑什么?”
胡阿甲咧嘴笑道:“我家有一头骡子,但不是很好骑。平时都是驮柴驮米,力气倒不小。”说到这里,阮凤凰已经把骡子牵来,蹄声“得得”,骡脚掌踩在石板上,清脆的声音像是打铁。
胡阿甲翻身骑上骡子,朝郑初一挥手:“兄弟上来吧!”他以为郑初一没坐骑。初一向他摆摆手,指着前方说:“我的坐骑一会儿就有。走吧!”胡阿甲俯下身,向阮凤凰交代了一句话,阮凤凰听了满脸绯红。胡阿甲又向阳台上的人挥手,大声许诺:“兄弟就交给我了,请大姐放心!”
他们三人,一人骑小黑马走在前面,一人骑骡子跟着,还有一人大步流星向前走。
阮凤凰走上小楼,和苏喜妹并肩眺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眼前的街市跟国内差别不大,房顶向南。太阳从东南方向照过来,瓦片闪闪发光。瓦房旁边,草棚、竹楼也连成一片。各色房屋前后,各种篱笆围绕,东一株香蕉、西一丛竹子,还有那一株又一株榕树拔地而起,树荫笼罩好几家人。在村庄下面,所有榕树的根盘结成网。房子中间的道路像是蜘蛛网,主道像一条巨大的刮痕。
严格说来,这里是村庄的过道,不能算是街市。但近年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也就有了市场的气息。如果遇到赶场天,这里人山人海,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都能遇见。阿拉伯王子和欧美白人在抢购一串安南珍珠,这样的场景都不算稀奇。
弯弯曲曲的街道像一条条河流,穿过小山包一样的房屋。街市连接田野,道路伸向远方。在乳白色的晨雾中,缓缓走来一头大象。大象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壮实的老汉,一个是苗条的姑娘。这两个人竟是鲨鱼妹和她父亲,谁也没想到他们给初一准备的坐骑竟然会是头大象。他们在大象上向迎面走来的三个人招手。骑着小黑马的小和尚停下来了,在牛背上合十行礼;骑骡子的大汉轻轻挥舞马鞭,让骡子绕着大象转——他这个举动不知是一种风俗礼仪,还是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以至于像头幼兽似的“撒欢”?
“大清早的,高兴什么劲!”小楼上有个人的脸更红了。
小楼上的两名女子看到,大象温顺地跪在路边,父女俩从象背上下来。那个虎彪彪的小伙子爬上象背,威风凛凛像个将军。
阮凤凰忍不住问:“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骑大象了?”
苏喜妹笑道:“骑大象不用学,人人都可以骑的。因为根本不是你骑它,而是它背你。”
她俩在小楼上望着,那父女俩在田野上望着,他们四人目送这三个男人,一人骑大象、一人骑骡子、一人骑黑马,往一片森林走去。
走到森林深处,还有一片雨林。在云雾缭绕中,三个男人驱动坐骑升上山岗。也不知道走了多久,这时小和尚手指前方:“到了!”
初一原以为前方应该是一座佛寺,没想到是一座教堂。他疑惑地看着小和尚,小和尚微微一笑,并不答话,只管带路前行。教堂前边有片空地,好些人穿着长袍在走动。小和尚招呼初一和胡阿甲跳下坐骑,把骡、象、马交给管事,带着她俩走进教堂,初一立刻大开眼界。
这座高台教的庙宇外形是教堂,里面却依次供奉天主教、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的尊神与经典。蟠龙大柱绕基督,莲花太极供真主,风格委实奇特。墙壁上又悬挂着斗大的汉字,写的是孔夫子的话。
老翁正在向一群儒生讲解《论语》,见来了客人,呵呵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位儒生对了一句:“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老翁击掌赞叹:“对得好,对得好!”
小和尚引着郑初一、胡阿甲,在一只天眼的注视下穿过讲堂,来到后院客寮区。这时天已黑尽,看样子该休息了。
胡阿甲嚷道:“竹竿仔呢?”
小和尚说:“你会见到他。”
“什么时候?”
“你想见他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客寮灯盏明亮,晚上老翁来看他们。他们说明来意,老翁颔首把他们留下。时间过得很快,又是一年五月初五日,下龙湾龙舟大赛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