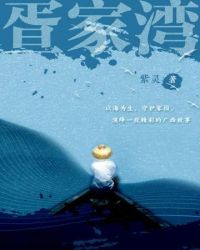一场秋雨过后,山上挂满溪水。这些溪水裹挟着山里的花草枝叶,一路刮着地面奔走,形成浑浊的泥汤,在石多土少的贫瘠大地上拐几个弯,汇到一起,流进大海。从高处望,风景依然很好,似乎上苍并不在乎下界的贫瘠,匆匆忙忙就赋予了这方土地美丽的外表,真不知这是对穷苦人的安慰,还是对穷苦人的戏弄。他们总是怀着饥饿的怒火醒来,张望远近的河川,久久不能理解眼前这美景有何意义、他们身处其中有何价值。
在浪潮的喧闹中,一轮红日从海面脱逃般升起。瞬间过后,它的力量显露了出来。天空布满云霞,光影倒射海面,与汹涌的浪潮合为一处,形成一口彩色的鼎锅。在蓬勃上升的氤氲中,太阳恰似一只巨眼,用严厉的目光审视地面的一切。
疍家人的船队在螺号声中又出海了。船只大小不一、桅杆高低不平,就这样三晃两晃地离开了港口。如果不是有敞着衣、拿着网的汉子站在船头注视前方,根本没人分得清这是渔船还是难民船。
半山腰的车辕树林边缘有块苍青色的岩石,一位妇人抱着孩子在这里眺望出海的船队。沿着山坡,分布着一些黄色斑点;围绕这些斑点的,是一道道呈辐射状的裂口——这是疍家人的草棚与土地。没出海的人与出海的人同步劳作,他们在这些斑点与裂口上兜转,一直要转到天黑,等船队回来,才会暂停劳作。
在一间大一点的草棚前面的空地上,一排排竹凳支起,上面摆着一个个大小等同的笸箩,每个笸箩里都盛着药材。药材并不算多,要么红红的一点,要么褐色的一撮,要么暗绿的一团,装在笸箩里,一名年少的僧人正在翻捡。
苏喜妹不知为何,一早起来就觉得心神不宁。净空在她的指点下分辩药材,眼见苏喜妹神情恍惚,就为她端来一碗水。苏喜妹接过这碗水,眼睛定定地看。碗里的水在晃,她的眼睛里却默默滑下两行泪。
一辆吉普车从防城县城出发,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小公路,向西面的山峰开去。车上有两个当兵的,一个开车,另一个挨着两个人端坐。他盯得很紧,有点像押送犯人;眼神却是和气的,好像有点崇拜被他押送的人。
这是一名书生模样的人,他左胳膊上套着一个袖标,上面的红色十字非常醒目。袖标的底色原本是白色,这时已变成一面小小的彩旗,估计是匍匐前进时在地面擦出的痕迹。当然,上面也免不了有些许血迹。书生对此似乎已习以为常,正以一种超然的目光欣赏着车窗外跳跃的风景。随着车身的晃动,他身边的女子不时叱叫一声,把他搂紧。这种叫声压抑而尖锐,引起大兵们发出浑浊的怪笑。
“浩然,我们什么时候到?”
“命令上说,下午三点必须到达。”
“营地是在山里吗?”
“是在山里。梵梵,前面就是十万大山。”
眼前群山起伏,一条带子般的道路把吉普车从田野“抛”进山林。他们经过一些村庄,有汉族、壮族、瑶族、京族等百姓居住。人们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出行、劳作,都很强调自己的身份,以免在交往中引起误会。逐水而居的是壮族人,会唱山歌;面朝黄土的是土著,会划龙船;在山里打猎的是瑶族人,身上似乎有着来自远古的力量,让他们身处恶劣环境也能生存下来——这点倒与在海上生活的疍家人有几分相似。
军营隐藏在一个瑶寨里。吉普车在树林里钻进钻出,车顶上落满了黄的叶、红的花,还有雪白的花粉。一根细枝拂过车门,把梵梵惊醒了。不一会儿,军营就到了。站在门口张望的是一些瑶民、土著,他们牵着牛、扛着锄,他们的农田就在军营前。
吉普车擦着水牛弯弯的长角开进了大门。还没停稳,一些勤务兵就拥上来说:“军医快点快点,前线撤下来的伤员已经有两车了!”林浩然的心一紧,立刻抱起工具箱一路小跑来到医疗点,开始紧张的抢救工作。
“你和勤务兵把伤员分类,用笔记录好。”林浩然吩咐道。
梵梵说:“好!拿针我不如你,拿起笔来我可比你强。忘了吗,咱们在学堂上学,先生夸我的文章比你写得好!”
“那你记清楚点,先生要检查的!”
“你占我便宜!”
他们在谈笑中进入角色,抢救工作一直进行到夜里。
吃饭时,林浩然问:“记录得怎么样?有没有特别的情况?”
“都记录了,全是外伤。好可怕呀!”
“别怕,战争就是这样。”
梵梵又问:“咱们的军队究竟和谁打?好像有法国人、英国人,还有日本人。”
林浩然:“混战呗,都是为了抢地盘。你把国军当‘咱们的军队’吗?难道忘了学堂是谁炸的、先生是怎样死的?”
“就你强硬!还不是被人家抓来当军医。”
“我们只是在救人,我们并不是他们的人。”林浩然看着梵梵,希望她明白这件事。但他从对方茫然的眼神中得不到任何回应,也只好作罢。
饭后,林浩然逐一查看他负责的这一部分伤员。这些缺胳膊少腿脚、歪脖子瞎眼睛的士兵,此时正在被巨大的疼痛所折磨,林浩然的到来为他们带来了希望与安慰。他们纷纷向他打招呼:“林医生来了!”“多谢林医生!”有的躺在床上说不出话,眨眨眼睛就当点头问好。
其实林浩然这时也极度疲倦了,真想倒下来就睡,但他不忍心抛下伤员不管。他知道陪同是最好的治疗,因此就索性坐在伤员中间,跟那几个还能开口说话的伤员聊天。
“兄弟,你是哪里人?”
“柳州。”“桂林。”“防城。”一个人问话,三个人抢着答。
“你是怎么受伤的?”梵梵坐在林浩然身边,双手托腮问其中一个。那人有些发窘:“被流弹打伤了。”
“子弹可不长眼。”
“我们班长可以不吃不喝,杀一天不停、杀两天不累。那天,胖大海、梭梭、鸭青、我,我们四个人跟班长到山里侦察,走到一座桌子山上,下了一场毛毛雨,我们就在一棵断头树下休息。胖大海使劲喝水,梭梭和鸭青比赛吃饼干,我没敢放开吃喝,随手摘了一个野生猕猴桃来吃。只有班长什么也没吃,双手叉腰站立、两目正视前方。
“我们班长姓冷,百色人,大家叫他冷班长。其实他一点也不冷,只是有心计罢了。他不吃不喝,说是万一在战场上迷了路,可以靠余下的口粮多活一天。十万大山山连山,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缝,人如果陷进去,喊破嗓子无人知晓。
“当时冷班长站在树底下,我们四人坐在石头上。按理说冷班长最危险,但怪事来了,忽然一颗子弹打过来,穿过他的裤裆,直接把胖大海的大头给崩了,脑花落在饼干上。
“梭梭和鸭青吓尿了,趴在地上装死。我躲到树背后,看见冷班长蹲下来,摘掉胖大海的枪,一只手拿一杆枪,端起双枪就冲上去。我不好意思再躲,扯起地上的两个狗熊,我们三个人也冲上去打助攻。最后鸭青被刺刀捅死,梭梭丢了一只耳朵,我断了这只手。”
讲到这里,他极力想把受伤的手举起来给林浩然看。林浩然轻轻按住他,微笑着说话:“我知道你很勇敢。”
“好恐怖呀。”梵梵说。
林浩然似乎不想评价什么,示意梵梵如果累了,可以靠着他睡。
梵梵悄悄问浩然:“能找间床吗?”
“床都让给伤员了。”
“那我睡车上行吗?”
“那两个兵不是什么好人,你怎么能睡车上?”
“跟着你真没意思。”这两个人沉默了,坐得虽然近,感觉却很远。
山里传来野兽的呼啸,远近连声。瑶寨有人敲鼓,像是在举行什么仪式。尖锐的竹笛、婉转的箫管、沙沙的铃铛、低回的吟唱,在鼓点声中合成一种幽暗的音乐,似在与野兽的啸声抗衡、但又像是在呼应。啸声—鼓声、啸声—鼓声,反反复复较量,到半夜才渐渐平息。
林浩然陪伴伤兵们坐到半夜,感觉自己也熬不住了。在呻吟声中、桐油灯下,他陪着这些伤兵借聊天来减轻他们身上的痛苦。这种强迫性聊天的声音被压得很低,听起来像是开水在闷罐里翻腾。
他身上靠着一个人,故无法起身活动筋骨,只能僵硬地坐在小马扎上。最多也就是把腿伸出去-缩回来、伸出去-缩回来,左脚伸了右脚伸、右脚又把左脚踩,如此而已。
在这困倦的时分,他多么希望,与自己靠在一起的,是他心中想念的那个人。那个人可以给他好精神。想到她的傻与真,他总是会沉浸在心底的微笑中。
天快亮时,就听到野鸡叫。似乎还有野猪在叫。山里面的声音又响起来,比先前更响亮,大有入侵之意。人类的村寨就在它们盘踞的山峰下,它们用这种不妥协的叫声宣告自己才是这片大山的统治者。伤兵们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对战斗习以为常;此时听到鸟兽叫唤,没人感到害怕,反倒觉得有意思。
“什么鬼声音?若是野猪,该是多大啊!”
“你这个桂林仔,要不现在也喊两声?”
“不到桂林不会唱,歌声飞到漓江上。”
“你还行。不过和咱们防城的疍家人比起来,还差一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