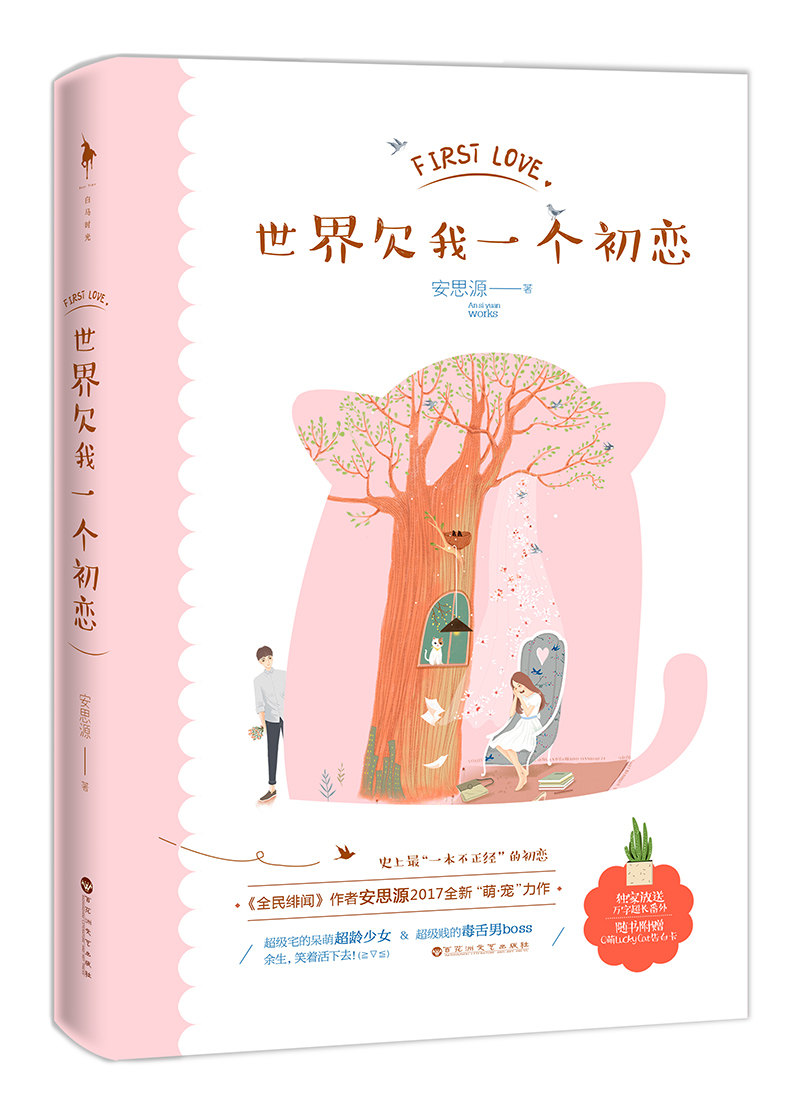[第1章第一卷]
第3节第2节,我的家世
事情终究如何?还得从头说起。
我的家乡座落在水阳江畔。爷爷和父亲都是农民。若是往上到我曾公,他是当地有名望的教书先生。再往上有中过举人或进士的。祖先孙奏诗曰:将发姑溪路,维舟古院旁。钟声惊泊舰,帆影动危樯。两岸荒村寂,三更画角长。离家数里外,客梦已他乡。他曾做过县令、知府,写过很多诗词。当时曾出版过《纪游草》、《二怀堂稿》等诗集,至今民间难以寻觅,只有在家谱上才能看到了。
我父母亲都不认识字。我出生后,相继三个弟弟也出世。父母苦了大半辈子,家庭条件再苦,一定要供我们上学。父母亲说,认识几个字总比他们不认字要强。
我们县城不大,位置偏僻,交通闭塞。外地来的生意人到我们县城就是到了尽头。西南北三面都在安徽的包围之中。且三个湖泊——固城湖、石臼湖、丹阳湖把我们这个县城围成一个孤立的岛。解放前,每每大水季节,皖南山区的洪水倾泻到湖泊中,只有一条通往水阳江的官溪河泄洪。承受不了洪水的压力就会破圩。圩区的大小几十多个圩很少有幸免过。有的圩甚至连续破过几次,圩内的百姓遭灾遭难,到处逃荒要饭。我所在的圩叫南宕圩,旧时称为豆渣圩,那土一遇水就如豆渣一样化成稀泥。遇到大水年代,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一眨眼功夫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为此每年圩内的老百姓都要加高圩堤,吃尽了千辛万苦。
九岁时我就开始挑土筑圩了,如今落下了一直腰疼没有好的毛病。
我的家离县城向西七华里,一个叫老圩埂的地方。村庄上的房子沿着旧圩堤而建,形成一条不规则的曲线,银灰色的茅草房参差不齐,偶然有一两户青砖小瓦房屋也破落不堪。
每年到了6、7月份的梅雨季节,连绵不断的阴雨,屋漏就成了老百姓挥之不去的梦魇。那如酱油一般的屋落水,滴嗒嘀嗒地从屋顶向下漏,家里的大小盆子都得用上。母亲常常支使我,把铁皮簸箕敲得“铛铛”响,据说可以惊动老天爷大发慈悲,停止下雨。
如果天刚放晴,最难走的就是路,那黑土非常有黏性,泥土沾在胶鞋不肯掉下来,只能随着步子一起到达目前地。我小时候去上学,遇上下雨天就赤脚,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带上一双布鞋到学校后洗洗穿上。
我住在村庄中间,靠近一个几百年前破圩形成的大潭边。上中学后,要到镇上一个叫张家渡的地方读书,那里有一所几个乡联办的中学。每天清晨起来沿着圩堤走这四、五华里的土路上学,尤其靠近大队部有一段路是竹园,两边的竹子遮住中间的路,常年积水。清晨去学校路过那里,阴森森的毛骨悚然。因为害怕,我常常叫上同学一道去上学。
父亲和母亲结婚前,他们都有过一段婚姻。父亲有个女儿三岁就随她的母亲改嫁在本村。母亲一直没有生孩子,她受尽了婆婆的种种虐待,说了一句最屈辱她的话:就是用根棍子在石缝里捣捣,也能捣出个癞蛤蟆来。
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生活非常艰苦。父母亲结婚的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6月17日生下了我,这天恰好是阴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端午景开花的季节,父母为我取名端景。母亲生我时已经34岁了,父亲比母亲大一岁。他们中年得子,欢天喜地。最高兴的是母亲,她被以前的婆婆曾经骂过“一只不下蛋的母鸡”,今天却生出了孩子。
我是家中的老大。从我有记忆起,住着两间小茅屋,门向朝南。左边是一个池塘,右边隔开一个本家就是老圩埂的大路。母亲怀上第四个孩子时我已经有记忆了,那是在老三出生后的第二年,她挺着大肚子,每天还要去生产队劳动。本想不要这个孩子,可是到医院,医生告诉她孩子已经大了,无法做引产手术。母亲希望第四个是女孩,结果还是给我添了个弟弟。最大的我七岁,最小的一岁。四个孩子和父母亲同睡在一张不大的床上,可见父母把我们带大的辛苦。
命运决定我的一切,老大在父母的眼中要求最严格,给弟弟们做榜样。从小父母亲就要我做简单的家务,常常鞭策我的一句话是:等你们将来长大了,分家产时多给你一个凳子。
清晨起来,我要把弟弟们夜里拉的尿屎清理掉。先是从灶台里取来一些草木灰盖住,再扫干净倒在茅坑里。有时取草木灰的同时,母亲叮嘱我留一些干净的灰(没有烧过后的硬块炭),装进一个细长的布袋里,我不明白那是什么,照着母亲说的去做。后来发现母亲在洗那布袋上的血迹。心想,难道母亲哪里经常生病?但那布袋母亲从不叫我去洗。
我九岁那年,家中发生一件天大的事情,我的弟弟老三溺水身亡。正是春耕季节,父亲在田里插秧,母亲正在做晚饭,老三看着老四在门口玩。一会他跑来告诉母亲,说弟弟要爬到水里去了。母亲慌忙跑出门,看到老四已经趴在水边。母亲把最小的老四抱回家后,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能够告诉她老四在水边的老三,自己竟然掉进了水里,老三的离去,后来的老四便成了老三。
最先发现的是邻居水头,她老远看到我家水口上好像浮着个人,就在对岸的田里使劲喊我母亲。等母亲把老三抱上来,已经没有气息了。听到母亲的哭声,附近干活的人也纷纷跑来,拿来一口锅扣在地上,把弟弟面朝下放在锅上,压着肚子,使喝下去的水能吐出来。
我正带着大弟放学回家,按照大人的吩咐,去田里把父亲叫回家。大队赤脚医生也被叫来,做了人工呼吸,但再也没有使老三苏醒过来。
晚上,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我同父异母的姐姐也来了,姐姐比我大十岁,她也陪着母亲哭泣。有几个邻居过来安慰母亲,说这是老天的注定,该应他只有这阳寿。母亲哭着说,是她不好,抱回了老四,没有把老三也叫回家。
外面天黑得厉害,大风把草屋的边缘吹得呼呜呜直响,仿佛有鬼就在我家四周活动。我和弟弟吓得好几个晚上不敢出门。当晚,两个本家的大伯,把老三装在一个小棺材内,安葬在误事谭埂背的坟山上。
一次,我和母亲在门前的树下拨豆。突然传来“叮当叮当”的声响,那是一个有名的瞎子算命先生,敲打着手中的一块铜牌。据说他能算出一个人的未来人生。
母亲叫住算命先生坐下。报了我的生辰八字,给我算命冲冲喜。弟弟的死,对母亲打击很大。我从小多病,肚子异样的大,她怕我也有个意外。睡觉前母亲总要拍拍我的肚子,听那声响,她能分辨出我的肚子有没有发胀。
算命先生沉默了一刻,掐着手指,一会说:你孩子福大命好,长大后遇事总有贵人相助,18、30岁有两道关坎;两妻之命,前程锦绣。
“那关坎能解么?”母亲问瞎子。
“能,初一,十五烧些纸钱给九仙太即可化解。”
后来瞎子又说了些陪衬的话,老来福气好,寿元八十不生病。母亲付了钱,算命先生敲着他手里的铜牌又上了路。她从算命先生那里得到些安慰,我也不知道那算命先生的话是真是假,也不懂在意。
我长大后,我的肚子也没有特意的去医治,一直很好,那一定是母亲精心照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