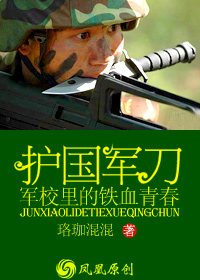[第3章那年,从脆弱和煎熬中开始]
第1节陆军机械化大学
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
我来到岔路口,伫立了好久。
一个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
我选择了这一条却说不出理由。
也许另一条小路一点也不差,
也埋在没有那脚印的落叶下。
那就留给别的人们以后去走吧,
属于我的这一条我要一直走到天涯。
将来从小路的尽头默默地回望,
想起曾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而我走的是人迹更少的那条路,
因为这样无名小路才将不会被遗忘!
——摘自《无名小路》
陆军机械化大学,全军首屈一指的综合性大学,培养过达官显贵、富商巨贾、军界精英,也出现过下岗工人、流浪歌手,甚至是杀人犯。但不管怎样,它造就了中国装甲突击集群的中坚力量,构建了960万平方公里神圣国土的钢铁城墙。毫不夸张地说,从北国冰城到南疆前哨,从东海之滨到西部戈壁,只要有坦克和装甲车的地方,就有陆大的学子。
那一年,乘着军绿色骊山大巴到达陆军机械化大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队部门口,一个PLMM哭的梨花带雨,旁边的男孩急得抓耳挠腮,两个头发理得沟壑纵横的屌丝,一个拿着扫把,一个提着簸箕,正窝在墙脚笑得十分淫荡!
这就是我对陆军机械化大学,这个号称“陆军之星升起的地方”的第一印象!
当然,很多时候,第一印象并不靠谱!这好比,当年的张柏芝,当年的钟欣桐,还有当年的酒井法子,那也是相当清纯的,不知悄然拨开了多少纯情少男的心扉,但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的,是吧?所以,那次的第一印象,无论是对那个地方,还是对那些人,也并不是很靠谱,起码部分不靠谱。
军校不交学费、住宿费、保险费、伙食费、教材费,更没有赞助费、择校费……
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这顺序没错吧?嘿嘿!没办法,某体育总局副局长要求的,我严格遵守,防止被批评!)
签到后,我见到了我的新兵班长,一个黑的窜种,严重可以怀疑人种、国籍的家伙,一身的疙瘩肉,面无表情往那一站,犹如一座铁塔,活生生从地里长出来的一般。
“自己来的?”黑铁塔依旧面无表情,严重怀疑是不是谁欠他200块钱忘记还了,丝毫看不出“军中之母”的慈祥。
“恩,自己来的!”
“爹妈没送送?”
“家里农活多,走不开!”其实,我只说了半句实话,家里农活是多,但最关键的是掏不起路费,家里穷。走的时候,我妈躲厨房里哭了,死活不敢出来,爸独自送我去的火车站,我让爸给妈带句话,说农民的儿子命硬着呢,不会出事的。
“那好,算你小子有种,跟我来吧!”这次,黑铁塔咧咧嘴,算是笑了,笑的真比哭都难看。
跟着黑铁塔进去,敲敲贴着“学员二队一区队三班”铭牌的那扇门,一个同样沟壑纵横的“龟头”探了出来,谄媚地笑着说:“班长,来新同学了?欢迎欢迎!”边说着边提过我手里的包,然后屁颠屁颠忙着去给黑铁塔倒水。
黑铁塔没鸟他,也没接“龟头”递过来的水杯,依旧面无调情地打量了我一番,然后丢过来一把钥匙,说:“3号柜子里的东西都是你的,把衣服换了,头发就不用理了,把家里带来的这些零八碎放储藏室去!”说着,转身又出去了。
黑铁塔一走,装模作样叠着被子的几位,如蒙大赦,立马就活泼了,纷纷跳下床围拢过来。
“兄弟伙,我是严实,四川人,出来跑码头,相互关照些哈!”说话的是刚才那个“龟头”。一个叫做严实,却一点也不严肃,更不实在的孩子,整个军校五年,他的生活完全可以用“悲催”二字来概括,但说实话,他很讲义气,可以为兄弟。
“你好,徐从余,浙江人。”我报以微笑,绝对八颗牙。
“Hi,王曦萌,上海人!半个老乡!喊我萌萌吧!”
“我是苏运江呀,福兰人!福北南边那个福兰哇,他们普通话不好,都听不懂的,还喊我酱鸭!”
“酱鸭,那是湖南,我就纳闷,面试你是怎么过的?用炸药包轰开的吧?”严实当时的这句抢白,无的放矢,却正中靶心。
酱鸭确实走了后门,却是堂堂正正,而且没花钱、没吃饭、没穿齐B小短裙,更没有潜规则,当然,估计也没人愿意潜规则酱鸭。话说面试时,酱鸭面红耳赤,哼哼唧唧老半天,面试官也没听出个所以然,自然就当场给亮了红牌。眼见儿子蒙难,说时迟,那时快,酱鸭他爹义无反顾冲入考场,从破塑料袋里掏出7张烈士证明,往桌上一摔,怒气冲冲,“不要我儿,赔我们家命来!”负责招生的干部犯了难,思索再三,还是要了酱鸭。
据酱鸭说,那些烈士证囊括了他们家四代几乎所有的男丁,从国内革命、抗日战争,直到边境反击作战,次次参战,仗仗死人,满门忠烈,换句话说,酱鸭家为这支伟大的军队输送了8名兵员,而酱鸭是唯一活着的。
各位看客,千万别以为这有多屌!你想啊,让你用你们家7条人命换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你干不干?如果有人很乐意交换的话,那好吧,我不得不承认,你跟我们大多数人不一样,你丫够狠,你丫就是一个畜生!
“罗生虎,喊虎子就行,陕西人!”一个高高大大、虎背熊腰的孩子朝我招招手,“赶紧收拾吧,班长说晚上要开班会!”
看着大家忙活去了,我才得空静下心来看了看。宿舍比高中那会大些,四张双层床分两边靠墙摆放,正对门靠墙放着一套八格的组合柜,屋子正中四张办公桌拼在一起,组合柜旁边别扭地放着一张行军床,雪白的床单平地没有一点褶,军被已经有点发白,应该是班长的铺位。这就是我今后四年的家,简单到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干净到地上可以照出人影。我的铺位就在进门左手上铺,下铺是酱鸭的,和我们紧挨着的靠窗上铺是虎子、下铺是萌萌,严实住对面,那边还有两个铺位也已经摆着被子了,看来人早来了。
五年的喜怒哀乐,各种的悲欢离合即将上演,而那时的我们,却懵懂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