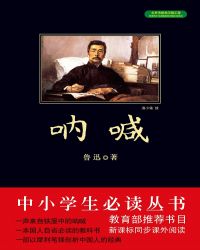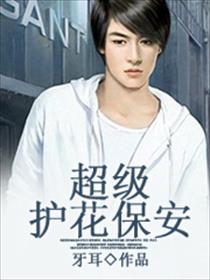事实证明,也许相思真的是魔障了。要不然怎么解释那须臾之间发生的怪事。
随着茶水进入到身体每一个细胞,除了一身通泰的感觉,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种很特别的、从未有过的感受。
就像,就像那茶水像是灼烧的烈酒一样,从心坎儿里生出热度来,然后要把整个相思子的枝干都烧尽了一样。
热,好热。
多像是在三伏暑天里啊!
相思禁不住颤抖了枝条,要去触碰夜风中的凉风。然而,晚风,晚风亦是热的!
怎么回事啊?难道,这茶有毒?
相思禁不住乱想,可是那个读书人也喝了同一个壶里倒出来的茶啊,要是有毒的话他一个凡人又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啊?稀奇,真是稀奇啊。
相思还在瞎想,亦不能动弹,她只觉得每一个枝条每一个叶片都沾着火星子,偏偏没有水来浇灭,她又一动也不动,只能活活的忍受这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灼烧感。
难受得紧,就像是当年遭雷劫时一样。
然而,这还只是外在,那个读书人看到的就更厉害了,几乎可以用惊悚来形容了。
茶水倒在树根的时候,读书人看见树枝没由来的颤了颤,他只当是有风轻过,或者是,他的树兄感激他的好茶,仅此而已,不甚在意。
可是,没有半盏茶的功夫,他还在摇头晃脑的背着《洛神赋》,却听见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那相思子的树枝开始扭动起来,像是娉婷的舞女,慢慢的,姿势变得诡异了,更像是一条隐藏在黑暗中的巨蛇。随之而来的,还有从枝叶里发出的类似于什么东西剥落的奇怪声音,像是有什么庞然大物要从树里钻出来一样。
书生抓起桌子上的茶杯,打算当作防卫的武器,想了一想,这是道观里的东西,还是放了下来。又抡起实沉的木凳,还是觉得不妥。最后只能把一卷竹简横在手上,战战兢兢的走向窗口,小心翼翼的朝外面道:“谁,谁在那里?”
当然不可能有人回答他。
他大着胆子,再次走了两小步,默念孔夫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才再敢出声:“是哪位道长么?”
深山之中,人迹罕至,往来的除了信客,便也只有这里面的道士了。
话刚刚喊出口,突然,从那相思子中爆出一个尖利的声音,像是一个女人绝望的哭泣。
“莫不是……莫不是真的有山精狐魅?”书生退后两步,跌坐在木凳上,半晌回不过神来,只是呆呆的听着那尖利而绝望的哭声,呜呜的风声也在他耳边回旋,到了最后大概是被那哭声感染了,竟似乎变成了附和的呜咽。
面对这种情况,正常的反应应该是快些逃出去,找个有人的安全地方。可书生像是被这别样的哭声吸引住了一样,不仅仅是他的脚已然走不动半分,更觉得,他的耳、他的心、他的整个身子,都被这可怖的哭声牵动蛊惑了,连思考的能力都没了。
突然,那相思子开始疯狂的落叶了,本来就很粗壮的藤蔓左摇右摆,因为缺水而有些干枯的叶片也随之一一落下,洒在脚下的泥土里。
而随着叶片的飘落,更为可怕的一幕出现了。像是有血从地底下渗出来一样,刚开始是树根脚下的泥土变红了,紧接着,那鲜艳的红色随着它的主根蔓延上去,像是染上了一层灼人的赤色。很快的速度,那么大一株相思子的每一寸都被这血色弥漫住了,简直像是一颗正在滴血的树。
书生看呆了,身体都僵硬得不敢动弹了,他确认,他看到了非人的东西。
那树终于停止了变化,只是整个树都被浓重的红色包裹,每一根枝条,每一个纹路,都是修罗场一样的压抑的红,又或者是,压抑的血色。
紧接着,书生看到了这辈子最难以忘怀的景象:如同滴血一般的树,隐隐有光华从它的根脉中透出来,然后,它的主根之中猛地爆出一道金光,整棵树都被炸裂了开来,无数的树皮藤蔓什么的如同被困太久而终于得到释放的小恶魔们,四处乱飞,打在窗棂上,打在墙壁上,拍在桌子上,还有拍在书生脸上的。
书生见状,急忙矮下身子,用手中的竹简来护住头部,躲过这一场无妄之灾。
等到树枝乱飞的声音小了下来时,他才敢冒出头去看,只见屋子里一片狼藉,而那株屹立在窗边不知多少年的古树,就这样没了,像是天雷劈了一样,连树根都没剩下,只有满地的残枝断叶,还有以前它攀附而生的种种痕迹。
书生目瞪口呆的看着眼前的一幕,思忖着,难道这古树是遭了雷劫了?可又不对啊,自己完全没听到任何的雷声啊!
他甩甩晕乎乎的头,只觉得刚刚的哭声还在脑海中游荡,又自顾自的想着,要不要改日去找道长要一个平安符?
而书生不知道的是,在这漆黑的天幕中,在那上头的云端,有两个人,一个白衣,一个玄袍,若是这样轻易现身,定会让人想到冥府的黑白无常了。
虽然,他们都长相俊美,绝不是那鬼差能比的。
却是狐狸白九,和魔君炽焰。
白九道:“你看清了没?刚刚到底怎么了。”
“虽然不快,但是老感觉眼前罩着一层雾,什么都看不见。”炽焰魔君回答。
“我就说这里雾气潮湿,要你选一个好地方吧,你非要停在这里,看吧,雾大得连个鬼影都看不见。”白九埋怨身边的人。
炽焰魔君平生最恨比自己弱的人说他的不是,当即反唇相讥:“你瞎嚷嚷什么?本君找的地方从来就不会有错。要不是你这死狐狸的拖累,本君可以直接以元神入物之术进到那书生的躯体里,哪里还来的那么多事?”说完了斗嘴的废话,他又道,“而且,那雾不是寻常的雾气。本君用灵力洗了眼睛的,就算是隔着高山也能看得清,可是,这一次却什么也看不见。很有蹊跷。”
元神入物之术只有特别厉害的大妖才能用,就比如这个虽然没什么战斗力但是平常法术还是很厉害的炽焰魔君。而像白九这样的小妖,便只能以元神入自己的本体,否则便会控制不住惹出祸端。所以,这样算来……白九的确有些拖累了。
然而,白九才不会在这个高傲自大的魔君面前承认这一点呢,他高昂起头来,一副“你再吹”的模样,一个白眼之后直接跳过了这个话题。他道:“我们刚刚算是及时出手了吧?”
魔君点点头。
他们立在云头,亲眼看着相思子的内部开始莫名其妙的燃烧起来,而那诡谲的哭声似有蛊惑之力一样,等他们真正反应过来时,那心火已经烧到了树枝上了,用肉眼都可以看见火星子和白烟了。
两个人连忙手忙脚乱的准备施雨灭火,却发现这个地方似乎另有蹊跷,这种高耗能的法术若说白九使不通畅也就罢了,可堂堂炽焰魔君竟也用不出来。两人只觉得这山间似乎有什么不知名的东西影响且阻碍了他们的法术。然而,当时情况危急,他们也来不及细细探究其中因果,只得以隔空取物之法将相思从那正在燃烧的红豆本体中带出来,再施法把烧得正起劲儿的红豆本体也以此法挪走,搬到了他处。这才敢松懈下来,斗几个嘴。
“奇怪奇怪,这里真的是太奇怪了,”白九感叹,“真不知道相思当年是怎么在这种地方还能修炼出妖灵的。”
“奇怪之处生奇怪之物,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性格变化莫测的炽焰魔君竟一本正经的说了句奇怪但很有哲理的话,让白九不得不再一次在心里吐槽这个魔的不正常。
冷静下来的两人这才想起了重点,白九问道:“这样是不是就算阻止了他们见面,也间接的破了这个情劫啦?”
魔君不知,只皱着眉头道:“希望吧。”但他隐隐晓得,天命不是那么容易改的,就算他们不在这里相遇,也会在另一个地方,用本该有的情绪再次重逢。这才是天命,不可违逆。
瞧着炽焰魔君皱起的眉头,白九也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便提议道:“要不我们现在就带着相思回去,只要她不再遇到那个书生,就不会有什么劳什子的要命的劫了。”
简单粗暴的做法,好像……有点儿道理。
魔君也赞同,便道:“也好,这里太过诡异了,回去也好。”
说罢,两人就准备带着相思离开。
突然,白九尖叫一声,结结巴巴的道:“相思人呢?”
原来两人以法术把相思从树中带出,就安放在道观的一处安静院落里的,可这再回头去看时,那空荡荡的院子里哪还有什么相思,连半个人影都没有了。虽说那只是元神吧,可这两个人怎么会看不见呢,难道这昏迷的元神也能自己跑了?或者,这里还有其他的人,暗中收走了相思的元神?
白九叫声不好,道:“这里怎么说也是道观,说不定真的有身怀异术的捉妖师,碰巧就把相思给收了?”
“别乱想,”炽焰魔君打断他,“你先用结界护好那相思子的树,我马上下去找。”说罢就要纵身跃下云头。
“唉,”白九不放心的拽住炽焰魔君的袖袍,“如果真的有这么厉害的捉妖师,你会不会也被捉了?”他有些心虚的道,“我可不想再花功夫去救你啊。”
“放心,本君可是一殿魔君呢,”他回头骄傲的笑,“这人间怕是还没有可以收得了本君的人。”
白九小声嘟囔:“那被老妖婆打得肉身陨灭的又是谁?”
正准备帅气的飞身下去的炽焰魔君,闻言脚下一个趔趄,差点儿没有直接从云头摔下去,心中悔恨:“这只死狐狸。”
而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斗嘴为乐的时候,一个面容陌生的绯衣少女站在院子里,迷茫的望着漆黑的夜空,道:“我是谁?这里,又是哪里?”
而此时,被怪力乱神之事吓得终于恢复了心神的书生,抱着他的那一册竹简,匆匆忙忙的从屋子里跑出来,正巧和这绯衣少女撞了个满怀,他急忙连声道歉。
而那少女,蹲下来捡起撞掉了的竹简,看了看,目光里透露着狡黠,轻启樱唇:“《洛神赋》?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你便是被游龙追赶而神色匆匆的惊鸿吗?” 笔夭司命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