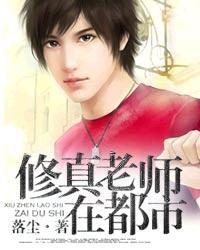恰逢花拂拿了玉佩来,太监用一只朱漆托盘托了进来,送到云深面前,一众目光便瞧过来,玉佩通身碧翠,彷如一汪寒潭水一般,雕的则是一幅龙翔九天,雕工不是那么精细,只是个粗粗的轮廓,唯一条龙尾雕的活灵活现的,甚是威武。云深泪珠噼里啪啦掉,边哭边念:“我昨天听人说我死去的娘是当今皇上的亲妹妹镜月公主,我就天真的想,那皇上岂不是我的舅舅了?我又多了个亲人呢。巴心巴肝的连夜雕了这块玉佩,手都磨出血来了,想着送给皇上舅舅,原是我想讹了,皇上怎么是我一个乡下野丫头高攀得起的?这块玉不要也罢。”
说着,抄起玉佩就要往地上掼去,宁千锋一把拦住,将玉佩握在手上,忙道:“丫头,这可使不得,你这上面雕的可是龙,摔了那可是大不敬之罪。”
云深哭声越发大了起来,“窑子都逛了,名声都坏了,再加一条大不敬之罪也没什么了。”
“谁说你逛窑子了?赶明儿朕就把那起子造谣的统统治罪,还你一个清白。太傅,你看看你这女儿,性子怎么就和当年的镜月一般模样?还不让人开口说话了?”
“横竖我是个没娘的。编派完我再编派我死去的娘,皇上陛下就请治我个不敬之罪,让我去见我可怜的娘去吧。”云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心里却握着分寸,皇上不晓得什么原因,似乎对她颇为忌惮,她不过使使小性子,他当不会治她的罪。况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蔽住皇帝的耳目,唯装憨卖傻。
外面站了阖府的人,都真真切切看见了云深二小姐和皇上这般闹,心里都绷着一根弦,真是乡下来的丫头,不晓得轻重,全靖国有谁敢这样在皇上面前闹?便是最得宠的闵皇后怕也不敢吧。万一惹怒了皇上,那可是死罪。说不定还连累阖府。
但,眼见得皇上非但不恼,还拉下脸来连哄带劝,真是叫一众人都惊掉了眼珠子。这位二小姐,得罪不得。
蓝老夫人同蓝暂终于看不下去,纷纷出言相劝,云深倏尔哭起了娘,倒令在场的两位汉子和一位老太太眼眶里都汪了圈泪,一个是失去了妹妹,一个是失去了妻子,另一个,大约是人老了不经哭了吧。皇上都含泪了,屋里伺候的摆阵仗的宫女太监们便也见机全汪了泪水噗嗒噗嗒掉。云深哭一阵,倒反过来劝他们:“皇上舅舅,爹爹,奶奶,你们怎么也哭了?对不起,是云深惹你们伤心了。你们快别哭了,不然我的罪过就大了。”
一场问责不知为何就演变成了一场思亲会,哭到最后倒是始作俑者置身事外了。大家抽抽搭搭住了哭泣,皇上犹拿着黄绢擦眼角,边问:“云深,怎么你的救命恩人和你的师兄不在?”
云深抽噎着答:“师兄就在外面的,至于那位恩人,神龙现首不现尾的,早上还在来着,后来就不知去了哪里。这会儿快晌午了,说不定一会儿会来蹭午饭的。”
外面的榕树一阵枝叶摇晃。云深的视线在榕树上掠过,撇了撇嘴。
蓝暂顺杆爬,“皇上,要不就留下来用膳?”
皇上摆摆手,道:“罢了,朕在这里用膳,外面站着的那几百号人该饿肚子了。我就不招你们烦了。云深,改天你爹病好了,让他带你去宫里玩。”
“对了,谢谢你这份礼物,舅舅很喜欢。”说着,竟将那枚碧翠的玉佩拴在了腰际。
云深破涕为笑:“真的吗?宫里的景致一定很美吧?舅妈们也很美吧?”
皇上:“……”
“起驾……”太监尖细的声音在空里旋转直上,阖府的人全部跪倒欢送,皇上已经走到銮舆边上,又回过头来,咬着牙道:“太傅,管管你女儿。”顿了一顿,“对了,朕好久没见老七了,是不是又病得下不了床了?太傅你哪天帮朕看看去。”
云深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浮着笑,“皇上舅舅,改天去宫里看您和舅妈们去。”
皇帝黑着脸,“嗯”了一声。舅妈们,这词用的。眸光又在人群里扫视一遍,在上官月明脸上略停留了片刻,笑道:“你师兄倒是生的好人才。改天去宫里的时候带上你师兄吧。”
这又是唱的哪出,真是叫人费解。云深却也只得顺从地答应着。
浩浩荡荡的仪仗来的威武去的雄壮,云深站在台阶之上却有些疑惑。最后那一句,是个什么意思?是真的托她的便宜爹去探望七皇子?抑或在提醒她便宜爹婚约之事?还是,在试探她昨晚有没有去云间小筑有没有见过七皇子?
前两者倒没什么所谓,唯第三种可能,说明了一件事,蓝府有皇上的眼线,且这眼线应该是能入得厅堂的人。
按说皇上在臣子家里安放眼线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她却不得不留心了。
蓝暂揩了揩额上就没断过的冷汗,无力地挥了挥手,“都散了吧,该干嘛干嘛去。”几百口子人齐齐给他行了个礼,都麻溜儿作鸟兽散。
孟氏贴到他身边,面露不悦,“老爷。”
蓝暂蓦地吼了一嗓子:“还不赶紧把你没干好的活干了去?真想让我夺了你的掌家位置吗?”没干好的活,无非是云深院子里的活。孟氏恨恨瞪了云深一眼,气势汹汹地走了。蓝暂无奈地瞧着她离去的背影,半晌,又回过头来瞧瞧仍立在台阶之上的云深,似想要说什么,嘴唇嚅了半天,却一个字也没说上来,摇摇头,一甩衣袖,走了。
云深看看人走的差不多了,道:“奶奶,这么多人闹了一上午,想必您也乏了,您先去歇会儿,我午后到您院子里看您去。”
“嗯,你回自己的院子吧。午后也不用去看我了。瞧瞧你的黑眼圈,戏演的再好,有这个,还不穿帮?回去好好补补觉吧。”
云深下意识地往眼睛上摸,哭肿的眼睛倒是摸的出来,黑眼圈却是摸不出来的,意识到老太太也不过是诈她,她气恼地一跺脚,撒娇术已经手到擒来运用的纯属:“奶奶!不理您了!”
她一蹦一蹦地跑下台阶,抓着上官月明的衣袖子离开,走出去老远,耳中依稀听见老太太在那里叹了一句什么。风微大,将话音吹散,她没听得清。
她问上官月明:“师兄,你听见老太太说的什么话了吗?”
上官月明摇摇头,“没听清。好像是说了镜月二字。”
云深默然地和他并肩而走,眉心微蹙,半晌,轻轻一叹:“我的娘亲,为什么我总觉得她像一团迷雾呢。好像有许多事发生在她身上呢。”
上官月明温声道:“那么久远的人了,即使有什么事,也早随着人的逝去而烟消云散了,你就别杞人忧天了。”
“但愿我只是杞人忧天吧。”
和宁苑的大门前云深没有再请她的师兄进去略坐片刻,她只是低眉温声道:“今天闹了这样一出,实在不宜再请师兄进去徒惹流言了,我可能会睡到明早,师兄,咱们明天见。”
上官月明很识趣地目送她进门、关门,还善解人意地对她道:“好好睡一觉,别想太多。”想来他也是看出了皇帝是为云深而来。
院子里的茉莉花开的正好,像一层细雪浮在翠绿的叶上,微风轻送,幽香无孔不入地蔓延开来,让置身其中的人觉得连衣袂发丝都是香的。从昨日住进来并没有来得及关注一眼这盛极一时的潋滟景致,况云深也不擅长赏花观景之事。以前在云雪山上没少荼毒她师父的桃花林,闲来无事,除了祸祸桃花林,便是睡觉。她在一株花树下坐了下来,揉了揉哭得有些疼的眼睛,脸枕在臂弯里,发起了呆。
诚然,今日的流泪多半是在表演,但又何尝没有一点真心在里面。她忽然觉得,她是在乎这个家的,在乎这个家里的人,在乎曾经受过的伤害,也在乎眼前得到的爱。也许,所谓替死去的蓝二小姐复仇,不过是她一直不敢直面自己的真心的借口罢了。她心底里,可能早就将这个仇,视作是自己的仇,将自己与蓝二小姐这个身份,合二为一了。
玄色身影落在她的眼前,修长漂亮的一双手变魔术似的在她眼前一晃,一个茉莉花编成的精巧花环便落在了她头上。
她眸光盯着他一动不动,声音说不出的倦怠:“你是谁?”
上官曦明一怔。他晓得她不是问他姓甚名谁,她是在问他名字背后的一些真相。
从云雪山到这里,不足十天的时间,太多的人和太多的事像冬月里北风卷集的鹅毛大雪一般一股脑都扑向她,没有一个是熟悉的,全是怀了各种心思的,纵然她是冰雪聪明胸有城府的,可也不过是个年仅十七岁的女孩子。怎么可能受得住。而这些人里,所有人在表面上都有一个身份供她去辨识,是好是坏,是亲是疏,她都能有个大致轮廓,唯有他,就是一个人,没有任何可供她辨识的东西。 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