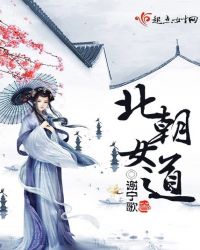朝中传来消息,梁武帝不仅赐了一万匹青布,还派了十几个东冶的锻工来寿阳做技术指导,算一算,最多半个月时间,人和货就能到。
侯景收到消息,不屑地哼了一声,“那个老儿真会糊弄人。”
楚朝露有些不解,王伟解释到:“因为御赐的每一匹青布上,都打上了皇家标记,所以一般不会用来做军服。而锻工虽然好,但咱们没有那么多铸造兵器的原料,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楚朝露眼珠一转:“青布的问题好解决,找个靠谱的裁缝铺子,将标记裁了或者遮掉便是,我记得寿阳最大的绣坊是谭家开的,我再去找谭家父女聊聊。至于铁矿么,虽然大的矿都是朝廷控制,但一些皇室子弟或者大家族,也会私下做控制一些小铁矿,估计临贺郡王那里肯定有。”
从议事厅出来去了后院,只见谭文君正坐在庭院的石桌上烹茶,一旁是凝神专注研究茶艺的谢宁华。
五月末,初夏时节,庭院里种的几棵高大合欢树开了一半的花,风一吹,粉色小羽毛一般的花瓣打着旋儿飘落,落在两位少女的头发上,衣襟上。
谢宁华抬眼看了合欢树,欣喜道:“方才还发愁这么一树好合欢花怎么采下来入茶,这一阵风可帮了大忙了!谭姐姐等等,我去拿了纱袋装合欢花!”
谭文君微笑着应了,楚朝露发觉,她不剑拔弩张的时候,很有几分小女儿的静美。
虽然知道自己的出现很煞风景,楚朝露依然走到了谭文君面前。谭文君淡淡抬眼看一眼她:“谢大人来了,坐。”那闲适自如的模样,仿佛她才是州牧府的主人。
楚朝露私下很佩服她的气度,也平心静气问道:“谭姑娘在府上住得还习惯?”谭文君点点头:“多谢侯将军款待。”
“谭姑娘,这次来找你,是有事情想和你商量。”楚朝露见她刀枪不入,干脆挑明了直说:“皇上御赐了一批青布,我们将军想改制成军服。寿阳最大的绣坊是谭家的,这单生意你们如果接了,你和谭老爷就可以先回去了。”
谭文君抬眼看楚朝露,黑白分明的眸子仿佛洞穿了一切:“朝廷有不成文的规定,御赐布匹不做军服,姑娘不会不知道吧?”
“既然不成文,我就当做是不知了。我只问姑娘一句,这笔单,是接还是不接?”
谭文君素白的手指沾了点水,在石桌上写了一个“反”字,然后指着问:“谢大人可否明示,侯将军真正的意图是否在此?”
真是个敏锐的女子,楚朝露心中一跳,却不正面回答问题:“谭姑娘应该明白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很佩服谭家的勇气,但也有一句话叫做胳膊拧不过大腿,姑娘和谭老爷何苦要和将军唱反调呢?”
谭文君支着下巴,看向很远的地方:“小时候读《左转》,我很不明白,世上为什么会有子路那么傻的人?身处叛乱之中,每一步都是危险,但他在意的却是冠樱断了,要把它重新结上。长大后,才明白,他回去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所以,死也要求保持体面和尊严。”
她顿了顿,带着微微的嘲讽之意:“谢大人是出身陈郡谢氏罢?你应该比我更明白,何谓风骨。”
谭文君说的那个典故,出自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路是卫国人,国家发生父子争国的动乱时,他正跟随孔子在外游历,如果是现代人,一定会庆幸自己逃过一劫,但子路听闻消息,却说“食其食者不避其难”,逆着众人逃亡之流返回城内。
回城后,他愤然当面斥责谋逆作乱的大夫孔悝,在双方的激烈交战过程中,子路负伤,帽子上的系带被砍断,他慷慨表示“君子死而冠不免”,从容系带,被砍成了肉泥。后世将“仲由缨”当作是不怕牺牲、慷慨赴死的代表。
楚朝露竟无言以对。作为现代人,她本能会权衡轻重,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像谭文君口中的子路赴死、魏晋风骨,虽然听起来很热血很美,如果是从前,也许自己还会被触动,但经历了这么多变故,身处这样的乱世,理智告诉她,那些都是童话故事。
如果想活下去,这样的冲动是要不得的。想起穿越回来后,单凭着一腔热血做了许多无意义的事,她理智告诉自己,只有小孩子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三观不同,看样子自己是不能说服谭家了。
谭文君见她不答,也不再说话,只是垂首静静喝着茶。
“谭姐姐,我找了好久,才寻了这么一枚合适的纱袋!”谢宁华兴匆匆跑过来,打破了沉重的静默。
“姐姐也回来了?”少女一歪头,露出无忧的笑容,楚朝露看了,只觉得真心羡慕。她笑道:“你们接着切磋茶艺,我出去一趟。”
楚朝露去了春雨楼。谭家作为淮南土生土长的世家,赵七娘一定很了解情况,看看能不能从其他地方找到攻破点?
她心里明白,侯景不是一个耐心很好的人,谭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忤逆他,他的耐心已经快到极限,如果再不就范,可能下场不会太好。
虽然认为谭家的做法有点傻,但她却不希望这样的人死去。大概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些理想主义者,她叹息着告诉自己,做不了理想主义者,至少不要做扼杀他们的人罢。
赵七娘一听谭家,也掩口笑了:“那可是块硬骨头。”
昔年谭家人丁兴旺,声势比崔家大得多,大约是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寿阳还是北魏的地盘,北魏和南梁连年交战,有一年,南梁的一个将军好不容易夺了寿阳回来,但不久就被北魏大军围城。
谭家一门上下,举全家之力支援南梁的将军,上至七十老翁,下至十岁小儿,全部投身军中。
后来寿阳陷落,谭家一门,死了个七七八八,单剩了现在的谭家老爷,谭阔一根独苗。
据说是因为他幼年时身子骨弱,母亲不忍心让他赴死,将他藏在了后院的枯井中。他在枯井里,整整躲了三天三夜,才爬了出去。
后来南梁收复失地,梁武帝给了谭家封赏,又加上谭阔性子坚韧,谭家也剩了不少祖产,几十年下来,一个家居然又重新振作了起来。
现在谭家虽然人丁不旺,但因了这份荣赏和傲骨,依然是淮南靠前的大家族。
赵七娘讲完谭家的事情,下了一句结论:“我劝姑娘还是算了吧。谭家这种硬货,惹不得,远着他就行。” 北朝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