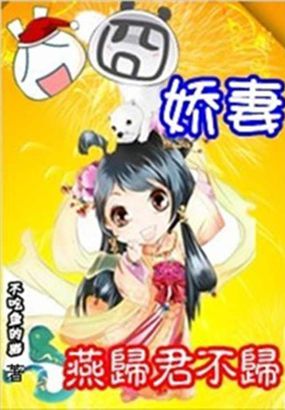惠子是在前一天的夜里服毒死的,次日中午才被佣人发现。按例打扫卧室的佣人敲了几次门,见无人回应,认为女主人还在睡觉,就转身离开。直到午饭时,惠子都没有出现,房门仍是紧闭,她们才预感到事情不妙,慢慢推门进入,发现她的尸体趴在梳妆台的大镜子前。惠子长发垂腰,穿着殷红纯黑的和服,犹如待嫁的女子,然而未曾梳妆的脸颊早已冰冷。佣人吓得瘫软在地上,许久才发出极惨烈的尖叫,把其他人都引过来。
若昕跟着王渝谦一同去了丧礼现场。她不清楚自己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她甚至不清楚她和惠子是否能算朋友。应该是吧,毕竟她在死前对自己推心置腹。
直到步入惠子家时,她才找到了答案。她对惠子有怜悯,有同情,更有勾起往事的伤怀。她在马蹄声中沉郁着双目,没有比此刻更怨恨她的父亲。她明白自己怨恨的并非单独一个人,只是谢欲自然地形成脑海中最具体而清晰的形象,让她可以有路可循,不会像无头苍蝇般发泄厌恶。那不是女儿对父亲的失望,而是女人对男人最义无反顾的憎恨。
宾客根本就不像是前来致哀,把此当作宴会,席地而坐,高谈阔论。丧饭也并不简朴:他们大口撕开烤秋刀鱼,灌下一盅盅清酒,又嫌酒味薄淡,想要几瓶烈酒助兴。
女人则聚成一团,叹息她是太爱和雄,忍受不了悲恸才会殉情。惠子的遗像挂在正中的墙上,散出同样的黯淡神色,在一派大肆喧笑中显得更为悲哀。她的父母双亲也坐渡轮从日本赶来,脸上承载着无限的失落。
到来的宾客向逝者行鞠躬礼后,再去安慰他们。樱田老先生鞠躬感谢,向每位宾客介绍站在他们身后的小姑娘——惠子的幼妹雪子。雪子今年才十五岁,长得和惠子有五六分像。若昕一眼就能认出她是惠子的妹妹。她笃定在一路上都哭得很惨,眼袋高高肿起,显得整个眼眶都往里凹陷。犹如花苞一般刚刚展现出的美丽被锁死在臃肿的眼神里。
她又落下一连串的眼泪。她母亲听见了哽咽声,转过身安慰道:“好了,你都哭了一夜,再哭下去会虚脱的。待会儿你也要陪我去招待客人,你已经长大了,该帮着家里做事。”
雪子咬着唇,用力点了点头,但是却控制不住自己,像是融化的雪人,只好随时用手绢捂住脸。
若昕走到院子里透气。庭院的角落有几株很大的樱花树。正逢三月初,盛春刚至,花色清丽。惠风走过,打落了漫天霞光。花雨击碎了小桥流水,泛起圈圈涟漪,有几朵落在桥边撑开的富士山纸伞面上。她走到樱花树下,伸手轻拈起因过盛而下垂的花枝。晚霞般的花影晕染在她的身上,将犹似山雪的双颊描上一道新妆。
她凝思良久,忽然发现日暮良太不知何时已站在了身侧。他显得有几分慌张,颔首道:“王太太,多谢您愿意来送惠子最后一程。”
他的状况看上去很不好,以尴尬的未婚夫身份,猝不及防地得知惠子的死,无疑令他备受煎熬。
若昕也鞠了躬:“日暮先生,我很同情樱田小姐的遭遇。请您节哀。”
“是我没福气,又害死了她。”
“我想并不是因为你,也许樱田小姐遇到了别的令她无法生存的苦衷。”
她犹豫再三,决定还是不告诉他真相的好。
良太却摇头道:“不是的,惠子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她三天前还约我去茶室,求我能否去和族中长辈提议暂时不要结婚。既然她那样想,我也不能强求。但是我绝不能让日暮家先悔婚,这行为太失礼了,极损家族的颜面。所以我告诉她,若是她不愿意,请她回去和樱田家商量,只要她那边希望解除婚约,那我一定会同意的。然后她就走了,可我实在没想到她竟会想不开。”
若昕叹道:“也许真的并不是你的错。”
她说完就打算返程。这地方太压抑,黑色的帘帐挂满了和氏木屋,连松柏,庭院,小桥都是小巧的。在她眼中仿佛是死人用的寿屋纸马,小巧玲珑。到处都是日本人,面染阴森死气,杵在当中,煞白着脸。身穿和服的贵太太更是竭尽所能地把面孔刷得像新墙一样白。
尚未走完石子小路,他们就看见河村彻迎面走来。
他很有礼貌地说:“神原太太,真是好久不见。我每次邀请胜平赴宴,您却都不来呢。”
胜平是王渝谦在日本留学时的名字。若昕也是不久前才知道:王渝谦东渡日本时,因家族关系同河村有了不浅的交情。
“我既没见过世面,又不会说话,若是做错了什么,白白为他得罪人,所以一直不敢出门,实在不好意思。”
河村哂笑道:“哪里会。神原太太愿意赴宴,那一定是我家的荣幸。下次请您一定要赏脸参加,届时必会盛情款待。”
他又鞠了一躬以示告辞,然后走过她的身边去安慰日暮。
“你不要太伤感,我会再为你留意的。大和男儿还怕寻不到好姑娘吗?”河村毫不避讳地在丧仪上说出此番话,重点都在为下属寻找新欢。
若昕和王渝谦说了一声,准备离开。王渝谦原本想起身送她,但被几个日本人拽在榻榻米上。他们借着酒兴用日语吱哇乱叫,一面像食盘上的八爪章鱼一样把他抓住。他根本站不起来,只好继续跌入酒池肉林中。若昕颇为同情地看了他一眼,但没让他看见那样的目光,原本也不想让他送,独自走到门外去拦黄包车。
周围全都是日本人的住宅,几乎每户人家的院子里都有几株越过墙头的樱花树,连成十里花海。她等了许久,也没能等到一辆黄包车,于是慢慢向外步行。虽然她不认识附近的路,但只要能走到任何一条大街,就不怕招不到车。
刚走了几步,她就听见身侧有鸣笛声。日暮良太坐在驾驶座上,摇下窗玻璃说:“王太太,我送您一程吧。”
她出于本能想要婉拒,又听他诚恳地劝说:“附近很不安全。我送您到最近的大街上,您就下车,不会耽误我的事。”
若昕上车后,良太又说:“最近时局很不太平,像您这样的——年轻女子在路边走,太危险了。”
他斟酌着措辞,原本想用美丽形容,但是又觉得那样太轻浮。
她接话道:“最近很不安全吗?我一直待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听说。”
日暮良太点头,说起最近的新闻:“听说有不少年轻女孩子夜晚在附近的无人处遭恶人轻薄,好像都是些流浪汉。他们实在太无耻了,竟然对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也下得了毒手。就是几天前的夜里,有两个女高中生又遭遇了不幸。虽然我们军营里的士兵击毙了歹徒,但是仍旧没有来得及救人。那两个姑娘受到侮辱后,当场投河自尽了,真是可怜。”
她把视线侧向窗外,凝望那片纯洁而灿烂的淡粉色樱花。她听说有人惨遭毒手,她也听说日本人最爱樱花。良太再说什么,她几乎就听不见了。
早晨十点,景行到了咖啡馆门口,店中一个人也无。他拿出钥匙开门进去,收拾好卫生后,站在正中间环顾四周。店里的桌椅,盆栽和摆件似乎都融进了他的影子。春黛绝对是上海城数一数二的好老板。她身上没有一点点架子,对员工又一直都很大方。邵晓慧虽然时刻不忘为自己捞好处,却也是个很开朗的女生。她和春黛的闲聊调侃是店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经常有那样一个午后,景行站在柜台后静听,她们倚在台前东拉西扯,聊起最近的新闻逸事,揶揄邻里的家长里短,不时发出清越的笑声,与咖啡的香气融合。
景行亦会把看过小说的内容,简而化之,用最白话的方式说给她们听。
春黛每回都听得很认真,有时会高声惊讶道:“那个男的有毛病吧?这就是很有名的好书啊。”
景行干笑一声,继续说下去:“手拿生锈时钟的老人称赞他:是个有精神的少年。”
春黛一脸无语,呵气道:“是个有精神病的少年。”
景行捧着书,笑得差点断气。两个客人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他们。春黛一脸淡定地对他们抛出笑靥,立刻让两个男学生屏住呼吸。“别见怪,他有精神病。”
三个人各自从住的地方附近买来零食,也会聊起彼此曾经的事。
春黛说:“我十六岁的时候,村子里有个小鬼一直对我有意思。长得挺俊俏的,又念过书,但没想到是个孬种,明明是他死缠烂打,结果反而跟别人说我先勾引的他,编出的故事像真的一样,害我被我家老头子打个半死。后来有一回他在河里洗澡,我故意走到上游去刷马桶。但是他根本不敢冲上岸骂我,你们猜为什么?”
景行不明白,忍笑摇头。
邵晓慧噗嗤一笑,指着春黛说:“你肯定事先把他的衣服给扔了是吧?”
“说中一半。不是扔了,我就是用他的衣服裤子擦的马桶。他向我划过来,我就趁机把另一个还没洗的,舀了半桶水,全泼他脸上去了,然后我就跑了呗。”
邵晓慧在前俯后仰中,惊讶地问:“李姐,你以前还刷过马桶啊。”她不敢相信眼前穿金戴银的俏丽女子曾经做过那种粗活。
“我是南京下面一个穷山村里出来的,什么活没干过。”
“哦~那你的名字是谁给你取的啊?真好听,不像是穷山村里的人会取的名字啊。”
春黛用指尖转动着腕上的金镯子,漫不经心地说:“找了个会算命的瞎子,让他帮我改的名字。”
“这样啊,那后来呢,后来他就没有找你麻烦吗?”
她轻描淡写地说:“后来啊,后来我就从家里逃出来了呗。”
邵晓慧没有再问下去。她知道春黛做过王渝谦的姨太太,把话题岔开,又骂起她最怨恨的家人,咬了一口核桃酥,“反正我就是死,也不会再让他们看见的。就他们那副像是被耗子啃过的德性,怕是谁好心把我送回去,都会被他们凭尸敲诈。”
今天邵晓慧始终都没有出现,春黛也没有来。上午照常一个客人都没有。景行打扫干净后,一直在复习英文。直到下午两点,春黛才慢悠悠地走进来。她像是没有睡好,即使妆容精致,但显得无精打采。她左右瞄了一眼,问:“就你一个人?邵晓慧呢?”
“不知道,她一直没来。”
“怎么搞的,昨晚也没说要请假啊。真是见鬼,一天到晚不知道在想什么。该不是把店里的钱都拐走,跑路了吧?”她口吻轻松地开起玩笑,靠在椅子上说:“我还想今晚把店门关了,找她陪我一起去逛商场。”
“不用关,我今天没事,可以在店里看着。”
景行打算等人到齐再说辞职的事。他已经想好了借口:大三新学期课程变多,他已无心力分神做兼职。
春黛打了个哈欠:“你一起去啊,我请客吃饭,再给你也买两件像样的衣服。你看看你穿的,跟在北平时有区别?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苛待员工。”
景行浅笑道:“你不挣钱啦?周末晚上可是生意最好的时段。”
她居然叹了一口气,阔气地说:“不挣了,先玩个舒心再说。光会挣不会花,算什么本事。”
她提起电话的听筒,拨了一串号码,打给邵晓慧的房东。然而接通后,那边却说昨天晚上没见到她回来。春黛请她去房间帮忙看看。大约三分钟后,房东的话语声才再度传来。这段时间,春黛一直举着听筒。
“我敲了半天门都没人应,房间里没人。看来她真的是一晚上没有回来。”
春黛几乎是把听筒砸回支撑架上,将景行吓了一跳。她瞪大了眼睛,紧张地说:“你快跟我走,去警察局看看。”
他们一下午问了咖啡馆和她租的房子附近的三家警局,都没有任何结果。邵晓慧就像是在世界上凭空消失一般。返回的途中,春黛默不作声,景行亦有气无力,当经过一条弄堂时,景行先是看见一摊乌黑的血迹,上面还覆盖着几片红色的碎布。然后他立刻发现一辆木板车边有两块点心。他认得出那就是他学会烤的饼干。
他把视线挪向身侧,春黛犹如一具艳丽的石像,盯着那一摊狼藉。
她说:“我们回去吧。”
景行想说的话一直卡在喉咙口,他仍是无法确定邵晓慧遭遇何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悸动与剧烈的压迫感堵在他的心口。
春黛一回到咖啡馆,把门从里面锁上。长久的寂静之中,她叫了声:“景行。”
景行抬起头看她。
“不要再管这件事了。”
他一言不发。
春黛说:“我想把咖啡馆关了,店面也盘给别人,不想再做了。”
景行还是没说一句话,默然凝视着她几近褪色的脸。
她打开抽屉,数清里面所有的钱,数了一遍又一遍。一共两百三十七元,她用信封装好全部都给了景行,僵硬地勾起一抹笑:“好聚好散。”
景行仍是沉默。她把信封架在景行的手背,低声笑道:“你还记得,你和我说的那个生锈时钟的故事吗?你也往前走,别再往回看。即使你回到过去,那段时间也照样是生锈的。” 无字花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