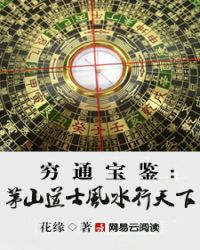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城堡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九章
他下了个狠心,挪动步子,走回贵宾楼酒店去,这一次不是沿着墙走,而是在院子中央踏雪前进。在门厅里他遇见了店老板,老板向他默默点头招呼,又向他指指通往酒吧的门,他只觉浑身发冷,也想见见人,便顺老板所指的方向走去。但是,当他看见在一张兴许是特意临时支起的小桌旁——因为平时那儿只放几个酒桶权且充作座位——端坐着那位年轻先生,而在他前面——这场面K.看了心里觉得压抑——站着大桥酒店老板娘时,他感到非常失望。佩碧得意地扬着头,脸上挂着那永远一成不变的微笑,看得出她充分意识到自己那不容置辩的风光体面,每一转身都把发辫一甩,她在酒吧里来往穿梭奔忙着,这时又拿来啤酒、墨水和钢笔,原来那位年轻先生面前桌上摆满了一份份摊开的文件纸张,他一会儿在这张纸上,一会儿又在桌子另一端的一张纸上找到某几个数字,将两者进行比较,现在正准备写点什么。老板娘的眼睛从高处向下俯视,她嘴唇稍稍翘起,好像很心安理得地看着年轻人和那堆文件,那神情似乎表示她已经把最重要的事全部说完,她的话也都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了。“土地测量员先生,您终于来了。”年轻人在K.进来时抬头望了他一眼说,话音一落便又埋头纸堆。老板娘也只向K.投来漠然的、毫无惊异之色的一瞥。佩碧则似乎是当K.来到柜台前要一杯白兰地时才看见他的。
K.靠在柜台上,一只手捂住眼睛,对周围的事一概不予理会。然后他呷了一口白兰地,把杯推回去,说这酒简直没法喝。“所有的贵宾都不喝这种酒。”佩碧只说了这一句,就把剩酒倒掉,冲洗了酒杯,把它放回架上去了。“贵宾们还有比这更好的白兰地酒喝。”K.说。“可能吧,”佩碧说,“可是我没有。”说完她就算是招待完了K.,转身去伺候那位年轻先生了,但是那位现在并不需要什么,她就只是在他脊背后面打转转,从这边到那边,来回走动,每次都毕恭毕敬地试着从他肩膀上看过去,看一眼桌上的文件;但她这样做纯粹是好奇,是装模作样抬高自己,就连老板娘也皱起了眉头对她颇感不满。
突然间,老板娘一下子露出注意的神色,竖起耳朵,两眼直勾勾地视而不见,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什么。K.回过头去,但他什么也没有听见,看样子别人也没有听到什么响动,可是老板娘却踮起脚尖大步向通往后院的门跑过去,俯下身子穿过锁眼往外看了看,回过头来时,眼睛便瞪得老大老大,腮帮涨得通红通红看着众人,然后用手指招呼他们过去,于是,众人便轮流趴在锁眼上往外看,看的次数最多的自然是老板娘,然而佩碧也屡受照顾,而与众人相比,对此最不关心的要算那位年轻先生了。佩碧和那位先生也在不多时以后就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只有老板娘还在那里使劲张望,她腰弯得很低,简直都快跪倒在地上,这种样子几乎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她只是在那里苦苦哀求锁眼开恩放她出去,因为,这时外边院子里大概早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当她终于又直起身,两手在脸上抹了一把,理了理头发,深深吸了一口气,眼睛似乎不得不重新适应这房间和这里的人(这样做她很不情愿,真是勉为其难)时,K.开口发问了——并不是想让她确证一下他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而是为了先发制人,免得再次受到打击,现在他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一想到受打击简直就心惊肉跳。
“这么说,克拉姆已经乘雪橇走了?”老板娘不言语,从他身旁走了过去,然而那位先生却从他的小桌那边回答道:“毫无问题,走了。既然您放弃了您坚守的岗位,克拉姆当然就可以走了。可老爷非常之敏感,这真是太令人佩服了!老板娘太太,您注意到了刚才克拉姆老爷是多么焦躁不安地往四下里察看吗?”看来老板娘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那位先生仍接着说下去:“唔,幸亏他什么也看不出来,连雪地里的脚印车夫也全都扫平了。”“老板娘太太什么也没有注意到。”K.说,然而他说这话并非抱着某种希望,而只是被那位先生的话惹恼了,听他那口气,好像一切都成了定局,一切都无可挽回似的。“也许那会儿正好没轮到我从锁眼往院里看,”老板娘说,这话首先是为了袒护那位先生,接着她又想说明克拉姆没有什么不足之处,于是补充道:“不过,我不相信克拉姆会那么过于敏感。当然,我们生怕他受到打扰,想方设法保护他,我们是从设想他是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出发这样做的,这是对的,肯定也符合克拉姆的意思。可是事实究竟怎样我们并不知道。不错,克拉姆不想跟谁谈话他就决不会跟这个人谈话,不论这人费多大力气,不管他怎么软磨硬泡也是没有用的,但是,克拉姆决不会跟他谈话、决不会主动让他来到自己面前,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够了,为什么定要说他事实上一看见谁就受不了呢。至少这一点没法证明,因为这种例子是永远不会有的。”那位先生不住点头。“当然,我的想法基本上也是这样,”他说,“刚才我那些话措辞上有些不同,这只是为了让土地测量员先生好懂些。不过克拉姆刚才出来时确实向左右两边来回看了好几次。”“也许他是在找我吧。”K.说。“有可能,”那位先生说,“我还真没有想到这一层呢!”这句话引起全场哄笑,佩碧对所讲的这些几乎完全听不懂,可她却笑得最响。
“既然我们现在高高兴兴地聚在一起,”过了一会儿那位先生说,“我想恳请您,土地测量员先生,给我提供一些情况,以便补上我这些卷宗里的空缺。”“这里写的东西真是太多了。”K.说,一边从远处向那堆文件投去一瞥。“是呀,这是个坏习惯,”那位先生说着又笑起来,“可是您也许还一点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叫莫姆斯,是克拉姆的村秘书。”这话一出口,整个屋子里气氛顿时严肃起来;老板娘和佩碧虽说当然是认识这位年轻先生的,但在听到提及他的名字和职务时仍为之一震。就连那位先生本人似乎也觉得自己说的话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似乎他想至少是躲避一下这句话中蕴含着的、说出后仍继续施放出的非同小可的威力,便赶紧埋头去看他的文件并提笔书写起来,以致屋里一时只听见笔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村秘书?村秘书是做什么的?”少顷K.问道。显然莫姆斯认为在他作了自我介绍之后再亲自作这类解释是不合适的,于是老板娘便代他回答:“莫姆斯先生是克拉姆的秘书,跟克拉姆任何其他秘书一样,但他的职务地点、办公地点,还有,要是我没有弄错,还有他的职务范围、职权范围,”这时莫姆斯一面写一面起劲地摇头,于是老板娘纠正自己的话说:“这就是说,只有他的办公地点,不是说他的职权范围,是在这个村子里。
莫姆斯先生负责起草克拉姆在本村需要拟定的全部文件,最先过目和处理本村人呈送上来的所有申请书。”K.这时脑子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用失神的两眼木然盯着老板娘,弄得她有点发窘,补充道:“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安排的,城堡的每位老爷都有一批自己的村秘书。”莫姆斯听这些话比K.专心得多,这时他补充老板娘的话说:“绝大部分村秘书只为一位老爷服务,而我是同时为两位老爷办事,克拉姆和瓦拉贝纳。”“对,”老板娘现在想起这点来了,便又对K.说:“莫姆斯先生为两位老爷办事,克拉姆和瓦拉贝纳,所以他是双重秘书。”“嗬,秘书还外加双重。”K.一边说,一边向这时几乎完全趴在桌上抬起头来面对面瞅着自己的莫姆斯点头,恰似听见别人夸一个孩子时向那孩子点头一般。如果说这种点头包含着某种轻蔑的成分,那么它不是没有被注意到,就简直是完全自找。怎么偏偏要在这个连让克拉姆偶然看上一眼的资格都没有的K.面前大夸特夸一个克拉姆手下人的功劳,毫不掩饰地意欲博得K.的赞赏呢!可是K.却一点不识抬举,比如,他现在是在千方百计要求一见克拉姆的,却不觉得一个能在克拉姆眼皮底下过日子的人有什么了不起,更谈不上欣赏和羡慕。因为,说实在的,接近克拉姆本人并不是他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而是:他K.要亲自(不是别人)带着自己的(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要求去会见克拉姆,会见克拉姆并不是为了在那里歇着而是经过他身边继续前进,到城堡里去。
于是他看了看表说道:“现在我得回去了。”这话一说出口,情况马上变得有利于莫姆斯。“唔,当然啦,”莫姆斯说,“学校勤杂工的活在等着您。不过您还得再给我一分钟。只有几个简短的问题。”“对此我不感兴趣。”K.说着便想向门走去。莫姆斯一捶桌子站起来:“我以克拉姆的名义要求您回答我的问题。”“以克拉姆的名义?”K.重复道,“难道他会管我的事吗?”“对这一点,”莫姆斯说,“我无权发表意见,您恐怕就更没有这个权利了,所以我看我们两个还是让他自己去决定好了。但是,我凭着克拉姆授予我的职权,却可以要求您留下回答问题。”“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插嘴说,“我不想再给您出什么点子了;我给过您不少劝告,我纯粹是为您着想,那是天下最最好心的劝告了,可您不识好歹,全都顶了回来,现在我所以到秘书先生这儿来——我什么都用不着隐瞒——仅仅是为了好好向村秘书汇报一下您的所作所为、您的意图,并且永远杜绝您重新在我们店里留宿的可能,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了,这种情况恐怕以后再不会有什么改变,所以,现在我说出自己的想法绝不是为了帮助您,而是为了给秘书先生稍微减轻一点负担,他面对的是您这么个人,是同您打交道,这项任务太艰难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是正因为我是完全坦率的——同您打交道我只能坦率直说而不可能有别的方式,但即便这样我也是勉为其难——所以只要您愿意,您还是可以从我的话里得到好处的。要是您愿意,我现在就请您注意:您想到克拉姆那儿去,唯一的通路就是先让这位秘书先生作记录。
不过我也不想把话说过头了,也许这条路还是通不到克拉姆那里,也许它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就到头了,这全得看秘书先生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对您来讲这是唯一的一条至少是朝着克拉姆那个方向去的路。可您现在却不想走这条唯一的路,而又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只是因为爱顶牛吗?”“唉,老板娘太太,”K说,“这既不是通向克拉姆的唯一道路,它也不比别的路更值得去走。您呢,秘书先生,如果我在这里说点什么,那么是您来决定我这些话能不能传到克拉姆那里去了?”“当然,”莫姆斯说,一面得意地低垂眼皮左顾右盼,然而两边什么也没有,“否则要我这个村秘书干什么。”“好,老板娘,您瞧,”K.说,“现在不是说我到克拉姆那里需要一条通路,我首先还得打通到秘书先生这里的路呢。”“我原想给你打通这条路的,”老板娘说,“上午我不是提出愿意把您的请求转到克拉姆那里去吗?我想的就是通过秘书先生办到这事。可是您拒绝了,而现在您除了这条路确实没有别的路好走。当然,照您今天这种表现,在您还试图对克拉姆来个突然袭击之后,成功的希望是更小了。但是这最后一丁点儿、一丝丝儿、差不多等于零的希望,却是您唯一的希望。”“这是怎么回事,老板娘,”K.说,“为什么您原先起劲地阻拦我,叫我别费力去找克拉姆,现在却这样重视我的请求,好像以为要是我这事办不成就一切都完了?如果说您原来是真心诚意劝我干脆放弃找克拉姆的打算,那么怎么可能现在又似乎是同样真心诚意简直是催着逼着我走这条路,甚至明明知道这条路根本通不到目的地也还是要劝我去走?”“我催您逼您了吗?”老板娘说,“我说您的打算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这叫催您逼您吗?您居然这样把自己的责任推到我身上,这真是——天下还有比这更蛮不讲理的吗?是不是当着秘书先生的面您才来劲了?不,土地测量员先生,我一点没有催您逼您去干什么,我只可以承认一点,就是我头一次见到您时也许把您估计过高了些。您那么快就把弗丽达弄到手,把我吓着了,当时我真不知道您还能干出些什么可怕的事来,我想避免再出什么祸事,就以为只有通过请求、警告等办法能打动您,防止事态恶化。
可从那时到现在这段时间我学会了比较冷静地全面考虑这件事。好了,您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您的活动也许能在外边雪地里留下很深的脚印,除了这个还会有什么结果?”“您说了半天,我觉得您态度上的前后矛盾现在仍然没有完全讲清楚,”K.说,“不过我总算是指出了这个矛盾,这我也就满足了。但是现在我倒要请您,秘书先生,告诉我一下,老板娘刚才说您同我谈话的记录以后可能会有的结果之一,就是允许我谒见克拉姆,这话对不对?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我愿意马上回答您的问题,为了这个,我是什么都豁出去了。”“不,”莫姆斯说,“这种逻辑关系并不存在。这里做的事仅仅是把今天下午的情况详实地记述下来以便交克拉姆的村档案室存档。现在这篇记述已经写完,只差两三处空白需要由您补上,这是制度;作记录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抱着任何其他目的也是达不到的。”K.默默地看着老板娘。“您干吗老盯着我?”老板娘问,“难道我说的同他说的有什么不同?他就是这样,秘书先生,他就是这样。先歪曲人家提供给他的情况,然后硬说别人给他提供了错误的情况。我打一开始就是对他这么说来着,今天是这样说,以前也都这样说,告诉他想受到克拉姆接见是没有丝毫指望的;既然没有丝毫指望,那么有了这份记录不也一样?这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我又说这记录是他能同克拉姆建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公务联系;这话不也同样清清楚楚,一点怀疑的余地也没有吗?但是,现在他不信我的,一个劲儿地希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有什么目的——能钻到克拉姆身边去,那么,如果顺着他的思路想,不就只有他现在同克拉姆之间仅有的这一真正的公务联系,就是说这份记录,才能帮他一点忙吗?我说的话就只有这层意思,谁要是硬把别的意思安在我头上,那就是不怀好意歪曲我的话。”“如果是这样,老板娘太太,”K.说,“那么我请求您原谅,是我误会您的意思了;因为我原以为——现在看来这是错了——从您以前的话里听出的意思是我确实还有一星半点希望的。”
“对极了,”老板娘说,“这确实是我的意思,您现在又在歪曲我的话了,不过这一回是反过来歪曲罢了。按我的意思,这种希望对您来说确实是存在的,但它只能建立在这份记录上。说有希望,也不是说您就可以劈头盖脸地拿‘我回答了问题,就可以去见克拉姆了吗’这样的问题将秘书先生的军。如果一个孩子这样问,大家一笑就完了,但如果一个成年人提这种问题,那就是对官府的一种侮辱,只是秘书先生给您留点情面,用他那巧妙的回答把这点掩盖过去了而已。我说的那一点点希望,正是指您通过这份记录才同克拉姆有了联系,也许可以算是一种联系吧。难道能说这不是希望吗?要是问问您,您到底有什么功劳使您有资格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送给的这点希望,您能讲得出一丝一毫来吗?当然,对这点希望现在还不可能说得那么确切,特别是秘书先生以他的官员身份,绝不可能对这个作出哪怕只是一星半点暗示。正如他刚才说过的,他只是按制度办事,把今天下午的情况记录下来;多一点他也是不会说的,即使您现在根据我说的去问他,也一定问不出什么来。”“秘书先生,”K.问,“克拉姆会不会看这份记录?”“不会的,”莫姆斯说,“为什么要看?他看得了所有的记录吗?实际上他连一份记录也不看。
他常说‘别拿你们那些记录来烦我了!’”“土地测量员先生,”老板娘抱怨道,“您这些问题真是让人头疼!要克拉姆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这份材料,了解您生活里那些鸡毛蒜皮,这难道有什么必要,或者哪怕只有一点点益处?您干脆放下架子,求别人不要让克拉姆看到这份记录,不是更好些吗?当然,这个请求也同那个一样荒谬——谁能瞒得住克拉姆什么事?——可怎么说也还能让人对您有点好印象吧。再说,为实现您所谓的希望,有必要让克拉姆看材料吗?难道不是您自己说的,只要有机会在克拉姆面前讲话就满足了,即使他不看您一眼不叫您说话也行?有这份记录,您不是至少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吗?弄得好说不定收获还会大得多呢!”“大得多?”K.问,“怎么个多法?”“只要您别总像小孩子似的,”老板娘叫起来,“希望人家把什么都端到嘴边给您吃就行!谁有本事回答您这些问题?记录要送到克拉姆的村档案室,这您已经听到了,对这个问题只能说到这儿,再多就说不准了,可是还有一点,您知道这份记录有多么重要,秘书先生、村档案室有多么重要吗?您知道秘书先生审问您意味着什么?也许,唔,很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审问的意义呢。正如他说的,他是按制度办事,平心静气地坐在这里尽他的职责。但请您注意,他是克拉姆任命的,是代表克拉姆办事的,他做的事即使永远到不了克拉姆耳边,却是自始至终得到克拉姆同意的。如果不是完全符合克拉姆的精神,能得到他的同意吗?我说这些决不是想当面拍秘书先生的马屁,我要有这个意思他也会坚决制止的,我不是在孤立地谈他这个人,而是在谈克拉姆同意他办事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谈的是现在的实情:他是一个工具,克拉姆的手就放在他身上,谁不服从他谁就等着倒霉吧。”
K.并不怕老板娘这些恐吓,而她用来诱他上钩的这希望那希望他也听腻了。克拉姆是远不可及的。有一次,老板娘曾把克拉姆比作老鹰,当时K.觉得这未免可笑,现在不然了;他想到克拉姆的远不可及,想到他那无法攻克的住所,想到他总是一声不响,也许只偶尔被他自己那K.还从未听到过的大声喊叫打断,想到他那从上向下俯视时凌厉逼人的目光,那既无法证实又无法否认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想到他那高高在上、按人们无法掌握的规律在自己四周划出的一层又一层的圆圈,这些圆圈人们的眼睛只能偶尔看见,K.从他低下的地位看去是一道又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线:这些都是克拉姆同老鹰的共同点。然而眼下这份记录同这肯定是风马牛不相及,此刻,莫姆斯正趴在记录上掰开一个椒盐卷饼,就着啤酒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盐粒和卷饼碎屑撒得满桌文件上到处都是。
“再见,”K.说,“我对任何审问都很反感。”说完他真的移步向门走去。“他到底还是要走。”莫姆斯话音里几乎带着惧怕对老板娘说。“他不敢。”老板娘说。下面的话K.就听不清了,他已经到了门厅里。〔18〕 天气很冷,刮着大风。从对面一道门的后面,老板走了出来,看来他一直在那门后通过窥视孔监看着门厅的动静。门厅里穿堂风猛烈地吹打他外衣的左右下摆,使他只好把它们卷起掖在腰间,“您这就走了吗,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您觉得这很奇怪吗?”K.问。“是的,”老板说,“不审问您了吗?”“对,”K.说,“我不愿受审。”“为什么不愿?”老板问。“因为,”K.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服服帖帖受人审问,为什么要让别人拿我开玩笑,为什么要让人在我身上使官老爷性子。也许哪天我也来了兴致,开开玩笑,使使性子,那时可以奉陪,可是今天不行。”“是啊,对,没错,”老板唯唯诺诺,然而只是出于礼貌随声附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同意。“现在我得叫服务员们到酒吧去了,”他接着说,“他们早该上班了。刚才我只是不想打扰审问才没叫他们来。”“您觉得这审问有那么重要吗?”K.问。“当然非常重要。”老板说。“那么说我刚才不该不接受审问了?”K.说。“是啊,”老板说,“您不该这样做。”因为K.不说话,老板又补充一句,或者为了安慰K.,或者为了快点脱身,说道:“咳,咳,不过事情总还没有严重到引起天上下雹子吧。”“对极了,”K.说,“看这天气不像会下雹子。”两人哈哈大笑着分手了。 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