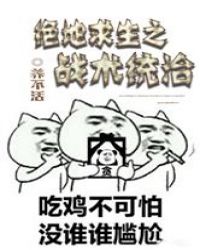“从前,小人是御医堂负责熬药的医者,这毒和当年的一模一样,传闻老堂主当年手上有一种毒素,是从蟾蜍里研制出来的,原本此毒只是用来麻醉,然后用特定的解药苏醒,经过对无数伤患的使用,其副作用渐渐暴露出来,老堂主当时为了避免此药产生更大呃害处,因此则秘密销毁了,因此江湖中,能够知道这个蟾蜍毒素的其实不多,原本这毒只是挥发的药物,如同一般的硫磺,朱砂,被火烧起来会有烟雾产生,致人一种昏昏欲睡的沉眠,要识别这种毒,可以用水浸泡,若是黑色的毒素化成绿色,则表示一定是蟾蜍毒。”
忍风双眉一掠,顿觉万重乌云掩盖其身:“我记得阿弥也曾经说过这些话,这么说……白云观上的事情不过是前兆……秋水所处的五毒门并没有放弃对这种毒素的调制,反而将这种只能使人昏迷的毒素变成一种杀人利器,这个五毒门,究竟在干什么!”
他愤愤得用手拍着椅背,将掌心拍得疼痛。直过了很久,还能从他的口中缓缓说出:“看来秋水是解决这一切事情的关键。”
容一奇面色铁青,凝重地不知道思考着什么,现场仿佛进入了一种可怕的寂静中。
晚风本应是吹走氤氲的,却在现在,又给了众人心头更多的愁云。
“自从小人当了仵作之后,就没有再见过这种毒素了,想不到居然在这里重现江湖。”
忍风点了点头,问跪在地下的仵作:“常听仵作替死者验尸之后,会留下一些值得考证的证据,尤其是替官府查验尸首的仵作,不知道你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
仵作说:“少侠你猜对了,小人正是得到一个碎布,上面的腥血是彦氏兄弟喉咙里的毒素。”
“如果说,我把这个东西和白日里的馒头一对比,若是在水中都能够产生绿色毒素的话,是不是就能够说明彦氏兄弟是在牢里被毒害的?”
忍风说着,看着坐在椅子上的这么多人,容一奇惊颤得不能合拢嘴巴。毒蜂则满头大汗,牙口死死咬合着,却还装成一幅毫不在意的样子。只有张久褚瞳仁里迸发出闪烁的亮光,他起身下袖,过了一会,才道:“来人,取两盆清水来。”
随从立马应声答应,退了下去。
张久褚语调似冷,对跪在地上的仆人说:“不要跪了,快站起来吧。”
说着,他让仵作坐在自己所坐的那张椅子上,仵作不敢下座,强行被张久褚按着坐了下去。
不到半盏茶的时间,随从来了,他手里端着两碗清水,张久褚转身,走到铁架上拿来燃烧着的宫灯,忍风和他相视一眼,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只见忍风从袖口里拿出昨日那块馒头来,容一奇脸色更糟了,他半张脸立在人群后抽搐着,又像惊惧,又像疑惑。毒蜂则站在他身旁,两人不敢有任何的接触,视线一直盯着这两碗放置在碗中的清水,平如纹镜。
仵作将从尸体上的沾过的毒素碎布拿出来,忍风则将馒头撕裂一小块,扔进了清水内。
众人细细观察着两碗水的动静,气都不敢轻易呼吸一口,只是不敢将眼神稍移水面半步,接下来就是张久褚将蜡烛照亮着两碗水。
“变色了!”
施云彪禁不住叫了出来,两碗水同时变色,而且都是墨汁放久了的褐绿色,容一奇瞪大双眼,眼珠暴露,一直顾着盯着烛心映耀在水面上的倒影,偶尔有几个烧过的烛心落在了碗里。一场试验惊心动魄,人心各异,纵有文字都不能将每个人此时此刻的心情描绘出来。
晚间的苍风还是一如既往地吹拂着,因为紧张,众人只感到有些麻木的悚意,绝非是风吹过时的透凉。
“好了,原来真的县衙里出了内鬼,事实真的像忍风说的那样,彦氏兄弟以及那个薛府家丁,都是被人有意害死的,谁会这么狠毒?!谁有这个胆子下这样的毒手,光天化日下居然在县衙里杀害证人?!”
张久褚登时怒火中烧,他急切地往后瞥向目光,射在了惊惧不已的毒蜂身上,毒蜂县令颤颤说:“大……大人,当时我和你一同去云天山薛府祖碑的,实话说,这……这我也不知道啊。”
他说完,眼神很不自然地看向别处,张久褚道:“那看守棧牢的孙其三,孙其五两人,会不清楚吗?传唤他们来。”
毒蜂只能硬着头皮让衙役去传孙其三,孙其五两人。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有解决不开的困局。在毒蜂出发去云天山的那一刻,孙其三,孙其五两人就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不妥。他们在白天已经商量好了口供,也预料着有此一着,因此,看上去,他们显得比众人更加淡定。。
孙其三背着手,遂不知危机已悄然降临。
孙其五则站在廊下,他眼神不定地看着从楼台照来的一帘月色,有人走动的脚步回响传到廊前,孙其三冷笑一声:“你看,照我说的去做,只要待会有人传我们俩,就把下毒的事退到那个穿红袍的人身上。”
孙其五还是惶惶不安,问:“可是那个人什么名讳,我们并不知道啊。”
“你懂什么,只要我们将这些烂事推到他们身上,我们弟兄俩就一点事都没有!”
“可……可是。”孙其五擦了擦脖子流落下来的汗珠,牙关打战。
“你镇定点行不行?万一被人看出破绽来的话……你我都要性命不保……”
走廊陷入了一片瘆人的静寂,来的人脚步飞快,孙其五像是想到了什么:“大哥……这个声音不是县衙里的人!”
孙其三当即吓得面如土色,他也猜到了来者。 雪影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