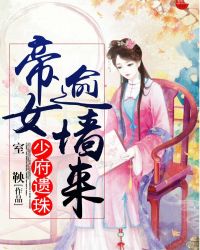第一百五十九章 藏而匿之
当章邯、蒙毅等人顺腾摸瓜寻找赵高勾结刺客的证据时,赵高已经迅速结了案,将案卷呈到了嬴政的案头。
嬴政屏退了书房内所有的人,手中抚着那卷竹简,迟迟没有打开。
赵高明白他在担心什么,也知道他想听什么,便上前一步躬下腰身,语气平稳、神色自若:“陛下,此案皆由昌平君的族人一手策划,与其他人无关。”
嬴政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他没有说话,将竹简推开,低头仔细看过。
赵高也不着急,垂着脑袋耐心等他阅完。
“朕看在昭彤的面子上优待他们、饶他们不死,没想到他们却不知好歹、积怨在心,竟要取朕性命。朕不畏死,却绝不允许有人暗中破坏我大秦万世基业。这一次,朕必须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陛下说的极是!陛下对昌平君的族人网开一面,他们反而恩将仇报、枉顾陛下隆恩、坏我宗庙社稷,这等大逆不道,依法当夷三族。昌平君身份特殊,他是曾经的楚国王族,又与我大秦皇室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此狼子野心,若不严惩,天下人当真以为我秦律只是儿戏。”赵高微微抬起头来,机敏而又迅速地扫过嬴政的面容,恰到好处地顿了片刻,“臣明白,陛下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与扶苏公子扯上关系。幸好公子恪守为臣、为子之道,与那些乱党泾渭分明、不曾有过任何往来。既是如此,陛下就没了顾虑,可以放心大胆地处治这些人了。”
嬴政抬头看着他,眼神似是而非,让人有些捉摸不透。
这么多年,他一直坚守着一个原则,那就是绝不在气头上做任何决定。虽然甫一看到卷宗时,他的心头立刻便燃起熊熊怒火,呼啸而过,誓将一切化为灰烬。然而待赵高说完这些话,他已经平静了些许,因为怒气而混乱的思绪得以重新梳理。
“当年是昭彤出面,才让昌平君一族得以保全。若是天下人知悉真相,难免不会想到旧事,将这些怪罪到她的头上。斯人已逝,不该再被世间的浊事所扰。再者,天下间多的是颠倒黑白之徒,他们不在乎事实真相,只以捕风捉影、混淆视听为乐。即便扶苏是清白的,他们也能无所不用其极来中伤他。朕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
听出嬴政话锋的转变,赵高心中迅速转了几个圈。他佯装痛心疾首,重重叹息一声跪了下去:“陛下所虑,令臣感怀。陛下既为人君、又为人父,凡事皆为扶苏公子着想,实在是为君、为父之典范!臣明白陛下的苦心,却又真心为陛下叫屈。陛下为了收服天下人心,一忍再忍。草木若有情,也当为陛下的诚心所感动。可是那些狂悖之徒却毫无知恩之心,陛下越是忍,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从博浪沙到咸阳,他们一直不曾悔改,反而越发猖狂!如今他们竟然想在陛下的家门口行刺!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味忍让并非长久之计,陛下您得让天下人明白,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我大秦之号令赏罚绝非空文!天命在陛下,您便要让他们亲眼看看,与你为敌的下场到底如何!”
他看起来义愤填膺,说到最后竟忍不住哽咽难平。
嬴政本来是有些心烦,见他这般,反倒不忍再说什么严厉的话。
“你的心情朕能理解,朕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京师重地竟然生出这等悖逆之事,一旦大肆传言出去,定会引起民心惶恐。天下间还隐匿着多少居心叵测之徒?有多少人隐在暗处蠢蠢欲动?一点小小的风吹草动,一旦处置不当,极易形成燎原之势。朕宁可息事宁人,也不能因小失大,毁了这来之不易的安宁。”
说罢,他长叹一声,似是下定了决心:“你所说并非全无道理,若要稳定,只靠求全拉拢断不可行,只有赏善罚恶,才能令臣民惧服。若不对这些人施以颜色,他们当真以为秦律只是摆设。”
赵高心头微动,抹了抹眼眶试探着问道:“陛下之意,这案子还是要严办?”
嬴政想了又想,微微颔首:“该办自是要办,只不过不要与昌平君扯上关系。你把案子交给李斯,告诉他将昌平君的名字抹去,只说是城中遇上了盗贼。这样的话,一来不会牵连扶苏,二来也不会引起其他几国王族的恐慌。朕严惩盗贼,为的就是除恶保民,如此一来,天下人既会感念圣恩,同时又震慑于秦法之严明,岂不是一举两得?”
“盗贼?”赵高微怔,一时没能反应过来。
嬴政默默收回视线,落在那一册卷宗上:“宫城脚下竟有刺客,这件事一旦传出去,你觉得天下的臣民会怎么想?”
赵高反应过来:“是,还是陛下想的周全。只说是劫财之贼,不提刺客之名。”
见他一点就通,嬴政稍觉宽慰。
“知道朕为何同意将此案先交给你吗?”
猝不及防被问到这样尖锐而敏感的问题,赵高的神色闪了一下。他小心翼翼望向嬴政,见他面上浅浅漾着些玩味之意,慌忙垂下头去。
“陛下是怕此案关系复杂,所以才先让臣去查的。”
嬴政并不打算放过他,继续追问:“何为关系复杂?”
一时间,赵高有些慌乱。他迅速在脑中思忖,决定还是应该坦诚回答。
“陛下是担心此事会累及扶苏公子。”
果然,嬴政对这个答案很是满意。他将案上的卷宗轻轻卷起,递给赵高。
“知子莫若父,朕相信扶苏不会做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可是,朕却不能保证他身边没有暗藏祸心之人。朝堂之上,错综复杂,他的事容不得一丝差错。并非是朕偏袒他,只不过关系到朝局稳定,朕不得不谨慎一些。扶苏常与李斯共事,如果交给李斯来查,恐有人说朕处事不公。你与扶苏鲜少来往,如果连你都证实扶苏无罪,那别人也就说不出什么了。”
赵高默默听着,心里暗自揣摩。虽然嬴政嘴上说着是为了避嫌,可他心里到底是因为避嫌,还是因为害怕李斯替扶苏隐匿,这一点,赵高摸不准。
摸不透的事情便闭口不言。赵高明白这个道理,捧着卷宗,恭敬地俯着身子:“陛下为国事殚精竭虑,相比之下,臣倍觉惭愧。”
“这件事你做的很利索,朕很满意。”嬴政看了他一眼,“朕还有件事要交给你。”
赵高心头一动,默不作声近前几步。
“昌平君的族人绝不可再留在咸阳。”嬴政缓缓靠在凭具上,一手撑住额角,“朕答应过昭彤不杀这些人,朕不会食言。除了那些案犯之外,其余人皆流放,永世不得返回中原。这件事不用通过廷尉,由你去安排。至于他府上的田宅家产,也由你登记造册,之后上交少府。事不宜迟、夜长梦多,限你十日之内办妥。至于扶苏身边之人,朕会亲自去查,你就不要再管了。”
嬴政态度强硬,将此事彻底压了下来。一场暗杀眨眼间变成了盗劫,赵高莫名有些失意。
事实上,这一切确如章邯与蒙毅所猜想那般,所有的事情皆由赵高一手精心策划。他明白人心的弱点在何处,便逐步向昌平君的族人灌输对嬴政父子的仇恨,尤其是对扶苏。
扶苏是嬴政的儿子不假,可他身上仍有楚王族的血脉。昌平君事发时,他不仅不说情,反而袖手旁观、坐视不理。昌平君死后,他更是疏远一切楚国王族。如此数典忘祖,简直天地不容。
仇恨的种子一旦种下,罪恶之花便开始孕育。
这么多年来,扶苏越发成熟,嬴政对他的期许与日俱增,想要扳倒他几乎已经不可能。可赵高不会放弃,既然搬不走,那便彻底清除掉。借刀杀人,不论成功与否,自己都能全身而退。就算不成功,此事定会将嬴政逼进暴怒的深渊,一旦他大肆彻查,不论有无实证,扶苏必定难逃一劫。
实际上,他虽然隐匿了身份接近昌平君的族人,却并未打着沅茝殿的旗号,所谓宫中之人来自沅茝殿,不过是他教给刺客首领的一个说辞罢了。对于刺客而言,若是不能亲手除掉扶苏,那么将这摊祸水引到扶苏身上亦能解恨。刺客自然而然地听信了赵高的话,只是他不知道,这句如同复仇利刃一般的话,其实也会要了他自己的命。
赵高已经猜到,一旦事发,不出意外会由郎中令来审问。若是刺客首领落在蒙毅手里,凭着他与扶苏的交情,必不会坐视扶苏受诬。如此一来,便可借蒙毅之手除掉唯一与自己有过来往的证人。虽然无法直接污蔑扶苏不免遗憾,然而相较之下,如何确保自己全身而退才是最重要的事。
当然,若是蒙毅没有选择替扶苏隐瞒,那么这件事就更加简单。嬴政对蒙毅与扶苏的关系心知肚明,绝不会将案子交由他去审。赵高已经想好了说辞,有十足的把握获得这个案子的审判权。
然而,赵高却低估了嬴政的忍耐力。他确实怒气冲天、如狂风席卷,可他心里清楚,自己的决定将会影响朝局的走向。
嬴政明显不想将扶苏拖进这滩浑水。
赵高看的清楚,虽然他很想给扶苏罗织一些罪证,然而面对嬴政这样精明的君主,他不敢轻易出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不仅伤不到扶苏,更会将自己的前途彻底葬送。
况且,赵高明白,嬴政并不完全信任他,否则就不会让蒙毅来看管案犯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赵高不敢节外生机,谨慎地处理着与案件相关的事务,并确认自己没有留下任何与刺客勾结的证据。随后,便迅速结了案。
自己辛辛苦苦策划多年,结果又是这样付诸东流。赵高越想越气,继而对扶苏的恨意也越来越深。
人心很是奇怪。若是细究起来,扶苏与赵高之间并无什么难解的恩怨,甚至在扶苏幼年时,赵高还曾短暂地做过他的师父。或许是因为自卑,或许是因为自负,在众星捧月一般的扶苏面前,赵高总觉得自己像是微不足道的尘埃,找不到任何立足之地。
他如坐针毡、极尽小心,当心中的恐慌和不甘积压难平,恨意便如荒草疯长,继而吞噬掉他心中仅剩的理性。
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扶苏就这样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至于蒙恬、蒙毅、章邯,他暗暗发誓,迟早有一天,一定要将这些不可一世的人踩在脚下。
扭曲的恨意促使他一次又一次设下圈套,但有嬴政在,他的计谋从未成功过。失败刺激着他的神经,也慢慢磨平着他的耐心。
赵高怅然若失地出了政事殿。他抬头望天,竟是晴空万里。期待中的暴风雨毫无迹象。
下了台阶,他刚准备去廷尉府找李斯,忽然听见一声呼唤。
“公子?你怎么来了?”见胡亥气喘吁吁,赵高将他拉到一边,警惕地环顾四周,“你先回去,臣忙完手中的事会亲自去兴乐殿向你解释。”
胡亥一把抓住他的手,指尖掐进肌肤里,钻心的疼:“我只问你一件事,是你泄的密吗?”
话音一出,赵高寒了脸:“公子在想什么?!这里人多眼杂,回去再说。”
胡亥不肯松手,执拗地瞪着他。
赵高无计可施,重重叹了口气:“不是。”
“真的?”
“臣何时骗过公子?”
胡亥将信将疑,犹豫着松开手:“好,那我在兴乐殿等你。” 少府遗珠:帝女逾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