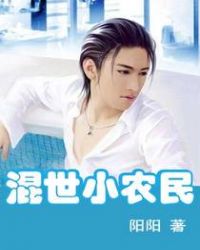第二百零一章 银针
等着再阳睡下了,韫姜才起身回自己的帐子里去。
到了外头,韫姜细声细语地对再枫道:“你也一直陪在这儿,怕是累着了,快回去休息吧。”她伸手抚过再枫的肩头,“你父皇跟前,要多说好话,别抱怨,知道么?你父皇生气是一码事,你们兄弟之间的情分又是另一码事。”
再枫重重点头,把韫姜的话都记在心里,又愧疚道:“德娘娘,对不起……要不是我,再阳他也不会……”
“不许说傻话。”韫姜佯怒,还是有盖不住的优雅与温情在她眼里打转,“你是最好的孩子,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不许自责,回去好好睡一觉,不要多想,知道了么?”
再枫鼻头一酸,默然垂下了头。韫姜抚上他的鬓角,柔和地引导他抬起头来:“乖孩子,有什么心思都同母妃说,别拘在心里头闷坏了。”
再枫嘴角抽搐着,显然压不住满心的内疚与自责:“德娘娘你好容易才叫再阳放开了,却出了这桩事,原是我没眼力见,否则也不会这样了。我怕再阳不高兴,也怕你后悔伤心,都是我的错……”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掩面哭起来。
韫姜眼眶一红,不想再枫的心思这般细腻,也是十分动容。她柔声劝他:“你没有错,再阳伤着了,我难免揪心,可是没有后悔,再阳也不曾郁闷。我们是好好的一家人,谈什么错不错的,岂不是生分了?”
她捻着绢子揾了揾再枫的眼角:“好好的男儿郎哭什么?我才不哭了,你反来招我伤心。”再枫知道韫姜哄着自己,于是勉强破涕一笑,死死忍住了泪。
韫姜特地叫泷儿过来,陪着再枫一道回去。等他们走了,愈宁过来悄声问:“娘娘可要去瞧瞧恪贵妃么?”
“去,为什么不去?”韫姜兀自抬步往恪贵妃的帐子处去,现在是紧要的关头,她和恪贵妃绝不能生出嫌隙,“本也没个对错之分,意外罢了。再勋是逞强了些,可也不是故意往再阳额上砸的。皇上大怒,因为他要顾虑到国本。可我们这些人,仔细想想,没必要闹得人仰马翻的。”
已有夜色,风也渐凉,愈宁叫顾诚折回去取个披风来。韫姜感受到瑟瑟的寒风钻入骨子里,让她的头脑格外清醒。
到了恪贵妃的帐子时,千珊同宁福正守在外头,一见韫姜过来,神色各异,一时也不知怎样开口。二人默然行了礼,欠身绾起帐帘,意在让韫姜进去。韫姜示意愈宁不必跟进来,独自入了帐子。
在外秋狝一切从简,一个帐子并不大,一眼能将帐子外间拢共看尽。恪贵妃无力地伏倒在椅子上,撑着手边的高桌,半驼着背。她很少有这样失态的时候,加上这次,韫姜却已亲眼见着两回了。
恪贵妃磕破了头,因此额上勒着洁白的布条,那上头隐约透着血色。——看来恪贵妃伤的不轻。恪贵妃支起身子来,也没招呼韫姜,只叫千璎带人一道退出去。
韫姜在恪贵妃身旁的一把玫瑰椅上坐了,相对无言,谁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
良久,恪贵妃才开口,因为她高呼恕罪而伤了嗓子,导致她的声音变得低沉而嘶哑:“再阳没事了吧?”
“已经没事了,伤口虽长,但也不深,包扎好了就无碍了。”韫姜的声音也闷闷的,凝着一缕忧愁。顿了顿,她才说:“现下皇上还在生气,我说了他也不听。等日后有个好时机,我再说两句吧。”
“不必了。”恪贵妃摇头,因额头上隐隐作疼,一下又停了摇头的动作,“本宫去求情,不是想让勋儿回来,是希望皇上不要生他的气,不要误以为他是个狠毒的孩子。”她深深吸一口气,压住奔涌而出的泪意,“勋儿他也没什么错,就是性子……确实是我惯着的。”
韫姜同贵妃相处良久,从没见过她自责的样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到了孩子这,贵妃也不过是个母亲罢了。
“隔开了也不全是坏事,听君悦说,皇上正挑着几个御前的人,打算拨去照顾再勋的。御前的人最妥帖不过了,又是得皇上青眼才担这份重任的,你也不用担心。”韫姜迟疑着,将心比心,若是把再阳接走了,她只怕没有贵妃这份镇定。因此犹犹豫豫的,韫姜还是拉住了恪贵妃微凉的手。
两个人的手都是寒凉的,凑在一块反而焐出一点暖意来。恪贵妃神情微动,半响,也反握了握韫姜纤小的玉手,韫姜的手很小巧,虽则纤瘦但软若无骨,恪贵妃有些别扭和不大习惯,还是抽了出来。
出了帐子,愈宁将备好的披风给韫姜裹上了,韫姜带上风帽,吩咐道:“叫泷儿去问一问君悦,御前的人选好了没。再勋离了恪贵妃,又没有可靠的人看着,我怕叫人钻空子。”
“是。”愈宁护着韫姜往回走,一面问,“怎么样?”
“倒还好,没有本宫想的那么糟。恪贵妃看事情明白,也省了我许多口舌。”韫姜其实有些无奈,也有些可怜恪贵妃。
她拢住前襟:“苏姐姐、宛陵,都不在我身边了。倒是夫芫,吵吵闹闹、冷嘲热讽的,陪我到了现在。那时候也说不出什么,莫名地不爱和盛挽蕴亲近,就算她文文静静的,我也还是更喜欢夫芫一些。”她有些黯然地笑了,“其实夫芫挺好的,她有她自己的好处。事到如今,就算她成为皇后的机会更微茫了些,本宫也还是愿意同她一块儿。”……
帐子内,千璎奉了热茶进来,小心翼翼地劝道:“娘娘喝盏热茶暖暖身子吧,别累着了。”恪贵妃无助地看向千璎:“你再去问问江公公,皇上消气了没有?有没有还生勋儿的气?你去问问。”
千璎眼眶一红,咬住下唇,细声细气哎了一句,不顾天黑风大,立时就退了出去。千珊守在一旁,跪下来给恪贵妃捏腿,颤声道:“娘娘别担心这个了,四殿下是皇上的儿子,父亲是不会和儿子置气的。”
恪贵妃沉重地点了点头:“但愿如此。皇上气本宫也好,骂本宫也罢,本宫忍着。可是勋儿是不当心的,他……”
“没事儿的娘娘,德妃娘娘都不追究,这事儿很快就会过去的。皇上最顾念情分二字了,又宽仁大量。连盛妃这样的都容谅了,咱们殿下这点子事算什么呀。”千珊胡乱把泪抹了,一门心宽慰恪贵妃。
“韫姜……”恪贵妃垂下高傲的眼眸,“罢了,本宫不能自己先馁了,否则叫那起子小人看笑话。”她站起身,“准备沐浴吧,本宫不能垮了。”
出了这件事之后,日子平寂了几日。再阳养得当心,也没什么大碍,照旧活蹦乱跳的,不过韫姜怕他伤口恶化,还是拘着他,不让他这些日子再骑马。再枫知道再阳平日无聊,就每日过来陪着他说话,或者求了韫姜允准,出去逛逛散心,兄弟两个还是极要好的。
徽予也没真气到骨子里,第二天就心软了,亲自去看望了恪贵妃。但再勋回来的事他只字未提,约莫是下了决心的。恪贵妃听徽予话里已经没有对再勋的责备了,也就安了心,没有开口请求让再勋回来的话。
这边韫姜得知之后也宽慰了些,要是恪贵妃有事,她也得多费心。这样解决了,也是桩好事。
这日阳光明媚,韫姜本想出去散散,奈何这几日为再阳多处费心耗神的,闹得身上有些不爽利。不得已辜负了这晴好的天儿,只窝在帐子里头。
愈宁调了一盏甜口的奶茶来给韫姜喝,蒙古爱喝黑砖茶同盐同煮的咸奶茶,韫姜在宫里甜口的蜜茶喝得多了,一时不大习惯。于是央了愈宁将盐巴替成糖块,煮出来的倒也是另一番滋味。
她才捧着茶吃了几口,又觉甜腻,想吃点酸的来。泷儿在一边嗤嗤笑了:“娘娘的嘴巴是越来越刁了,吃甜的就要酸的来配,吃咸的就要辣的来配,愈宁姑姑慢些走,娘娘等会儿还不知要讨些什么呢。”
韫姜拿眼瞋她,伸手在泷儿腰上小劲拧了一把:“好你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在这儿编排本宫!”她笑靥如花,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反倒被逗得高兴,“去,你去给本宫拿,也不必劳烦姑姑了。”
泷儿咯咯笑个不住,躲去愈宁背后,俏皮道:“奴婢去就是了,且看小厨房有些什么,一应给娘娘拿来,好叫娘娘挑的。”她话说完,就旋身去了外头,才打起洒花幔帐,就听她一句:“晴昭容娘娘来了?”
韫姜探身往幔帐外看去,见是晴昭容神色有些沉重地站在外头。她漫开的笑意也便一收,问:“怎么了?你不是同公主她们看马去了么,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晴昭容欠身进来,琼如立在帐子外,悄悄儿把眼珠一转,泷儿就知会了她的意思,半侧过身示意愈宁将帐子中的人都带出来。
一众人出了帐子,愈宁问琼如:“可是有什么事儿了?”
琼如也不知如何说起,噎了一下,说:“确实有点儿岔子,奴婢不敢乱置喙,姑姑同姐姐且等一等吧。”
愈宁一下心里有了数,悄悄儿杵了泷儿一下,泷儿心里明白,等着愈宁和琼如去看茶的功夫,自己另去了他处。
帐子内,韫姜扶着晴昭容在垫了羊毛毯的软榻上坐了,自己挨着旁边的圆凳端坐好了,才问:“你可是有话要同我说?”
韫姜的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草药的清苦香气,混合着“兰生幽谷”的香气,蕴成韫姜独特的味道。晴昭容每次嗅到这股幽淡的香味,都会莫名的心安,她凝重的神情在不经意间松缓下来。
她徐徐从袖中取出一枚银针,展示给韫姜看,一面开口道:“这是我在二殿下所用的马鞍上找到的。”
韫姜却意外的没有惊诧或愠怒的表情,晴昭容迟疑了一下,继续说,“今日我得了皇上的允准,得以同公主们一道,去马场看一看马。因定城公主和绥安公主起了兴,想请我教她们骑大马。也是巧了,定城公主那匹大马的马鞍不称心,这样必是骑不安生的。臣妾斗胆,想起二殿下骑的马正巧同这一匹体量相近,加上二殿下最近养伤,也用不到马鞍了。我便先斩后奏,先使它一使,回来再同姐姐说项,姐姐哪有不允的呢?结果取了那马鞍出来,一开始倒也没事,但后来马渐渐的狂躁起来,我便立时叫人护了定城公主下来。再四下仔仔细细检查了,才发现马鞍后头被人放了银针,已经凸出了半个尖儿,扎在马背上,马才渐渐狂郁的。可幸定城公主身量苗条,体格轻盈,否则若是二殿下,又该怎样呢?”
韫姜捻着那银针一转,并不言语,晴昭容有些惑然,但仍旧徐徐说:“二皇子身量高,翻身上马的那一记下去,只怕就会叫马掀下来。他们骑得都是大马,力气也大,不过是平常驯得乖了,可若是真发起性来可不是玩的。”
“而且正如姐姐所见,这银针并不现眼,又细,藏在马鞍底下,一下也看不出端倪。只有马鞍上施压,一记刺在马背上,才会发作起来的。可见有人是想钻这个空子了,这几日殿下不骑马,马鞍的检查难免会疏漏些。”晴昭容扶着腰,挪了挪位置,“我知道后,不敢随意声张,在场的人也没几个,我都吩咐了不能多嘴。定城公主她们是明事理的,知道兹事体大,都各自装作不晓得的样子回去了。”
她一指那银针,继续道:“我已粗略查问过,这几日大殿下常陪着二殿下,也不曾去骑过马,只有四殿下偶或来练习骑射。”她平视向韫姜的双眸,“表面上看,被咱们发现之前,只有四殿下的人进过马鞍房,不过显然四殿下不会有这么狠毒的心意,那不就是恪贵妃娘娘吗?只可惜没有证据罢了。”
她见韫姜迟迟没有反应,有些愕然:“姐姐怎么不急,也不打算追究么?”
韫姜这才浅浅一笑,将银针往手旁一放:“这针是本宫吩咐人放的,听你一席话,看来若是旁人也都会这么想,那这场戏就做真了。”
晴昭容一时有些错愕,不曾想竟是这样,她默了片刻,才问:“姐姐为什么做这个?不怕伤着二皇子吗?”
韫姜微微一笑:“你以为,为什么定城想骑的马的马鞍偏偏不称心呢?”她的眼底沉淀着深不可测的城府,“诚如你所说,表面上一查,就像是恪贵妃做的事。而且她也完全有理由,那就是因为出了阳儿这档子事,才导致恪贵妃母子分离。依照恪贵妃的性子,做出这种事也不稀奇。但是这样明显,反而刻意了。宫里的事么,本来就是一团浆糊,说也说不清,就看疑影兜在谁头上罢了。”
她的声音很绵柔,说话又慢条斯理的,让晴昭容有些猜不透她的用意:“这……姐姐难道是和恪贵妃娘娘联合做了一个局么?”
“现在正是微妙的关头,恪贵妃同四殿下的事,若是旁人有心,拿来宣发一下,就没法真正过去。与其等别人的出其不意,不如自己先办了。”韫姜支颐,沉静道,“你别看这几日风平浪静的,其实难呢。”
晴昭容这才慢慢懂了些,喃喃道:“想必姐姐说的是盛妃娘娘,她现在孤立无援,门下羽翼又不够丰满,单凭一己之力和姐姐、恪贵妃抗衡本就吃力,加上她如今恩宠不足,位份不高,愈发落入下风。可要是恪贵妃娘娘同样不济了,与她而言也是大有裨益。所以……闹出来,反而更像是盛妃娘娘的手笔。”
“你明白就好。”韫姜抬眼见愈宁进来奉茶,于是招呼晴昭容吃茶润润喉。等了等,晴昭容迟疑着,仿佛有些担心:“可是这件事终究是往恪贵妃娘娘身上泼脏水的,万一恪贵妃娘娘脱不了嫌疑……”
“不会的。”韫姜把眼一眯,盯住晴昭容,“这个你自然不必担心。到时候,你看见了什么,知道了什么,如实说就好,不必为了恪贵妃而隐瞒些什么。”
晴昭容眼珠子一转,心里掂量了一下,韫姜没有提前告知,想必没有自己,这场戏也能演下去,或许连定城公主都不一定知情。她细细想了,当时就是千珊在一旁若有若无地点拨了一句,她才想到再阳的马鞍这事儿上,一切行云流水下来,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她沉了口气,望着韫姜的眼睛:“姐姐信我么?”
韫姜笑了:“不信你,何必巴巴儿跟你说这么多?——好了,茶也吃了,该把这事儿闹出来了。”
她二人出了帐子,才往徽予的帐子去,路上果不其然遇着了盛妃,泷儿不知何时悄无声息地回了帐子,现如今跟在韫姜身后,仿佛从没离开过。
婵杏听见了风声,不敢耽搁,立时将消息递给了盛妃。这事儿既然不是盛妃自己做的,她岂能不来盯着,谨防她们将脏水泼给自己?
“姐姐同晴妹妹要往皇上那去?”盛妃装作不知情的样子,懵然问韫姜她们。
韫姜沉着一张脸,将盛妃上下审视了一通,犹豫片刻,温温道:“是了,盛妃妹妹同去吧,有桩事,或许妹妹知道。”
盛妃眼神一动,心里也计算起来,顿了顿,她才道:“不知是什么事,姐姐大可问过妹妹,何必去皇上那儿呢?”
韫姜浅浅一笑:“还说不准呢,得到皇上那分说明白了才好,妹妹还是不要推辞了,否则一会儿御前的人来请,也是麻烦。”
盛妃眼帘一垂,七窍玲-珑心里早想过千百个念头,脸上还是文文静静的笑容:“那便跟着姐姐同去就是了。”
三人一同到了徽予的御帐子,恰好前脚商议国事的王公才走,徽予正有空暇。三人便请了通报,一道入内去。
帐内的徽予才吃了茶小憩片刻,未料三人同时过来,下意识觉着必有大事,于是默然叫人看座。三人过来请了安后彼此坐好了,晴昭容适才率先开口,先把银针呈上,再将马场的事又详尽说了一通。随着她慢慢叙述,韫姜适时红了眼眶,装出又怒又怕的模样来。
果然一通话说罢,徽予的脸色也阴了大半。
韫姜紧跟着开口:“臣妾实在不知道阳儿是碍着谁的眼了,要受这样的算计。若没有今日晴昭容的误打误撞,阳儿还不知道会怎样……”她掉下两颗泪来,啪嗒掉在手背上,也刺在徽予心里。
晴昭容明艳的脸上也是一扫晴空、尽是阴霾:“臣妾年纪轻,没有经历过事,吓得不成。也没敢立时声张开来,只得先找了德妃娘娘,再来报的皇上。”她绞着帕子,“臣妾问过马厩的人了,也没问出什么来,说这几天除了四殿下偶尔骑马,也没别的人了……”
韫姜一蹙眉,沉默着没有开口。盛妃见她沉思,于是斗胆开口:“晴昭容说这话,难不成是疑虑是恪贵妃娘娘所为么?”
晴昭容一吓,瞪大了眼:“臣妾也没这个意思,实话实说罢了。”她讪讪道,“这恪贵妃娘娘才同四殿下两下分别了,也碰不着四殿下,怎么能借四殿下做这个事儿呢?难不成恪贵妃娘娘能收买御前的人?怎么想都是不能的,御前的人规矩最严了,是皇上调教出来的人,怎么会做这样的事。”
徽予他多瞧了两眼盛妃,心里也暗自思索起来。现在再勋身边的都是御前的人,照例连骑马一例事也都是他们跟着伺候,但专司马厩房的奴才,不知是不是恪贵妃的人。但这样,也未免太瓜田李下了。
“本宫不过一说罢了。”盛妃还是气定神闲的样子,但心里知道,既然不是恪贵妃,那不就是自己么?
晴昭容打量着徽予的脸色,小声说:“……那个时候,定城公主和千珊也在,若是恪贵妃做的,千珊怎么会不拦着我呢?”
盛妃迟疑了一下,微笑道:“不过若是要拦着,未免太‘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吧?照例昭容你做主就是了,千珊一个奴才能置喙什么?”
韫姜一咬唇,没有搭腔,只是颤着声音,“皇上,还是请恪贵妃过来吧。”
徽予一扬手,江鹤立时疾步退了出去。这档口,盛妃不忘悄悄儿打量韫姜的神情,小声道:“姐姐也别伤心了,也是殿下有福气,才躲过了这一劫数。”
正是微妙的档口,恪贵妃带着人来了,徽予叫她免礼,又将银针递交给她,命江鹤将事情讲了个大概。一通话讲完,恪贵妃把脸一冷,睨向盛妃:“臣妾没有做这件事。”
盛妃没有急着回应恪贵妃狠辣的眼神,只默然端坐着,听恪贵妃继续说:“若是臣妾做的,怎么也不舍得让定城涉险才是,纵然如江公公说的,定城体态轻盈,没有酿成大祸。可事情总有万一,臣妾怎么舍得自己的女儿?现如今臣妾身边只有定城和寿城了,所以是拿一百二十个心去照顾她们。因此定城去看马,臣妾才特地嘱咐了掌事宫女千珊跟着。若真是臣妾做的,千珊怎么也该知道,怎么会不劝着?”
听恪贵妃这样辩驳,盛妃将适才的反驳之语又说了一通,恪贵妃冷笑道:“朝阳宫做事,必得把事做绝了。若本宫有心要害二皇子,这马都不会让定城去看,以免出岔子。否则不就会像这样,出这样难以预料的纰漏么?不禁功亏一篑,还惹一身臊。”
面对恪贵妃的驳斥,盛妃单是付之一笑,娴静道:“姐姐别恼,不过就事论事罢了,说明白了就是了。”
残害皇子,绝不是简单靠嘴皮子功夫就能敷衍过去的,徽予适时开口:“这桩事,朕已经知道了大概了,诸人的说辞,朕也都听了。既然各执一词,那便查下去。”他朝向恪贵妃,没有说下去。
恪贵妃心里有数,起身福礼:“臣妾问心无愧,但凭皇上查证。” 皇上他雨露不均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