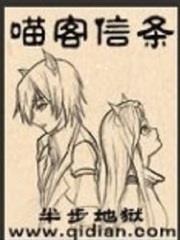立政殿别院中,三公主闷闷不乐,只呆呆瞧着窗外,不时轻叹一声,也没个人劝诫,也不听谁宽慰,就叫她呆呆守了一早。直到日上三竿,才有采女急匆匆赶来,小心道:“启禀公主,吴少卿往寺中去了,怕是不会来了……”
三公主闻言点头,温和道:“他刚回京中,自有万千琐事缠身,太常寺失了寺卿,自要他辛苦许多。我想见他,又不欲他来,只不愿耽搁了他的要事。李妈妈可曾好些?”
那采女听她体恤,便觉心中一暖,柔声道:“有公主牵挂着,李妈妈自是一日好似一日。始终她上了年纪,惊吓过度,又受风寒,许还得养些日子,尚不能服侍公主。”
点了点头,三公主也是叹气。她这几日为吴景辰操心,苦闷得紧,偏生一直陪伴照顾的李妈妈又受了风寒,重病卧床,不能服侍在旁,再没人能与她说说心事。一应宫娥采女们自是体贴,无微不至,却不比得李妈妈那般处处为她着想,她也不好与她们多说心事,这才愈发烦闷,也不知如何是好。
不多时,耳听宫人通禀,就见武后大步走进别院,瞧见三公主一脸愁容,无奈道:“我儿又生相思!”
公主见她,自是连忙施礼问安,却不敢多说什么,便觉着这几日来,武后的脾气愈发难以揣摩,虽然对自己疼爱一如往昔,却不再像从前那样亲近,叫她多少有些敬畏。她最是善解人意,晓得自皇帝病重以来,武后以一己之力,撑起前朝大事,着实不易,情有可原,才多有体谅,尽量不惹她心烦。
见她乖巧可怜,武后便愈发疼惜,才道:“吴景辰平安归来,你原该宽心才是。是了,你助他一臂之力,他尚不曾来谢恩,确有些不懂规矩,待我提醒他就是。”
三公主应了一声,轻声道:“多谢母后挂心。少卿公务繁忙,我自晓得,只要他平安归来,我便心满意足,不求其他。”
武后瞧她痴情,便道:“太常卿之位久缺,我已命吴景辰递补。现如今他官居三品,难免奔波。我儿体谅,自是他的福分,他年纪尚轻,还需要多多历练。”
三公主闻言点头,自为他高兴,却也隐隐觉得担忧。始终吴景辰再有本事,也不过是个十六七的少年,凭借大衍宗出身,做上少卿,已经十分勉强;现如今他出任九寺之首,就不知别人如何看他,诸事繁杂,也不知他能否兼顾。
吴景辰眼下自是焦头烂额,太常寺那一堆琐事就够他操心许久。然而太常卿莫名获罪,始终叫他觉得心中不安,这才急着赶往刑部,吩咐常如牵马,却听他道:“师兄稍安勿躁,刑部大狱原非轻易去得。太常寺虽为九寺之首,却管不到六部之事。事关刑狱,原该与大理卿先行商量。”
此言一出,吴景辰才恍然大悟,也不是他不知朝中规矩,实在是今日事多,搅得他心神不宁,一时失了镇定,才道:“如此,便先往大理寺去。京官过失,原归大理卿一手把握。”
常如领命,服侍他上马,好言劝道:“师兄才经舟车劳顿,又为京中诸事烦恼,本不需这般急切。太常卿虽获罪入狱,始终不曾过堂受审,自有他家人奔波运作,不会叫他在牢中吃了苦头。更何况他三品之尊,大理寺也不敢怠慢,师兄还需保重自身才是。”
他这话说得体贴,吴景辰却是摇头,道:“事有蹊跷,拖延原无益处。及早探明,免得夜长梦多。”
两人说着话,就听得路上喧闹非常,才瞧着几队府兵横冲直撞,在街坊间奔走喝骂,浑不顾良家商家,围住了一句话不问,推门就搜,惹得民怨沸腾,叫城中百姓侧目。
吴景辰见状皱眉,暗想自己到长安不过数月,却也见识了城中安宁,从不见府兵欺压百姓,便不知出了何等大事,京兆尹才能许他们这般胡来。寺府各司其职,他也无法干涉这些府兵蛮横,瞧了片刻,便也摇头要走,却见得一人发足狂奔,朝着自己冲来。
还不等他开口,那人就急切喊道:“师兄,不得了了!大理卿与京兆尹一道,领兵围住了大衍府,说是要搜查人犯,请师兄速归!”
吴景辰心中一震,暗叫不好,一念衍生,离在震上,火雷噬嗑,应在上九灭耳凶爻,竟是刑狱负枷之象,便晓得崔华霍遭了劫数,恐犯牢狱之灾,忙连声道:“速速回府,崔寺丞恐有大难!”
常如闻言,不敢怠慢,这就脚下生风,直追骏马,与吴景辰一道朝府中赶去,只叫街上行人比之唯恐不及,一个个慌忙逃窜,也不顾得这许多,就晓得出了大事。
大衍府外,果见兵丁林立,团团包围,隔着一道门墙,与府中弟子对峙,气氛剑拔弩张。大衍府乃是太宗皇帝钦赐,大衍宗立足世俗所在,虽在京中,却如世外桃源一般,自有威严,原不是谁想搜就搜,想查就查;吴景辰与常如不在,众弟子自不能让兵丁擅闯,这才把住了门墙,不许任何人出入。
吴景辰升任太常卿一时,大理卿和京兆尹已然晓得,自不敢放肆冒犯,便也不曾下令硬闯,只叫他府中人请他速归,两人脸上都是一副凝重神情。
不多时,吴景辰策马狂奔而来,只见这般阵仗,便知出了大事,这才快步走到大理卿面前,急切道:“崔寺丞何在?”
大理卿闻言一愣,随即恍然,才道:“太常卿神机妙算,下官正要请教!崔华霍涉险杀妻潜逃,请寺卿放开府门,让下官搜拿人犯!”
闻听此言,他便觉得天旋地转,勉强站定,才与常如对了眼色,晓得府中并无外人,便挥手叫众弟子让开,任凭府兵一拥而入,自与大理卿道:“大衍府任你搜查,你却将事情细细说来!崔寺丞决不致杀妻潜逃!”
几人进得府中,耳听着府兵叫嚷,才见大理卿抱拳拱手,道:“寺卿稍安勿躁,容下官细细秉来。”
原来昨夜两人分别之后,崔华霍自顾返家。他家婆娘恨他一走月余,杳无音讯,不晓得寄封家书回来,浑不顾家中如何,便是怒极;才见他进门,那悍妇就叫骂不休,与他着实争执了一番,摔打吵嚷,一闹闹到了二更天。
他家两口子不吵不过日子,左邻右舍早已习惯,只隔着墙骂了几声,也没往心里去。谁承想今早日上三竿,他家里毫无动静,安静得不同寻常,才叫好事的邻居生疑,叫门不应,这才小心进去。
邻居一进门,便见他家中乱作一片,地上满是鲜血,家奴倒毙院中,他婆娘被一刀插在心口,死在了前厅。那邻居双腿发软,一屁股瘫坐血泊之中,缓了半天,才放声尖叫起来,已然被吓得半死。
出了人命案子,自然惊动地方。府衙前来勘验,见他一家五口皆被砍杀,独不见崔华霍身影,才晓得事情不对,不敢怠慢,这就报到了大理寺中。凶杀人命,崔华霍不知所踪,自然嫌疑最大,才叫大理卿急急招来京兆尹,闭锁城门,全城搜捕。
吴景辰听到此处,悲愤交加,怒道:“崔寺丞分明是遭陷害!你身为大理卿,这等伎俩都瞧不清楚么!”
大理卿晓得他俩亲近,不敢激怒,才小心道:“寺卿所言极是,下官自也晓得。崔华霍为人耿直,又最忠厚,在寺中一向安稳。说他自灭满门,下官绝不相信,可如今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什么死不见尸!崔寺丞还活着!”
抹一把冷汗,大理卿愈发加了小心,低声道:“是,崔华霍自然无恙,却不知身在何方。他家里出了人命,他却凭空消失,于情于理,下官总要将他找到,过堂审了,才能理清此案。寺卿信他,我也信他,可王法如此,他总要显身,说清案由才是。”
吴景辰只觉得胸口发闷,几乎喘不上气来,也晓得大理卿所言不错,就觉得此事蹊跷非常。崔华霍摆明是遭了他人陷害,却不知他如今身在何方,若他真平安无事,即便内有苦衷,不能向大理寺说明情由,也该来大衍府求助才是,断不该隐匿行踪,人间蒸发。
常如见他情绪激动,这便奉上茶水给他凝神,道:“师兄莫急,凡事总有个因果。与其跟两位老爷争执,倒不如静下心来,先卜定崔寺丞平安才好。”
两口茶压住心火,吴景辰这才勉强冷静下来,道:“理当如此。取蓍草来。”
大理卿和京兆尹不懂,常如却知道他着实担心。陈远道上窥天道,把握因缘际会,念头一起,便知过去未来;吴景辰没有这样的本事,却也能心念空灵,窥视因果,卜算吉凶祸福。如今他心乱如麻,失却空灵之念,不得以借助外物,对他这等人物来说,实属罕见。
不多时,沙盘蓍草奉上,众人瞧着他眉头紧缩,摆弄半天,心下紧张好奇,却不敢出言发问,等得焦急,才听他沙哑道:“崔寺丞尚未应劫,性命无碍,只见了困相。”
众人松一口气,大理卿这才舒展了眼眉。如果崔华霍真是凶手,他作为上官也难辞其咎,大理寺中出了灭门歹徒,他这大理寺卿便也做到头了。呼一口气,他才小心道:“那凶手是?”
满堂安静,就等吴景辰道破天机。他却半天不肯开口,紧咬牙关,只一滴豆大眼泪,坠在沙盘之中。 少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