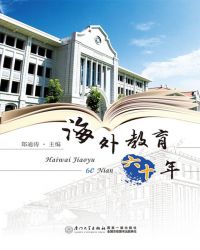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海外教育六十年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三、译词的基督教化
对于理雅各译本的另一重要批评则是认为其传教士的身份影响了他对孔子思想的解读,“理译儒经,反映的是西人的观点,对中国典籍必多曲解附会”。它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理雅各传教士的身份是无疑,其译文中确实也存在基督教气息的字句,比如对其最多批评的以“Heaven”译“天”,以及以“God”译“帝”。这类批评来自中西两方,有趣之处是,现代的中国研究者批评其文化中心主义,而与理雅各同时期的西方批评者则批评他对东方文化的平等主义。
在理雅各所处的时代,对大多数传教士而言,中国人是异教徒和下等民族,他们不可能有God。而且如果“找到基督教的上帝的可能性,竟然早已呈现在中国经典文本当中,这无疑威胁到传统笃信福音的传教神学的绝对排他性”。因此,理雅各的观点和行为也使其时刻处于教会及各种保守传教士的明枪暗箭之中,而他从传教士向学者身份的转变也与此有一定关系。时至今日,一些中国研究者则仍然习惯性地补上一刀,比如有研究者如此批评理雅各用“Heaven”一词译《论语》中的“天”:“实际上就是西方殖民者用其语言对被殖民地的改写,是赤裸裸的东方主义。这一例子再一次证明了理雅各的文化身份——他毕竟是一个由伦敦会派到大英帝国在香港的殖民地的传教士,他从未忘记过自己的身份和使命。”虽然我们不否认理雅各翻译中的宗教倾向,但如此概念化地批评似乎太过简单。就《论语》的关键词翻译来看,所谓基督教化的译词仍然是少数,如他用“sage”而非“Saint”翻译“圣人”;用“mean man”而非“sinner”翻译“小人”,又如用“the rules of propriety”翻译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的“礼”。
对“礼之用,和为贵”一句,理雅各在注释中言,“礼很难翻译成任何一种语言。它含‘合适’之义,是‘事之宜’,它施行于人与人之间,但同时符合最高存在者(superior beings)的要求。在此,它与我们的‘ceremonies’一词意义相近”。在正文中,理雅各并未选用“ceremonies”翻译“礼”,而是选择“the rules of propriety”,“propriety”意为“符合道德及社会规范的行为,正确恰当的状态,或良好社会行为之规则”。而很多译者则选择“rite”或“ritual”,如白妙子译为“ritual”,安乐哲译为“ritual propriety(li礼)”,许渊冲译为“the rites”。“rite”意为“宗教性仪式之一种”;“ritual”除做形容词外,名词意为“一系列重复的仪式”。因此,理雅各的选词无疑是最不宗教化的。虽然他在注释中提到的最高存在者(superior beings)暗含God之意,但这里他并未让God出场,这也与他一直被批评的努力“基督教化《论语》”的形象不符合。
我们再看其最具宗教化的“帝”与“天”在《论语》译本中的呈现。
“帝”是《尚书》中多次出现的汉字,但在《论语》中只出现在最后一篇《尧曰》的祈祷词中。这是理雅各《论语》译文中最具宗教气息的一段,我们可以将其与安乐哲的译文对照阅读。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理译:I, the child Li, presume to use a dark—coloured victim, and presume to announce to Thee. O most great and sovereign God, that the sinner I dare not pardon, and thy ministers, O God, I do not keep in obscurity. The examination of them is by thy mind, O God. If, in my person, I commit offences, they are not to be attributed to you, the people of the myriad regions.
安译:I, Lu, dare to humbly offer in sacrifice a black bull, and dare to call upon the August High Ancestor. Those who do wrong will not be pardoned. I will not shield your subjects from your sight, but will let all decisions rest with you. If I, your subject, personally do wrong, let not the many states be implicated; if any of the many states do wrong, the guilt lies with me personally.
相比较而言,无论从句式或醒目的“O God”“O most great and sovereign God”的用词,理译确实像一位牧师在虔诚地祈祷。在注释中,理雅各谈到,要明白他为何将“帝”翻译为“God”,可以阅读他的著作《中国人关于上帝和灵魂的观念》(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1852)在这本书中,理雅各试图从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读中找到超越的、精神的存在,并认为“中国人认识真正的上帝,他们所崇拜的最高存有,与我们所崇拜的是同一实体。”此后,他又书写了《中国宗教:与基督教比较视野下地儒教和道教》(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 1880)。这些著作都是在说明早期中国文化中有作为精神的上帝的存在。正如穆勒在1870年《关于宗教科学的演讲》中提到的:“如果我们凝视那些中国人的眼睛,我们就会发现,在那里同样能够看到一个心灵对另一个心灵的反应,还有他们所说的上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无论他们在表述上显得多么无助,也不管他们在崇拜方面显得多么不完美。”这无疑也是理雅各的观念。
理雅各的这些研究及其所持有的理念自然会影响到他对《论语》的解读,但同时,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型译者,他秉承的仍然是尽量客观的态度以及对异文化的尊重。这也是唯一一次在一段中呈现出明显基督教气息的译文。
理雅各对帝(God)的解读其实是和其对“天”(Heaven)的解读紧密相连的。相对于仅出现在最后一节的“帝”,被译为大写的“Heaven”的“天”则分散出现在《论语》各节中,共16处。第一次出现在“五十而知天命”(2.4)中,理雅各将“天命”译为“the decrees of Heaven”。在注释中,他则直接翻译了朱子的注疏:“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the decrees of Heaven=the things decreed by Heaven, the constitution of things making what was proper to be so.)
单独的“天”字第一次出现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3.13)理雅各在此节的注释中用了大量篇幅谈“天”。首先,他提到朱熹所注的“天即理也”,随后说,“如果没有智与义的最高主宰的本然认识,如何能言天即理呢?”随后,他又引用了《四书拓余说》对“天”作为“高高在上者”的解释。
通过以上理雅各在注释中对作为“Heaven”的“天”的解释,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他将西方的“Heaven”与东方哲学中的“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个“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就是朱熹所言之“理”。对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来说,西方的“Heaven”只是一个想象中的精神性处所,但从思想的路径上看,它也是一种人类对终极世界的追问,而在这一意义上,不管“Heaven”和“理”之间是如何千差万别,它们在这里还是拥有了共同点。同时,作为“智与义的最高主宰”的“上帝”也暂时剥离了其作为人格神的身份,而等同于更为抽象的“天”。理雅各曾说,“中国人所使用的‘天’,基本上与英国人所使用的天堂是一样的,意思都是指‘上帝’(God)”。这里的理雅各看似在以西方的概念来释“天”,但同时,他也在以中国的“天”与“理”在解释“God”和“Heaven”。这种双向的诠释很难被称为以某一种主义(或文化)来归化另一种主义(或文化),它更多的还是在努力寻找两种文化实现彼此理解的交点。
理雅各除了在关键词的翻译和理解中展示其文化态度外,他极具特色的注释也是其处理文化问题的重要方式。理雅各译文的一大特点即其附上了篇幅超过正文的详尽注释。这种方式非常像中国的注疏传统,而他则将这种翻译定义为“学术型翻译” (scholarly translation)。他在1867年说到,“作为一个勤勉的译者就必须努力地工作,仿佛他只是在为第一百个读者而工作似的,因为只有这个读者才会去关注学术上那些需要小心应对处理的技术细节(此外的99个读者并不关注那些批评性的注释)”。
这些注释中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既有对某个汉字从读音到意义的解释,也有对各家注疏的介绍。除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仅在《学而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诸如何晏《论语注疏解经序》(释论语二字)、阮元编《皇清经解》(对1.1中“亦”之解释)、毛奇龄之《四书改错》(1.4中释“传不习”)、王引之《经传释词》(1.10)等数部典籍。这种研究方法自身无疑已是对其异文化——中国经学学术传统的尊重和学习。
此外,在其注释中,理雅各也适时地为某些可能造成西方人误解的语句做出说明。如对“无友不如己者”(1.8),理氏特意辩白道:“对中国的道学家而言,交友有增进自身知识及道德之目的,因为这并非一句鼓励人自私的格言。”这也是对朱子“友所以辅仁”一句的发挥。在“三年无改于父之道”(1.11)一节,他也解释了“三年”及“父之道”,他说:“这里的父之道不是太糟糕的道。旧说三年为三年之丧,今日这一观点则被推翻,三年并非限定于这段时间。”这些解释无疑都展示了他在尊重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自身都是理解他人的起点,但“没有对话的才能,没有进入另一个人心灵世界的才能,说明——因此也是诠释学——是不可能的。”从传教士到学者身份转化的理雅各,也是从自身出发、通过对话、理解他者的理雅各。有些研究者也认为理雅各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和翻译,“他获得了理解孔子和中国传统的一种方法和一种新道德。这是超出了理雅各1861年所规划的那种(对待中国经典的)冷酷直面的态度与立场的。确实,理雅各1873年的华北之旅,昭示出他依据开始通过那位中国圣人朝向德性与智慧的追求的同情,来修正自己对于这位圣人的理解,并以此照亮他自己的生活”。 海外教育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