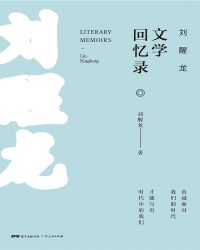第18节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18节·
曾经预告,引起父亲对我的小说由批评到表扬的变化之缘故,还有一个,但需要一篇长文才说得清。后来,我不止一次写过,也很多次公开说过。
1986年11月中旬,在大别山腹地的红安县城,听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冯康男先生的讲座。过程中,这位饱经风霜的长者,朗诵了一首短诗:
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
在场的有来自全黄冈地区的近二百名业余作者。后来的日子里,当我重复提及这首名叫《一碗油盐饭》的小诗时,那些曾经与我一同听过的人,莫不是一脸茫然,丝毫不记得曾经有过此事。就连冯康男先生本人也健忘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电话聊天,提及这事时,他满是狐疑地反问,自己是不是真的这么朗诵了?1986年秋天那一次,听冯康男先生即兴朗诵完这首小诗后,难以克制的泪水竟然在自己的脸上肆意横流。
多年之后,因为不断转述,导致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写信来,说这首诗是他写的。我一直在克制着不理睬,不去放大内心深处的愤怒。2002年的夏天,荒谬又重新出现,一位男子不仅写信,还千方百计地打来电话,说这首诗是自己上小学时写的。巧的是这位男子也是红安人,我终于发现再不愤怒不行了,在一番厉声斥责之后,还狠狠地摔了家里的电话。家里人从未见我对外面的人发这么大火,若不是夫人抱着才两岁的女儿过来提醒,我可能会生更大的气,发更大的火。稍后几天,对方的家人悄悄打来电话,替他道歉,说他最近受到别人压迫,心情不好,并请求我原谅。曾经以来,总在说,自己不晓得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写诗的女孩我没见过,传诵此诗的长者却熟识她。写诗的女孩名叫黛妹,生长在鄂西长阳县的美轮美奂的清江边。黛妹只活了短短的十八年,因为一场凄凉的爱情,而导致神情恍惚,在一场车祸中回归永生。在长阳如果有人无意中见到某处小小的墓碑前,摆着一束新艳的野花,那一定是黛妹的安息处。为了纪念,当地文学爱好者出资为黛妹修建了这座小小的墓碑。也成了传诵者的我,在浠水县的一次文学创作会议上头一回说起这首诗时,在县文化馆看门的一位老人,失控地就在街边放声大哭,泪水流得比所有人都多。
在没有这首就叫《一碗油盐饭》的诗时,看油菜花,就能早早闻到那浓酽的菜油香。有了这首名叫《一碗油盐饭》的诗后,油菜花一开,依然可以早早闻到浓酽的菜油香,同时,还能感到一种诗一样的痛苦。2004年3月底,应法国方面邀请去巴黎,参加法中文化年中国文学周活动,在一个关于乡村文学的讲座上,我再次讲到这首诗。在新艳的时尚之都,陈年的乡土同样难以抵抗。站在讲台上,看得见一行行泪水,在异国的人们脸上清晰地流淌。演讲结束后,担任同声翻译的那位加拿大老人,一定要我将那首诗用汉语写下来,他要好好收藏。加拿大老人曾经为已故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当过同声翻译。在这首诗面前,他说,自己哽咽着几乎翻译不下去了。这种痛苦,也是诗一样的痛苦。
日常人生中,时常会有某种尴尬出现。在某些场合,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不甚合适,某个与他最亲近的人往往会装作不经意咳嗽一声,给这个人以善意提醒。写作是很个人化的,各个方面是否合适,往往也是需要最理解的人给予适当的提醒。我从不羡慕我的同行一次次从欧美文学大师那里得到点化,也从不妒忌他们信口就来滔滔不绝地引用欧美文学中的名篇名句,更不会强迫自己吃两颗安眠药以化解飞机恐惧症从而不时去到世界某地以显示自己也是世界性作家。文学这东西好就好在充分尊重每个人的造化,让那种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小地方的人也能将其价值极大化。能从前辈大师或者当代名家中得到启示,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那种主要得益于身边人事的方式,不仅省心省力,也更加有趣味、有活力。后来的经历证明,当初冯康男老师朗诵《一碗油盐饭》,正是于乱纷纷人世中,专门针对我的一声咳嗽。这样的咳嗽,别人听见了也不会在意,更听不懂。在当时,我也是似懂非懂。我注意到了,不仅注意到了,还惊讶自己为何被感动得如同重回少年?直到几年后,自己忽然一改行文风格,同样写山里,同样写水边,虽然没有达到物是人非地步,也没有差异到天壤之别,从《大别山之迷》到《村支书》《凤凰琴》,这中间的区隔还是足够巨大的。
2006年元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圣天门口》研讨会上,陈思和教授在发言中谈及自己当年如何读显克维支的《你往何处去》,再谈到自己现在如何读《圣天门口》。研讨会刚刚结束,《文学报》评论部主任朱小如就感慨地和我说,陈思和到底是陈思和,所说的就是导师的话,与学生辈的那些人不一样。也许别人还不懂陈思和谈刘醒龙,为何要扯得天高地远,先说显克微支。朱小如说他是懂了,也只有他才懂得,陈思和这是在教别人如何进入刘醒龙的小说世界,如何才能读懂《圣天门口》。一般俗手光顾着定调子,下结论,以凸显自己独领风骚。真正的高人才不会这样,反而只是谈方法。方法对了,路走对了,自然会有正确的结果。反之,只会是风马牛不相及,不是张冠李戴,就是李代桃僵。再说浅俗点,也就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很显然,冯康男先生的一番话,让我发现了与众不同的自己。
1995年4月,去杭州,《江南》杂志将那一年的文学奖颁给了我的中篇小说《白菜萝卜》。期间有去金华的活动,在火车上,与谢冕先生谈到《一碗油盐饭》,老先生听后完全无动于衷。这应了那句话:一个人的经典!那些只能作为一个人的经典的作品,关键不是不好,也不是与别人在审美判断上存有巨大差异。那些只能作为一个人的经典的作品,从本质上看,所显示的意义,往往是如何拨云见日的方法。在我这里,后来的写作让自己一直遵循一条规律,但凡能够写得简洁明了的小说,一定不要弄得神龙见首不见尾,但凡能够用朴素形式来表现的文本,就一定要做到质本洁来还洁去。《一碗油盐饭》就是那条蜿蜒在莽莽群山中的小路,大多数人未必会有机会从这里经过,凡是必须要经过的,则要走对才行,不然就出不了高山大壑。将某些看上去很深奥前沿的写作,放到这条小路上一测试,就会发现原来是满肚子牢骚无处发泄,满脑子欲望膨胀得比挂着广告条幅的气球还要大,说是文学塑造,实际上是自己将自己弄得不像人形。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