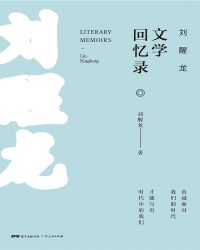第4节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4节·
因为父亲工作调来调去的缘故,小时候我上过不少的学校。不过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还是贺家桥中心小学。“红卫兵运动”后期这所小学改名为温泉中学。在我读完初中不久,它又在当时的体制之下被改为板桥大队小学。听人说,前两年差一点儿被撤,幸得一位在国内证券很有业绩的同学慷慨捐赠,这所已经严重退化的学校才得以保存下来。与校园平摆着有一个比较大的塆叫河西塆。两者相距大约一里路。据说,河西塆原先风水极好,塆后背靠虎头一样小山,小山的两翼又伸展出两条山岗,恰似猛虎添翼。塆前面有一口好大的水塘,水塘两边各有一只长年不干的甜水井,名副其实地是虎嘴和虎眼睛。在先人留下来的传说中,河西塆是典型风水宝地。贺家桥是个小镇,隔着河与河西塆遥遥相对。地相先生曾经说,河西塆是只吊睛白额虎,迟早要将贺家桥吃掉。相对于河西塆,住在贺家桥的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没头没脸的也是个精明刁钻的生意人。他们买通地相先生,反说河西塆在虎口之中,地脉极坏。哄得河西塆人听信了地相先生的话,填了一眼井,使老虎瞎了一只眼,又在河上修了一座桥,像箭搭在弓上一样威慑着老虎。贺家桥与河西塆虽然自此以后相安无事,却也没能干成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养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人物。贺家桥最辉煌的历史也不过是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做了一阵鄂豫皖苏区红山中心县委所在地。
小时候上学,先经过河上那座桥,再顺路直朝河西塆奔去,到临近塆前的水塘时,小路忽然一扭身,强迫我们转个90°大急弯,折向校园。实际上这路是河西塆的,不是学校的。到学校去,本应有另外一条路。过桥后,走上几十步远,便有一道田埂,直通到学校操场边。若道路顺田埂而去,至少要省去河西塆那条弯路的三分之二。所以,大约从学校建立之日起,所有的学生,包括老师,都有过铤而走险的经历,从田埂上抄近路,走捷径上学或回家。田埂很窄,一到春耕,农民就在上面辛辛苦苦地种上绿豆或黄豆。凭着现在一个成年人的良心起誓,我们当时绝没有破坏“革命生产”的念头。我们只是不想走弯路。田埂很窄,经不起几回踩,那些绿豆黄豆,年年的收成都没有播下的种子多。到了冬天,田里不再有水,如果不种麦子或油菜,一定会种上紫云英。虽然从来没有人故意去踏去踩,因为失足的缘故,沿田埂两米多宽的庄稼,年年都会葬身于师生们的脚底。
河西塆是一个生产队。当年的生产队长是个五十岁来岁的男人,厚厚的头发不肯留着,剃了一个光头,晒得黑黑红红的。不管天晴天阴,下雨下雪,从不见他戴过帽子。在我的印象中,他终日扛着一柄锄头,在学校门前的田畈中转来转去,不时能听到他冲着田里劳作的某人大骂:“你这个四类分子,今天不把这块田搞完,晚上开会专你的政!”他见我们在田埂上像野马一样飞跑,也大声叫骂着,说要将我们抓起来,送到学校里划一个小四类分子,但生产队长只是干打雷,不下雨,从没见他真的撵上来抓我们。即便真撵,也只是将我们撵到路上便作罢。
大约是在我上五年级的时候,从不戴帽子的队长,被派驻生产队的工作组撤职,戴上一顶坏分子的帽子,原因是他勾结四类分子暗地里私分生产队里的粮食。其实,是他见到四类分子们饿得可怜,将队里准备给养猪场当饲料的红薯蒂和没有长成形的红薯根,分给了他们。生产队长被撤职后,工作组的人自己管起生产队里的事,也是到处吆喝叫骂,却是戴着白草帽,穿着白衬衣,裤腿挽得老高,露出的双腿也比生产队的姑娘的脖子白嫩几分。工作组的人对付我们这些抄近路的学生,是动了真格。我是撞在这只枪口上的第一只猎物。
那天,我不知道河西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过桥后,脚一沾上田埂,便飞快地跑起来。突然之间有人冲着我大吼一声。尽管我跑得像风一样,最终却被黄豆禾绊倒在田里,像泥猴一样被撵上来的工作组的人抓住。工作组的人押着我走进校长办公室,并唤来班主任,少先队中队长、大队长等人。工作组的人在狠狠痛斥我的同时,也将一心一意地培养红色接班人的学校领导批判得体无完肤。最最入木三分的是工作组的人严正警告,学校再也不能听任学生走这条修正主义道路了。工作组的人要我先写一份检讨书贴出去以观后效。我洗去身上的泥污,回到教室后,拿起笔正想着如何写检讨书,那边工作组的人发现我是刘区长的儿子。虽然他仍旧要我写下去,语气却缓和了许多。工作组的人说我是红五类出身,如不好好检讨,更容易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写完检讨书,我对着学校办的批评栏,提心吊胆地可怜巴巴了几天,那检讨书却一直没有出现在上面。
因为工作组的人较真,学校里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路再远再艰辛也要走,修正主义道路再近再舒服也不走”的活动。说这活动没效果也是不真实的。有一段时间,田埂上这条确实没人走了。随后的某个晚上,我在学校排练完节目回家时,见天黑无人,实在忍不住抄近路的诱惑,重又踏上了田埂。行至半中间,猛地发觉迎面来了一个人。躲又无处躲,心想若碰上工作组的人就完了。我硬着头皮迎上去,才知来人不是工作组的人,而是我们的校长。
又过了一段时间,“修正主义道路”又如当初一样畅通了,田埂上每天都有许多小学生蝴蝶般一阵阵飘来飘去,而不理会工作组的人在怒吼。渐渐地工作组的人也对自己成天追赶小学生的举动感到不满,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安排人上山砍了一堆杂刺,拦在田埂上。谁知小学生中也不乏刀枪不入的勇士,仅仅一个星期,荆棘堡垒就被攻克,乖乖地退至两旁,让出中间的路来。工作组又叫人堵上。小学生们又再次弄开。几经较量后,工作组的人又有新的发明,他牵来河西塆最凶恶的一只大花狗,用一根绳子拴在田埂上。大花狗雄赳赳地镇守在“修正主义道路”上,很令工作组的人高兴了一阵。不料好景不长,我们每天经过大花狗身边上学时,扔给它一团熟红薯,放学时,又叫它一声大花。大花狗经不住我们的物质引诱和花言巧语的腐蚀,没过多久,大花狗就开始网开一面。当我们重新走在田埂上,它还亲热地舔着我们的脚跟。工作组的人及时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将大花狗用筷子牙齿镇压后,换了一只戴着嘴笼头的大灰狗。我们则以变应变,每天早中晚三次,用土块石头猛砸大灰狗,打得大灰狗一见到背书包的小学生,就赶忙伏在田埂下的土沟里,连头也不敢抬。
就在我们以为工作组的人无计可施时,工作组的人用一天三个工分,安排了一个田埂看守人。
一天三个工分的田埂守护人,是河西塆的一个傻子,用当地人说法就是大苕。时至今日,我还坚信,天下再也找不到比这大苕更忠于职守的人了。大苕成天到晚坐在田埂上,只要有人走近,就说:“工作组下了命令,谁也不许从这儿走。”整整一个夏季,竟无人能越雷池一步。田埂上的黄豆眼见着能头一回获得丰收了。有一天工作组恭恭敬敬地领着几个人,说是检查工作,要走那条“修正主义道路”。大苕横里拦住说:“谁也不许从这儿走。”工作组一时性起,推开大苕就往田埂上走。大苕急了,用力甩开工作组,追上去将走在最后的那位拦腰一抱,扔回到田埂头边。嘴里还嗷嗷叫唤,工作组说了,谁也不许从这田埂上走,只要有人走了就扣他的工分。另几位见势不妙,赶忙自动退回来。回头一看,扔在田埂头边的人,脚踝摔断了。自然,大苕不能守田埂了。至此,工作组的人再也不见拿出什么新招来。
多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因故路过贺家桥时才发现,那条田埂真的变成了一条大路,远远望去,似乎可以通汽车。我低头和身边一个与我当年一般模样的小孩说着话,并遥指那条路,问是什么时候修的。小孩很是困惑地说不知道。那神情又分明是在反问:这路难道不是一开始就有吗?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