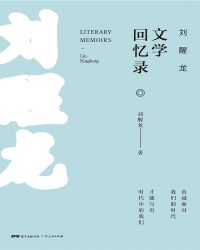第50节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50节·
有一个更大的秘密值得注意:在《圣天门口》中,我不再使用“敌人”这一概念。可是,产生“敌人”思想的土壤深厚到扁担插下去也能开花。《圣天门口》要出第二版,我在修订时,发现书中竟然还残存有几个“敌人”。近些年来的美国总统最爱使用“邪恶”这一概念,到头来惹得更多的人厌恶在这个位置上。纵观教科书中的历史,莫不是以他人为敌、以异类为敌。好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世上最大对手是自己,小说中人,用一点一滴的圣洁来改写自己,改造身边的人事,应该不难理解为,这样做才是改写历史的正途。
关于“敌人”这一点,一直没有人发现。
是我亲自出面提醒后,才引起注意的。
人就是人,每一个生命都是历史不可或缺的财富。谁能想到,孙中山在广州多次精心组织暴动,无一不是以失败告终。反而是武昌城内一群愣头青的年轻人,仓促之中出手起事,反而成就了辛亥革命的大事。即使是物,也还可以各尽其能。
文学的判断只能是隐含在文学之中。这是不二法则。否则就会闹出主题先行、图解时政等让人不齿的笑话。眼看着用这类图解来写作的人不会再有市场时,却有一种图解某类思想的作品行销于时下,甚至还能引发一定的喝彩声。
中国文学的资源十分丰富,却存在着滥用的问题。
《圣天门口》不存在“基督立场”。不能因为小说中出现“福音”和“小教堂”,就往这方面联想。小说中还出现有“巴黎公社”,难道就要说她有异国情调吗?文学当中的中国传统才是我一直所看重的,我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探索。传统也好,时尚也好,“基督”在中国更像是某种流行。客观来看,有没有信仰和信仰什么并不会导致社会生活出现重大分野。譬如,泛神主义者可以认为“圣”就是我们的敬畏之心,环保主义者可以认为宁可走路也不坐汽车就是一种“圣”。
就小说来看,我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的能力救不了全部的人,那就救一部分人,再不行就救几个人,还不行就救一个人,实在救不了别人,那就救自己,人人都能救自己,不也是救了全部的人吗?这个意思我想人人都懂。
不仅是写作之初,写作前许久,我就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那时候,我们家附近住着一户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人家。那户人家住着两间搭建在别人家墙边的破茅屋,一家四口,没有一件完好的衣服。在那种时期,那样的人家是没有政治地位的。奇怪的是,我一直对他们家有着深深的敬畏。这种敬畏并非来自小学课文上,偷辣椒的老地主,将少年刘文学活活掐死。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童年时的那种敬畏,来源于那户人家的大人小孩,衣服破得再厉害,那上面的每一个补丁都是整整齐齐的。还有他们仿佛总也弄不脏的手脚与脸庞,总也洁白得没有丁点牙慧的口齿。如此等等。当年我的情感可不是在他们那一边。然而,临到写作了,我才明白,那种记忆竟然一直在左右着我的情感。我不认为,“圣”是可以升到高天之上的精神控制,我景仰的“圣”可以小到记忆中,那户人家的孩子将一块洗净的旧布叠得方方正正装在荷包里,作为清洁自己的手帕。所以,才有小说中的董重里,因为随身的一块手帕始终保持着洁白,才被在肃反运动中杀人如麻的欧阳大姐法外施恩。我要强调的是,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神圣的角落,所以,每个人在对待他人时,都要记住并由衷尊崇这类角落,这也是一些评论家就小说所提出来的所谓“雪家精神”,也是我们的文学理论中有所缺位的中国文学中的“高贵精神”。
《圣天门口》中的雪家,其实也是饱受损害与污辱的。下卷中,在书的最后部分,有个细节,雪柠从抽屉里拿出一沓从不同年历上撕下来的杂乱无章的日历,每张日历后面都写着一个耳熟能详的男人名字,独独没有世人以为是恶魔的杭九枫。这一个细节,最能展示两个人的力量,一是杭九枫的圣洁力量,二是雪柠的承受力量。所以,雪家的力量,也还在于承受,而草莽英雄杭九枫也有着对神圣力量的虔敬。人性从来都是复杂的,所以,在众多的人物之中,杭九枫也是我创造出来,并深爱着的一个人物。在雪家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大爱与大善,还应包括承受之上的那种承担,承受是被动的,承担则有主动因素。但二者又是互动和互为因果的。我喜欢并尊重笔下的每一个人物。相比之下,有时候我会更加喜欢小说中的那些非主要人物,例如常天亮、荷边等等。
面对写作过程中的人与事,写作者还要经受我该如何做的灵魂拷问。
小说精神往往反映着写作者一定的个人精神亲历性。
《圣天门口》的结尾,有意频繁使用“吊诡”一词。这样做的用意,是想在正统之外赋予历史新的品质,也可以说历史本来具有这样的品质。从“吊诡”一词出发,有人会觉得其意义在于颠覆与消解,而用人们对历史复杂性的重新认识,或者以重新认识历史之中的我们等观点来理解,应当更合适。
关于历史的经典小说,必定同时又是一部心灵史。只有与心灵相伴相随的东西,才会真的深入到历史真相中。历史的品质几乎就是心灵的品质。在时代与历史的交接过程中,许多真相注定要被那只强而有力的大手尽可能彻底地抹去。有一个时期,大家都爱说海枯石烂心不变。如果心灵有所改变,就会意味着某种重生。只要能够把握住这条心路,无论历史改头换面到何种程度,写作者就不会被历史的吊诡所迷惑。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