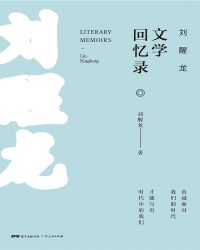第41节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41节·
我更愿意把农村称为乡村。“乡村”才是真正意义上农民的领域,而不带有任何政治意味。我在乡村待了十六年,父亲是区里的干部,但我们全家一直租住农民的房子,除了要拿着供应本到粮管所买粮油,其余作息方式与农家子弟几乎没有区别。那时区里干部的孩子也都如此,当年的老师,直到现在还记得当时三个特别淘气的干部子弟,我是其中一个,那两个现在很有成就,一个号称金融大鳄,另一个成了武警部队的少将。
有人说我是农民的代言人。我不敢说自己是农民代言人,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代言人。但我对乡村的感情超过农民自身。作为个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提到乡土,我就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这辈子无以为报的念头。一个人,一个只能写作的人,能还给乡土什么呢?就算把自己撕碎撒入乡土,对乡土又有什么用处呢?这种强烈的感觉,我从写作《分享艰难》就有了。我一直觉得,1949年以前,真正爱土地的是地主,因为土地不属于农民。1949年以后,农民拥有了土地,他们爱土地,但他们不拥有话语权。城里人有很多渠道表达愿望,但农民不行。离开乡土的人可以在任何场合、用任何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喊出来,但祖辈都生活在乡土的人跟谁说呢?我能做的,就是用手中的笔把他们的愿望表达出来。这样做绝对不是代言,而是情感上的自我安慰。事实上,世上一切的代言都不可能成功,想要成功,只能是被代言的群体自己挺身而出,才会形成真正的力量。
我的全部情感来自乡村。我一直试图获得某种回答,对于乡土,一个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讴歌反而显得苍白,为什么诅咒无法掩盖她的美丽?从来乡土只属于远离乡土之人,她是人类所有挥之不去的传统中的一种。我对乡土上发生的一切都充满深情,绝没有鄙薄任何人的意思,包括外来的知青。问题是知青们时刻把自己当作外来人,他们对乡土的情感是值得怀疑的。《弥天》出版之初,在上海举办研讨会,有人讲了一个女知青的真实故事。这个女知青是极不情愿下乡的,总在想着怎么离开。有一天机会来了。一批官员来村子里视察,女知青就等在路边一堆热乎乎的牛粪旁,等官员们过来的时候,她用双手把牛粪捧起来,送到庄稼地里。于是,官员们就号召大家向她学习,并马上把她调走了。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过去的一切行为负责,正视过去的行为。很多人正是缺少这一点。很多知青只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负面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乡村也受到了伤害,甚至受到伤害更严重。
对乡村感情深厚,不代表对城市的天生排斥。对城市我从来不反感,城市给了我很多新鲜的生活和体验,甚至给了我安身立业的家,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反感城市,那是反常的。於可训先生曾经著文,谈到我的小说,哪怕是最遥远的乡村,其背后也有一个强大的城市因素。这一点,是看我看得很透的,我的作品真的是这样。我是1994年作为“人才引进”调进武汉的,当时《凤凰琴》的影响比较大。我是从乡土走来的,刚到武汉的时候,情绪波动比较大。城市信息量大,变化快,而我内心永远有一个乡土的背景存在,难免为乡土而产生焦虑和痛苦。
乡村受到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农民负担重,文化教育落后等。我看过一本关于农民的书,里面有一个情节:几十个农民上访,在天安门广场,面对崇高的国旗,齐刷刷地下跪。我看到这里,泪流满面,这就是我们的农民,软弱中有坚强,无奈中坚守对国家的信仰。很多人写乡村的怨恨和丑恶,却对那里的善和美没有真正理解。当然,我们已经进化到21世纪,农民应该从心理和文化上进行调整,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