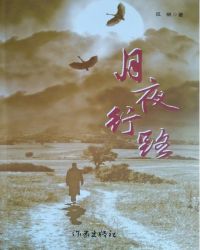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月夜行路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袅袅青烟
家乡的习俗:倘若人家盖了新屋,或分家析产另立了门户,即在立灶生火的那一天,至亲及好友,抑或邻里相知,则要备一份礼物前去祝福。主人呢?自然要置办几桌丰厚的酒菜款待。贺礼自然以宾客的情义、身份及经济状况而分薄厚了。
依照惯例:至亲者必须蒸十五个大如瓷盘的花卷,兼备一截红布与一份香烛,大致还有财神、灶王爷画像之类的物什。除此而外,似乎还需再添些现钞;一般人则送几把擀好的长面,附带一些别样的东西,诸如蔬菜、米面,或烧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以缓解立灶之初始的蹇迫与困顿,大有藉此扶助、接济之意味了。
是日,主人家预备好了酒菜,擀就了长面。请同族或村里有声望的长者设供主祭,首先点燃香烛、洒酒跪拜、祈求财神爷赐福;祝祷灶王爷惠施,青烟袅袅、顿顿稠饭、四季不断;尔后祭奠各路神明、祖宗先人佑护家宅、儿孙平安、衣食丰裕;接下来就兴高采烈、热情洋溢的开吃,尽情尽兴憧憬美好生活了。
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燎烟”礼仪。旧日的“燎烟”仪式很隆重也很繁缛:新屋盖就,或另立了门户,则请阴阳先生择定诸事宜行,或专事砌灶安锅的吉日而举行“燎烟”礼仪。
“燎烟”那天,富裕人家还要延请道士念祷“安神”之类的经文,摆供设祭的求神祗庇佑;盛邀戏班前来锣鼓喧天的吟唱,尽情日混各路神仙开心。否则诸神众仙是不愿效力的,尤其是那位专司人间烟火的灶王爷跟老伴儿,虽说你恭恭敬敬地将两位仙家供奉在了灶台上方,倘若老人家忙得不可开交,抑或你本是一个穷命世,哪能心甘情愿的替你尽职尽责哩?
假若稍事不周的话,二位仙家就整日端坐在锅灶上方,眼睁睁的盯着你成年累月往肚子里灌清汤,或叫你死灰冷灶的揭不开锅,甚至吃了这顿没有那一顿。日子如此的苦涩、艰辛,二位仙家也不会怜悯你的。这般凄惶、愁楚的光景,终于熬到了腊月二十三日傍晚,灶王爷就悄没声息的携着老伴儿上天言事去了。
两位仙家一旦在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面前,提及你家生活之清苦、难肠:哎哟,那真是马尾巴提豆腐啊——哎哟哟,没年没月的灌着清汤寡水哪,不是没上顿,就是断了下一顿……
灶王爷跟灶奶奶的老丈人与丈母娘——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听了能高兴嘛?弄不好你的倒霉光景还在后边哩。所以“安神”是极重要极隆重的环节,首先必须虔敬地把灶王爷和那个形影不离、成年累月跟着爷们混吃混喝的老太婆请上座,等二位仙家坐周正、稳当了,摆上丰厚的祭品,点燃香烛,稽首跪拜,祈求老人家施恩予惠。再由德高望重的长者点燃几根干柴,念祷着填进灶膛里,算是生火了。
接下来哩?赶快把肥猪肉倒进锅里炒啊——锅吃不足油水,做出的饭就寡淡无味。新立的灶,刚安了锅,倘若不沾腥带荤,那就注定往后的日子里,不停的往下灌清汤去吧——
旧时的贫苦人家砌灶安了锅,实在无力置备孝敬灶王爷的供祭与“燎烟”的酒菜,就倾其所有弄一顿长面,请一伙亲朋好友来造点儿势,也算新的生活从此开始了吧?不论光景怎么蹇迫、困顿,安锅立灶的饭,那是必定要吃的。即使亲朋好友,也真诚希望你家灶火常旺,屋顶的青烟袅袅不断啊——如果村里谁家的烟囱不冒青烟了,那么就肯定无疑的遇上了什么麻缠?
据悉:有人能从邻居家的烟囱里冒出烟的浓淡、色泽、缓急程度,判断出人家做的什么饭?虽然这是一种臆测,但是说明关注邻居家烟囱里冒不冒青烟,则隐含着一种情感。一般人都希望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家的青烟袅袅不断,由此证明他们的生活还能够维持,或日子过得红火。只有那些素有积怨,或相互敌视的人们,才盼望你断了青烟。这样则说明你过得很不好,抑或遭逢了困厄、灾难,而且就此断了烟火。这就是人情世故与实际的乡村生活写真。
提及家乡的“燎烟”习俗,曾有两次深切的体验与感受——早先跟父母回到家乡,暂时寄居在兄长家。大约刚过了三十天,父亲就去世了。那年我刚好虚岁十八,弟妹年幼无知,一家人的生计靠我和母亲劳作维持。日子过得十分凄惶而辛酸。
大致过了数月天时,人家传话让我们搬离。无奈,我起早摸黑的脱土坯,兄长弄了些板皮、檩条之类的材料。深秋时节,求人帮忙垒起了两间小土屋。没人抹墙泥、盘炕、砌灶,我摸索着干。一家人搬进新屋住下,已是冷冻寒天的初冬时节了。
立灶生火那天,仅有外祖母带着十五个花卷和一些米面、香烛一类的福礼来“燎烟,”此外没有任何亲戚或族人道贺。母亲擀了些长面,让我们几个饱餐了一顿。至于灶王爷嘛?记得外祖母把馍摆在灶台正中,似乎还用红布包裹了两碗米面一起供着。老人家祝祷了些什么?确实记不清楚了。然而外祖母嘱咐母亲:一定要在腊月二十三日“祭灶”那天,想法侍奉好灶王爷的神情、语气,至今难以忘怀。
当初盖了那两间小屋,大约在生火开灶的时候,没能依照乡俗好好招呼、款待、敬奉各路神祗和灶王爷,抑或得罪了财神爷,还有别的什么狗球猫屌的神仙了吧?总而言之,多年来,一直没什么好日子过。起初是清汤寡水的日子,即使这样,依然是灌罢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叫人愁肠难解。后来总算衣食无忧了,不料又接连遭逢了困厄与不幸。真令人难以应对、支撑哪——
小舅刚分了家。母亲向邻居借了几升白面,蒸了十五个花馍,再没别的物什做贺礼,想想装了一竹篮土豆、萝卜,连同那十五个花馍交给我去“燎烟。”走到途中,又饿又累,坐下歇息时揭开花布,看着那些花馍非常诱人,忍不住就一阵吞掉了两个。
到了小舅家,外祖母数了数花馍,倍感疑惑:怎么十三个呀?
我谎称:路不好走,可能是歇息的时候弄丢了。
外祖母很豁达:唉,丢了就丢了吧——
他们的“燎烟”礼仪很像样,敬奉灶王爷和诸神的供品也非常丰盛。因而生活过得很殷实,也很舒心。
后来再次离开了那片古老而苍凉,并令我很忧伤很难忘的土地,酷似一片落叶随风飘荡。多年来,有点儿像候鸟一样不断的迁徙、移居、筑巢,似乎也忘却了“燎烟”的习俗,至于专司人间烟火的灶王爷,还有他那位形影不离的老太婆,究竟是什么模样?也真想不起来了——说实话,也没有着意去想这些闲蛋。
人们在有意无意间忘却,或丢失了许多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曾经的“燎烟”确是一种祈愿与憧憬,衣食无忧了,还需要些什么哩?坦白地讲:我吃饱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想人生想未来,还想社会与民众……总之尽想些不着边际的问题。然而,似乎从来没想过灶王爷跟灶奶奶,大致因着他们曾经一个劲儿给我灌清汤的缘故吧?
现在家乡的变化很大——虽然家家都住上了小楼,但是“燎烟”的习俗依旧没有改变。立灶、生火的那天仍然很是热闹:主人为了表示日子过得很红火很宽裕,不仅邀请亲朋好友祝福,而且还约请村里人凑热闹。“燎烟”的礼仪弄得很庄严与隆重,敬奉神祗及灶王爷的祭品很丰盛,场面和气氛也很讲究、喜庆。
灶王爷同形影不离的老伴儿在享食人间供品馨香的间隙,瞅着开心就餐的人们,也禁不住眉开眼笑了。特别是到了腊月二十三日“祭灶”那天,家家户户都摆上丰盛的祭礼,虔敬地侍奉灶王爷和他的老伴儿吃饱喝足了,尔后点燃鞭炮,喜气洋洋地恭送二位仙家上天言事去了。至于他们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说些什么?那就不晓得了。 月夜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