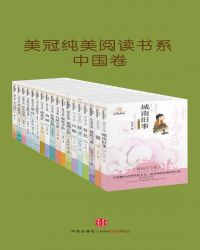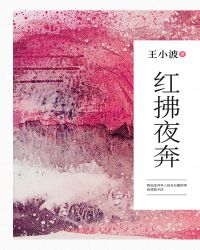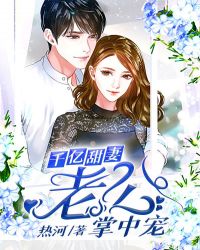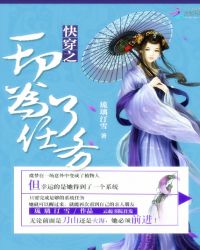一桶水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冠纯美阅读书系·中国卷(共18本)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一桶水
导读
《一桶水》发表于1936年1月,刊于《中学生》第61号。
1930年,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夏丏尊先生创办了《中学生》杂志。1931年,应夏先生的邀请,叶圣陶主持《中学生》的编辑工作。从此,叶圣陶先生主编该刊一直到解放前夕。在长达二十年的岁月里,该刊以先进的思想内容、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青年读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说《一桶水》反映的是1936年前后“新启蒙运动”中,下层市民扫除文盲、移风易俗的社会现实。小说着力塑造了阿掌和阿秋这两个富有上进心、聪明、善良的儿童形象,体现了作家对儿童的理解、热爱和赞扬。
两个小学生大家挟着一卷纸,在一家棚户的门旁边站住。背后跟着六七个比他们大一点儿的男孩女孩,男的赤膊,女的破裤管齐到膝盖,脸上都露出一副等着看戏文的神气。
“里边有人吗?”
“谁?”走出来的是比小学生大一点儿的两个男孩:青布衫敞着胸,头发长到两寸光景。
“你们一家有几个人?”一个小学生看定黑暗的门框问。
“我们一家三个人,”大一点儿的竖起右手的三个指头,“我们弟兄两个,还有个妈妈。”
“你们念过书吗?”
“没有念过。”弟兄两个齐声回答,大家摇一摇头。
“你们识字吗?”
“我们没有工夫识字。”
“你们妈妈识字吗?”
“识字?”一个中年妇人在黑暗的门框里出现了,左手挽着头发,右手拿着个木梳,“你们问我做什么?”
“现在不识字的人都得识字。本地有一百二十四个识字学校马上就要开办起来。教你们识字,一个钱也不要。我们是来给你们记下个名字。”
“我也得识字吗?哈哈!”中年妇人随手梳她的头发。
“除非你满了五十岁,”小学生留神看那中年妇人,估量她的年纪,“你同你的两个儿子都得识字。”
“小弟弟,”中年妇人带着讥笑的意味说,“我们不比你们。你们一个指头都不用动,家里有现成饭吃,念念书,识识字,满写意的。我们吃口饭,全靠两只手,不做就不得吃,哪里来的闲空工夫去念书识字?”
“这不要紧,”小学生亲切地解释给她听,“识字学校是整天开着的。夜里开到九点钟。你们去识字,随你们的便,什么时候有工夫就什么时候去。”
“小弟弟,我还要问你们一句:识了字就有饭吃吗?”
“这个……这个……”两个小学生都涨红了脸。
“哈哈,他们又回答不出了!”围在小学生背后的六七个男孩女孩好像占了便宜似的。
“你们姓什么?叫什么?”一个小学生把挟着的纸展开来,又从衣袋里取出一支铅笔,等着动笔写,借此遮掩自己的窘态。
“告诉他们好了。”大一点儿的儿子看见娘有些疑惑的样子,就抢出来说。
“告诉他们好了,”六七个男孩女孩和着说,“我们的名字都写上去了,不见得就会给他们摄了魂去。”
“我们姓孙,我叫孙阿掌,弟弟叫孙阿秋,妈妈没有名字。”
“年纪呢?”小学生一边写,一边问。
“我十六岁,弟弟十五岁,妈妈四十一岁。”
“又不对什么亲,连年纪都要问明白做什么?”中年妇人这样自言自语,同时把绞好的头发挽成个发髻。
就是这一天傍晚,娘儿子三个敲了整天的石子回来,正围着一盏美孚灯吃泡饭,醮头张老大收太平公醮的份钱来了。
孙大娘放下饭碗,从枕头底下检出一个蓝布小包来,解开了,取了两个双毫小银洋,翻覆看上几眼,就郑重地交到张老大手里。
阿掌、阿秋两个的眼光给小银洋吸引住,直到张老大把小银洋放到衣袋里,还是舍不得离开他那个衣袋。
“我走了,这是收条。”张老大把一张黄纸条放在桌子上,转身走出,随即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
“嗤,四毛钱换这么一张黄纸条!”阿掌把黄纸条抓在手里,发出愤愤之声。
孙大娘把蓝布小包仍旧藏在枕头底下,同时说:“你不要把它弄皱了,明天好好儿贴在门上,也算是我们孝敬神道的一点儿意思。”
“他一拿就是四毛钱,叫我们三个白做一天的生活!”阿秋顺着哥哥的口气。
“你不要说这种罪过话,”孙大娘眼望着阿秋,轻轻地说,好像怕给谁听见似的,“我们应该孝敬神道,说什么白做不白做!我们但求常常有生活做。我们但求神道保佑,不要把我们的破棚烧得精光。出几毛钱,我是不心痛的。”
“太平公醮每一年要打两回,可是火烧每个月就至少有两回,神道的保佑在哪里呢?”阿掌放下手里的黄纸条,一口气把剩下的泡饭吃完,随即跑到锅灶旁边洗碗筷。
“而且烧起来总是大烧,”阿秋也吃完了泡饭,带着碗筷走到哥哥身边去,“不是四五十家,就是一二十家。神道简直把我们当做玩意儿,他爱听我们的啼哭,他爱看我们坐在焦炭堆上!”
“难道你们两个发痴了?神道的事儿也好随口嚼蛆?”孙大娘念了几声阿弥陀佛,才匆匆吃完她的夜顿。
但是阿掌并不就此住口,他看着阿秋说:“每家人家四毛钱,你算算看,三百家人家一共多少钱?”
“三四一千二百毛钱,换起大洋来,就是一百块钱不至一点儿。”
“每年两回就是两百来块钱。这笔钱省下来,很可以派用场。白白送给道士真是傻。”
“你说不用打醮吗?”孙大娘洗罢锅灶,正擦着手,睁大了眼睛说,“一年打两回醮,还是常常要火烧。若说不打醮,只怕天天要火烧哩。”
“防火烧该有旁的法子,”阿掌伸张两条胳臂,挺一挺胸膛,“我们要把那法子想出来,再不要年年花冤枉钱。”
“冤枉钱!”孙大娘一屁股坐在床上,“大家情情愿愿出钱,谁也不叫一声冤枉,自然有不冤枉的道理在里头。难道大家都是呆子,独有你是个聪明人吗?你没有进学堂去念洋书,就有这么些昏想头。等到你依了今天来的两个小学生的话,真个去念起洋书来,昏想头一定还要多呢。哼,我们实在用不着念什么洋书!”
“妈妈,我也不爱念什么书,念了书还不是去敲石子,”阿掌站到孙大娘面前,“不过,打醮的事情,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你不相信,只要问阿秋。那天张老大来关照,说又得出份钱了,我就不快活。我们的钱是力气换来的,又不是偷来抢来的,为什么要花到那种事情上去?我总是这么想,防火烧该有旁的法子。”
阿秋接上说:“这一回的钱,张老大已经拿走,不必再说。下一回再打醮,妈妈,我们不要出钱吧。我们……”
阿秋的话没有说完,忽然外面扬起一片喊声。“火呀!”“火呀!”“妈妈呀!”“爸爸呀!”“奶奶呀!”“救命呀!”“救命呀!”这些声音搅和在一起,尖锐,哀酸。
“又火烧了!”娘儿子三个急忙向门外跑。只见东边约摸离开五六十家的人家正冒浓烟。狭窄的小弄两旁边,人影子一会儿闪进草棚里去,一会儿又闪出来,抱着孩子,背着东西,嘴里喳喳地嚷些什么。有几个人提着水桶跑过。有几条草狗赶来赶去乱叫。
“离张老大的家不远了。”阿秋说了一声,就牵着阿掌的手向东跑去。
三四个火舌头吐出来了,照见那草棚近旁挤着许多人。烧红的芦柴屑飘飘扬扬飞到天空。作为柱子的毛竹发出毕毕剥剥的爆裂声。一阵风来,火舌头就舔到靠西一家的棚顶。
“啊……”挤着的人一阵呼喊,像受惊的蜂群似的骚动起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孙大娘突然醒悟似的,回进自己的草棚。
半个月以后,阿掌阿秋进识字学校了,因为白天要做生活,他们吃过晚饭去。同在一起的是邻近的年纪相仿的男孩女孩,一伙儿去,一伙儿回,有说有笑,倒也没有什么不惯。可是字实在难认。那先生教一个字要翻来覆去说上一套话,听听也不免有点儿厌烦。孙大娘是没有去,她说:“有工夫识字,还不如乘乘风凉,早点儿睡觉。”警察到过她家里一趟,告诉她不去识字就得受罚。她含糊答应了,等警察转了背,努着嘴说:“什么都用得着你们管!不识字又不犯法,看你们怎样来罚我!”
在到校和回家的路上,阿掌、阿秋和同学常常谈起最近一回火烧。一连烧去三十几个草棚。一个老太婆两个小孩丧了命。救火车开不进狭窄的弄堂。水桶拿不出许多。往来取水只是杂乱无章的一阵胡闹。问到起火的原因,只为捉臭虫烧着了芦柴墙。太平公醮就在火烧的第三天开场,接连打了三天,醮头张老大就是烧得精光的一个。真个有神道的话,那神道简直是专同人家开玩笑的坏蛋。谈到末了,阿掌就来这么一句:“防火烧该有旁的法子。”
一群少年男女几次商量的结果,大家认为草棚本来是容易着火的东西,又加烧饭点灯都在零乱的家具旁边,一不当心,自然就闯出祸事来了。最要紧的还在把零乱的家具收拾得清楚一点儿,锅灶不要贴着墙壁,点灯的桌子上或者凳子上不要放旁的东西,臭虫要在白天里捉,每晚上要仔细看过,有没有火种留下,才好睡觉。
“我们一共有三百家人家,要家家这样做,只怕不容易吧。”
“我们这里有三十多人,用我们的嘴,一家一家去劝,每人劝十家,事情就成了。”
“单只是劝,还是不行。我们应该在自己家里先做起来,给人家做个样子。”
“我们还要去替人家收拾,”阿掌兴奋地说,“人家怕事,懒得动,我们可不怕事,喜欢动!”
“我们几时开头呢?”
阿掌说:“就是今晚上开头好了。天气热,早睡也睡不着。我们有的是嘴,要好言好语劝人家,等人家相信了才罢休。”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进棚户的区域。昏暗的小弄里,两旁排列着乘风凉的人,扇子劈拍劈拍地乱响,唱山歌声和小孩啼哭声搅在一起。那些人看见这些识字学生,不由得带笑带讽地说:“读书官人回来了,读书官人回来了。”
识字学生散了开来,各就自家邻近的人进行劝说,板凳有空地位,把屁股点在板凳角上,不然就蹲下来,以便和听话的人齐肩。大家一听到提起火烧的事,言语好像开了水闸,滔滔汩汩泻个不歇。到后来听说防止火烧可以从收拾家具入手,有些人就不免笑起来。说事情只怕没有那样便当。烧不烧到底在天意,天意不要你烧,你去放火也烧不着。并且,要收拾得清清楚楚须得有空地方,草棚只有那么一点点大,什么东西都挤在一块儿,你要收拾除非把东西丢掉。
识字学生于是作第二套的劝说。收拾总比不收拾好点儿,就不为防火烧,东西有了一定地方,使用起来也便当得多。并且,东西也不用丢掉,收拾之后,屋里自然会见得宽大起来。又说,这个事情并不难,不妨试一试,只要少乘两个晚上的风凉就成了。以后只要永远记着,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再没有旁的事情了。如果人手不够,或者嫌麻烦,愿意给他帮忙。
听话的人这才带点儿勉强答应下来,说:“你们这批孩子念了洋书就有新花样。譬如白做义工生活,依从你们收拾收拾吧。”
识字学生见目的已经达到,不再同人家多辩,就站起来去劝说第二家。
不到三天工夫,收拾东西的劝说传遍了棚户的区域,动手收拾了的也有百来家。就说孙大娘家里,已经改变了面目。躲在里角的锅灶搬到了门旁边。小小的一只破板箱专盛木柴,和锅灶隔开一个水缸。板箱上面挂着小竹橱,里面放着盐瓶油罐饭碗那些东西。一横一竖两张板床贴着里角。娘儿子三个所有的衣服打成两个包裹,放在板床的脚横头。除了便桶以外,一切盆桶瓶罐都藏在床底下。原来挂着的撕破了半边的天官像收下来充了柴火,就在那地方挂着娘儿子三个做生活用的几柄小铁锤。一张板桌站在屋中心,桌子上只有一把泥茶壶一只绿豆色茶碗陪着那盏美孚灯。桌子旁边是一条长凳,一把坏了靠背的椅子。
邻舍跑来看了,说:“孙大娘,你们的东西好像少了许多,你们的屋子好像大了许多了。”
孙大娘用并不严重的埋怨口气回答:“他们弟兄两个起劲,把屋里翻了个身。现在好像新搬场,样样东西都不凑手了。”
“我们也是这样。不过收拾过后,眼睛看去觉得清爽,坐坐躺躺也舒服些。真不明白,我们从前为什么只管乱摊乱塞,把家里搞得像狗窝?”
没有动手的两百来家听到这样的话也就兴奋起来。好久没有拂拭的芦柴墙掸去了灰尘。霉蒸气的破篮子破箱子被提到门外头浴着太阳光。躲在各处的臭虫遭了劫运,不待出来吸血就被屠杀。衣服棉被重新经过折叠。瓶甏(bèng)之类擦的擦,洗的洗,都显出一副新面目。他们有的看人家的样,有的自出心裁,给一切东西找个新的适当的位置。他们好像参加一种游艺的竞赛,不爱惜自己的力气,同时也忘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目的。只有十来家是孤老头子或者年迈的老太婆带着她的小孙子,他们颓唐得厉害,鼓不起中年男女少年男女那样的兴致。阿掌、阿秋一批人就给他们代劳,实践了自己的约言。
“我们也得收拾收拾道路呀。”不知道是谁这样提了出来。
“好的!”许多扫帚就在各家门前扫动,使成群的苍蝇骇得一阵乱飞。
一群识字学生从学校回家,一路踏着象牙色的月亮光,谈谈说说,又提到各家收拾东西的事情。
“喂,”一个推塌车的少年工人提高嗓音说,“你们有没有留心?有许多人家又把东西乱摊乱塞,木柴木花堆在灶门口,火油灯摆在眠床旁边了!”
“怎么没有留心?”一个纱厂女童工接上说,“不过我们家里还是像前些天一样,没有改变。”
“单单我们家里整齐是不行的,”阿秋立刻给她个回驳,“三百家人家挤得紧紧的,一家闯出祸事来,就有许多家陪着受累。故而非家家整齐不可。”
阿掌说:“我看,我们得再来一次劝说。只有一句话,大家要像念佛一样,念在口里,记在心里。就是说:‘要防火烧,第一要把家里收拾清楚。’他们当初只是一窝蜂,听了我们的劝说就收拾一下,并没有留心到这一层。现在须叫大家特别留心。”
“倘若大家识了字,就可以把这句话大大地写起来,贴在各家墙上了。”对于识字并不感到兴趣的一个香烟厂童工忽然发现了文字的用处。
“今天警察又来过了,”一个翻砂厂的少年工人接上说,“说十天以内谁不去上学校,就得拉到局子里去。”
“大家想不透识字有什么用处,字又那么难识,硬逼也是白费心思。”阿掌停顿了一下,又说:“像我们妈妈,她就说有工夫识字,还不如早点儿睡觉,让身子多歇息一会儿。——这且不要管她。我想,我们还得劝说一桩事情,就是每家预备一桶水。救火车开不进我们的弄堂。火起了,慌慌忙忙到河里去取水,取起一桶来至少泼掉半桶。故而要在平时预备一桶水。”
“你这法子好,”推塌车的少年工人拍手说,“每家一桶,三百家就是三百桶。”
“我想,”香烟厂童工抬起头来望着月亮,“那一桶水还得放在一定的地方,用得着的时候,拿起来就一点儿不费事。”
“照这样说,”翻砂厂的少年工人想得更进一步,“我们应该时常练习救火。怎样提水桶,怎样向火起的地方跑,怎样回转身来再去取第二桶水,都要练习得很熟很熟,到时候才可以不慌不忙把火救熄。你们看,救火会里不是时常在那里练习吗?”
一群识字学生听到这里一齐拍手说:“什么事情都要商量,越商量越会有好主意。现在我们可以同火神抵一抵了!”
他们怀着热烈的心情,一跑进棚户的区域,就分头向各家劝说。
“读书官人,你们又有什么新鲜花样吩咐我们了?”影子斜拖在地上和墙上的男女乱纷纷地问。
“要防火烧,第一要把家里收拾清楚!”
“要防火烧,每家必须预备一桶水!”
他们说家里要永久收拾清楚,不可今天弄清楚,明天就弄乱了。又说一桶水要永久放在一定的地方,大家要一同来练习救火。
阿掌劝说的是张老大。张老大的新草棚又搭起来了,毛竹芦席和稻草都是赊来的。他正牵挂着新债务在那里叹气,听了阿掌的话,恨恨地说:“让它再烧吧!把我人都烧死顶好!防火烧,我不高兴!谁保得定防了就不烧?”
“张伯伯,你当醮头,很起劲的,吃了自家的饭,干大家的事。现在说的也是大家的事,为什么就不高兴了?难道你只相信神道,不相信自己吗?”
“相信自己又怎么样呢?”张老大眼瞪瞪地望着稻草还没有剪齐的屋檐,“一会儿烧起来了,我一个人,两条胳臂,也奈何它不得。”
阿掌举起两只手,说:“我们有三百桶水,我们有练得熟透了的救火本领,怎么说奈何它不得?从前吃亏在我们没有合起伙来干,现在我们合起伙来,力量就大了。张伯伯,你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大力量!”
“你说合伙合得成吗?”张老大幽幽地说。
“怎么合不成?打太平公醮,大家情情愿愿出钱,这就是合得成的凭据。现在说的比打醮更有把握,大家为了自己,自然会高高兴兴合起伙来。”
“这件事情我总不来领头。”张老大还是有点儿不信服。
“张伯伯,我们不要你领头。你只要依我们的话,平时预备一桶水,到练习的时候,你也来一起练习,就是了。”
“就依你吧,”张老大有气没力地说,“现在年纪大的都得跟从你们小伙子了!”
镗,镗,镗。破锣声在棚户区域里跑过。停了一口气的工夫,又是三声:镗,镗,镗。
家家门里立刻都冲出一个人来,男女老少都有,手里各提着—个水桶,木桶铅桶都有。
“三声是西边,向西边跑呀!”像风吹的落叶似的,人群向西边涌去。西边的落照正红,仿佛真有个火烧场在那里。
“哈哈,好玩的事儿,我们去救假火!”
“看见吗,你的水泼掉半桶了?”
推塌车的少年工人高声地叫唤:“大家不要嘻嘻哈哈!救假火要像救真火一样!水不要在半路里泼掉!要浇在火场上才不可惜!”
人群冲到棚户区域西边的尽头,只见阿掌站在一个土堆上,手里举起一面红布小旗子。这是火场的记号,大家就争先把桶里的水向土堆浇去。有些人跑上土堆,去浇阿掌的身体,嘴里喊着“给你淴(hù)个浴!”
阿掌立刻成了落汤鸡,衫裤通湿,淋淋地滴着水。
“哈哈!”大家觉得有趣,都停了步看着阿掌大笑。不担任提水桶的男女和小孩也踏脚拍手助兴。
“你们忘了!”阿掌挥动旗子,好似军官一般威严,“赶快到河埠头去,取第二桶水来!你们闲看的让开一条路!你们这样团团围住是要误事的!”
人群一阵移动,闲看的站到两边。浇过了水的急忙转身向南,抄到河埠头去。后到的才得挨近土堆前浇水。
一会儿,落照已经收了光,阿掌估计差不多个个人浇掉两桶水了,就发出命令说:“今天的练习就此完毕。往后听见锣声再来。一件事情不要忘了,空桶得取了水带回去,放在老地方!”
“啊,我们打太平锣回去!”大的小的宽的尖的喉音一齐仿效着锣声:“汤,汤,汤——镗,镗,镗。”脚步踏在湿漉漉的泥地上,发出兹札兹札的声音。
阿掌从土堆上跳下来,望见张老大的背影,提着一个空铅桶独自走去,就追上了他。“张伯伯,你看今天不是大家都来了吗?”
“唔。要是早有这回事,说不定我的草棚不会烧掉了。你想,离开起火人家有八家呢。”
“今天大家不很认真,往后还得好好地练习。要练习得像兵操一样,又认真,又整齐,又勤快,那我们就不会吃火烧的苦了。”
两个人并排走了二三十步,阿掌又自言自语说:“我们更得劝大家识字哩。要是有一种容易识一点儿的字就好了。”
“怎么说?”
“我们这里不识字的多。有一句话,一定要一家一家去传说。听了的还是要弄错,要忘掉。张伯伯,你是识字的。倘如大家都识了字,有什么话不是可以写在纸上贴起来吗?譬如救火方法,就可以一句一句写出来,叫人家看得明白,记得牢固。”
“你的话不错——我要到河埠头取水去,你先走吧。”张老大和阿掌分路。
阿掌回到家里,只见阿秋已经取了一桶水,放在板床横头。他高兴地说:“阿秋,等会儿学校里回来,我们来练习造句,说的是救火方法。”
“好的。”阿秋跟着娘盛冷饭,回转头来答应。 美冠纯美阅读书系·中国卷(共18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