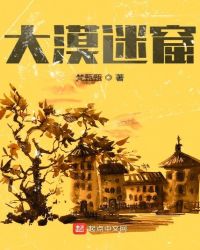第28章 白眼镜和颤抖的皮肤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谎言树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费丝在自己床上醒来。她的身上还穿着丧服,而且感到有些恶心、筋疲力尽。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她想起自己从洞穴划船回来,趁着夜色踉跄着爬上楼梯,倒在了自己的床上。
有关昨夜冒险的回忆缓缓地展现在她眼前,如同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挂毯。它似乎是一盏魔术幻灯。身骑恐龙,遭翼龙袭击,观看狗捉老鼠比赛,把自己的手突然插进装满老鼠的袋子中……
她的注意力被受伤的痛处吸引。在自己大拇指的根部,她找到两处深深的、不祥的紫色凹洞,周围的皮肤变成了骇人的黄白色。她仔细盯着它,想起了被老鼠咬住的痛苦,以及后来用盐水清洗伤口的刺痛。
费丝真的去看过狗捉老鼠的比赛。有人在那里看到了她,夹杂在一群男人中的孤独女孩。站在星空下的她曾是那样的笃定和敏锐,但此刻的她一想到自己冒过的险就感到胃里一阵绞痛。流言蜚语肯定已经被散播出去了。她珍视的隐形术将支离破碎。费丝的大脑再一次飞转起来,像老鼠一样,寻找着角落和逃生的方法。她必须得彻底否认一切,或者说自己是在出门散步时迷了路。
她渴坏了。就在她喝干瓶子里的水时,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忽然发现自己想不起最后一次为小蛇的水碗添水是什么时候了。
她急匆匆地拉开盖在笼子上的布。那条蛇和往常一样盘踞在碎布条上,但乌黑鳞甲上闪烁的黄色和白色亮光看上去却暗淡而苍白。
“不!”费丝打开笼子,急忙给它的碗里倒了些水,温柔地敲着它盘成一圈的身体。它动了,这让她松了口气。然而,当它抬起头时,她却看到它的双眼已经蒙上了一层半透明的浑浊外皮。“别死!别离开我!对不起!”当它沿着她的手臂斜倚在她的肩膀上时,她感觉贴着自己皮肤的鳞片如同纸张一般。
一阵微弱的敲门声响起。
“抱歉,小姐。”是瓦列特太太低沉的声音,“如果你想在育儿室里和你弟弟一起吃早饭的话——”
“瓦列特太太!”因为恐慌而心生冲动的费丝突然打开了房门,“几天前你给我喂蛇用的老鼠——它是怎么死的?它有没有可能吞了毒药?”
看到背着蛇突然出现在门口的费丝,瓦列特太太稍稍有些被吓到,不过很快又重新镇定下来。
“那只老鼠被困在了陷阱里。”管家迟疑地看着那条蛇,“它看上去不太像是中毒了——不过我猜这是有可能的。”
“它有些不太对劲——看!”费丝拎起蛇的头部那一圈,好让管家能够看到它浑浊不清的双眼,“药橱里有没有什么能为它催吐的东西?”
瓦列特太太边看边皱起了眉头:“小姐——你的手怎么了?”
满心惦记着小蛇的费丝完全忘记了要掩盖手上的咬痕。“是谷仓后面的一只老鼠。”她匆匆解释道,“这……这现在不要紧了!”
“和你的宠物相比,你的伤口才更需要处理。”瓦列特太太的语气坚定得令人吃惊。
“可是——”
“你的蛇正在蜕皮,小姐。”管家耐心地说,“仅此而已。”
费丝张口结舌,感觉自己就像个傻瓜。她当然知道蛇会蜕皮。不过,她根本不曾想起这件事。她只想着这条蛇会死掉、离她而去。费丝松了一口气,几乎感到有些反胃。她没有害死这条蛇。
15分钟之后,放下蛇、换上日间服饰的费丝在客厅里坐了下来,而瓦列特太太则打开了药橱。
管家坚定而温柔地捧起费丝的手,用一块沾了某种药物的布擦拭着她的伤口。空气中充斥着酒精的辛辣味。费丝努力不缩回手,把眼神从伤口上移开,望向了摆满瓶子的药橱。
“这看上去像是一个酒柜。”她大声说道。
“体弱多病的女士们就喜欢这样。”瓦列特太太回头看了看那些瓶子,“她们能从这里找到的解药,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白兰地可以刺激心脏,樱桃酒可以抗疲劳,哦,我听说任何东西混上汤力水都是治疗疟疾的良药。”
“这里有很多人得疟疾吗?”费丝满心疑惑地问道。
“我从未听说过,小姐,不过我相信那些身体欠安的小姐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管家的脸上面无表情,声音中却夹杂着些许的揶揄。
不一会儿,瓦列特太太皱起了眉头。她的视线越过费丝,凝视着窗外。
“上帝救救我们。”她低语道,“那是什么?”
费丝转过身去,隐约看到南边远方的天空中出现了棕灰色的污迹。
“看上去像是烟!”费丝回答。它升腾起来的地方很近,不像是从镇子里飘过来的,而坐落在那个方向的只有几个地方——教堂、牧师住所、电报塔、邮局和亨特小姐的住处。一丝隐隐的怀疑爬上了费丝心头。
瓦列特太太望向窗外的烟雾,紧皱着眉头,显然同样在思索着什么。
“你回到床上去,桑德利小姐。”她终于开了口,看都没有看费丝一眼,“你需要睡眠,不然会把自己累病的。普莱斯今天早上要去邮局取信——他会弄明白出了什么事情的。”
抵不过疲倦和管家的坚持,费丝踉踉跄跄地爬回床上。她以为自己睡不着,却几乎一下子就跌入了梦境之中。她梦到自己正坐在客厅里喝茶,拼命想遮掩从她的袖口和衣领中爬出来的藤蔓。亨特小姐坐在对面的一张摇椅上,皮肤如纸一般,多了一层白色硬皮的眼睛里满是恐惧。
费丝再次伴着低语声醒了过来。那声音听上去是如此的邻近,以至于让她恍惚以为是从自己的房间里传出来的。过了一会儿,她才意识到那低沉的对话是发生在仆人楼梯上的。她挣扎着爬下床铺,跑过去把一只耳朵贴在了墙上。
“……为那个男人的精神祈祷。”这听上去是普莱斯的声音。和往常一样,他说的话十分谨慎严肃:“你觉得是诅咒吗?”
“我觉得这座房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诅咒。”瓦列特太太不无讽刺地答道。
“杰妮就觉得自己被诅咒了。”一阵长久的沉默。
“她怎么样了?”管家问道。
“病着,越来越糟糕——即便是在教堂里。她吃不下、睡不着,做着噩梦,汗毛直立。有人说她就要死了。”
“他们还说过许多愚蠢的事情呢。我希望他们别让杰妮听到这些话。我不想让这样的想法在她脑子里生根……”
说话声飘走了。
杰妮不会死的,费丝告诉自己。她当然不会死。本来就没有什么诅咒。这只不过是杰妮的想象力在捉弄她,只不过是持续不断的恐惧、失眠、食欲不振以及一夜又一夜睡在冰冷教堂里的结果……
费丝的皮肤下面涌上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一瞬间,她希望自己能像蛇一样蜕皮,脱胎换骨,成为另一个人。
时间滑过了下午3点钟,费丝已经错过了午饭,可有人却在她的房门外留下了一个餐盘。应该是瓦列特太太。
下楼的时候,她碰到茉特尔正在走廊里踱步,焦躁不安,看什么都缺乏耐心。
“费丝!你到底去哪儿了?”她并没有等她作答,“你得照顾你弟弟。他今天早上四处乱跑!”
“可我得和迈尔斯舅舅去发掘现场画画!”费丝说道。
“就是那个链条会断掉、还有人往下扔石头的可怕地方?不行,费丝——我当初就不该允许你到那种地方去。而且你舅舅今天一早就过去了。他们显然就快挖到下面的洞穴里去了,他不想错过任何一步。”
这是一大打击。费丝从未像此刻这样希望能观察发掘现场的那些人。
“除此之外,我需要你在这里看着霍华德。他一直在写字——育儿室里到处都是墨水——可他并没有穿上自己的蓝色外套!你知道他写字时必须穿上那件衣服!他还有几年就该上学了……”她停顿了一下,把一只手举到额头上。“学校。”她嘟囔道,仿佛这个想法让她感到十分心痛。
“对不起。”费丝开口答道,“可我上次为他穿上那件衣服时他哭得太厉害了——”
“那就让他哭!”茉特尔火冒三丈,“这是为了他好!如果我们现在放纵他,他会变得更加糟糕!他会在学校里遭到嘲笑,被人用藤条抽打手指。这还会影响到他进入社会之后的生活——如果他不能用正确的手势使用餐具,没有人会邀请他去任何地方!霍华德的未来正处于紧要关头!他的未来……”她的声音弱了下去,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
费丝咬了咬嘴唇。“如果这不是现在能纠正过来的,该怎么办?”她问道。
“费丝,你弟弟不是个左撇子。”茉特尔坚定地回答,仿佛费丝提出的控告是不公平的,“你今天怎么了?”她皱起眉头,好好打量了费丝一番。“你简直是一团糟!你上一次好好梳头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你的身上闻上去有股柠檬的味道?”她环顾走廊四周,“一切都是一团糟!杰克勒斯医生随时都有可能过来。”她瞥了瞥时钟,“他去哪儿了?迟到两小时都没有一点消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能够感觉得到。”
就在此时,外面传来了马蹄声。
茉特尔舒了一口气。“终于来了!”她说道。
结果来的并不是杰克勒斯医生,而是医生送来的一封道歉信。他为了照看亨特小姐而耽搁了。
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亨特小姐在夜深人静时发现一群男人正在她家不远处游荡。尽管家中只有一位年长的女仆与她做伴,亨特小姐却并没有当回事,因为有人在狗捉老鼠比赛后缓缓走回家或是坐在崖顶上喝酒也算不是什么稀罕事。
然而,在她就寝之后,却被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以及“着火了”的尖叫声吵醒了。她叫醒自己的女仆,带着她冲到楼下,发现自家屋后正腾起一阵棕色的烟雾。亨特小姐派女仆去牧师住所寻求克雷的帮助,然后开始动手搬出家里和隔壁邮局里值钱的东西。首先就是她照看的那些珍贵邮件。
令她感到意外的是,她发现一群正好经过的男子跑来帮她搬起了家具和值钱的物品,还为了遮挡烟雾在脸上蒙上了布。可当她看到他们把自己的行李箱和家具搬上独轮手推车或是背在背上时,才意识到这些人并不是来好心帮忙的。她朝着他们喊叫,想把自己的首饰盒从一个“救助者”的手中夺下来。他粗暴地推了她一把,害她向后跌去,脑袋撞到墙角,失去了意识。
“我们正在尽力查明她的头骨里是否出现了破损或出血。”杰克勒斯医生在信中写道,字里行间没有了他平日里对于头盖骨的热情,或是对女性头盖骨的蔑视。
费丝想起了自己在崖顶上说的那些谎言。它们看上去是那么的渺小而脆弱。不过,这两个男孩肯定直接跑回了比赛的小屋,在本就喜欢吵吵闹闹、还喝了酒的一群男人中散播她的谣言,况且他们距离亨特小姐家还不到一英里的距离。如果说费丝的其他谎言是温和地燃烧着,那么这个谎言就是在一堆事先准备好的火药上丢下了一颗火星。
茉特尔并没有把医生信中的最后一段内容读出来,而是愣愣地站在那里,穿着美丽定制连衣裙的身体颤抖着,一丝红晕沿着天鹅绒的短项链缓缓爬了上来。
费丝满心恐惧地看着她,不知道信中是否提及了自己的名字。有人认为,袭击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你女儿在血腥的比赛中寻欢作乐时散播了诽谤的谣言……
然而,茉特尔抬起头时眼神却越过了费丝,没有望向她,脸上乌云密布、神情涣散。
“医生感谢我们协助他进行了调查。”她突然说道,“并为自己在这段痛苦的时光中打扰我们表示抱歉。今后他将尽量避免打扰我们。”
“这话是什么意思?”费丝问道。
“这就是说,我们再也看不到杰克勒斯医生了。”茉特尔答道。她的声音很高傲,却充满了苦涩,“他正在把亨特小姐从死神的口中拽回来呢,无疑相信这样做能够改善他与她的未来。若是她醒来以后成了白痴的话,那就如他所料想的了。”
费丝觉察到信中有什么她不知道的内容。听上去,医生不得体的追求突然戛然而止了。她想要为此感到释然,可母亲表情中却夹杂着什么令她害怕的东西。茉特尔既没有摆出一副好斗的表情,也没有吵吵嚷嚷——换作以往,她在虚荣心被人刺破时都会变成那副模样。她的脸上面无表情,还透露出深深的倦容。只有这么一次,她的容貌看上去和她的年龄几乎吻合了。
霍华德无聊得快要发疯,于是费丝把他带到花园里,还拿出了家中陈旧的槌球,把筐子插进坚硬的土壤中。这里的草太长了,害得球总是毫无章法地蹦来碰去。每当费丝忘记比分,或是球躲进草丛中、掉到空洞里,霍华德都会放声大笑。几小时之后,瓦列特太太把晚餐端到了草地上,就像野餐一样。
玩耍的时候,走在霍华德身边的费丝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脑海中浮现出亨特小姐整洁的黑色头发下那破碎的头盖骨。她还想象女邮局局长会退化到胡言乱语的状态,或是变成一个流着口水的傻瓜。
这就是你想要的,一个声音在她的脑海中响起。那是她的思绪,可她却几乎能够听到它在与自己对话。你想要报复她,现在你成功了。然而,这并没有给费丝带来任何的快乐。
“也许她就是凶手之一。”她压低了嗓门说。
她把双手按在脑袋两侧,强迫自己思考。如果她对自己看到的幻象理解得没错,凶手应该有两个人。传闻亨特小姐与拉姆本特有染。亨特小姐不分昼夜总是乘车外出,而拉姆本特则声称自己有睡眠问题。这给了他一个在奇怪的时间外出的绝佳借口。他们可以秘密会面,从而共同参与一项“阴谋”。
费丝不知道他们有何动机去杀害自己的父亲,可拉姆本特就是写信给迈尔斯舅舅、邀请牧师到维恩岛上来的人,而亨特小姐从一开始就是这家人的敌人。
你必须赶尽杀绝,脑海中的那个声音告诉她。你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了。
“我们能不能再玩一次?”出现在她身旁的霍华德第二十次问道。
“你现在应该累了吧!”费丝大声说道,尽管她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一点也不疲惫。她嫉妒他。她也能一遍又一遍地玩着同一个游戏却又不会失去其中的乐趣,或是担心其他任何事情吗?也许这个本领就是她所失去的或从未拥有过的东西。
环顾四周,她看到西方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桃粉色的光晕也已逐渐消失。在草的遮挡下,破旧不堪的木头筐子已经变得越发难以识别了。
“天越来越黑了。”她大声说。她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天黑。“这是最后一局了,小霍。这一次我是认真的。”
“你累了吗?”霍华德问道,随即把头歪向了一边,“出了什么事?你是不是在暴怒?”他的保姆考德尔小姐就经常暴怒,所以霍华德也学会了这个词。
“不是的。”费丝设法挤出了一个笑容,“不过……我头疼。”
“鬼魂是不是让你生病了?”霍华德的眼中闪过一丝忧虑的神色。费丝不知道他无意间听到过多少有关杰妮的对话。
“不,当然不是!”费丝强迫自己微笑,“你把鬼魂赶走了,记得吗?因为你是个好孩子,还会抄写经文。”
霍华德垂下目光,两只手紧张地绞在了一起。“我没办法把它赶走。”他低语道,“它回来了。”
“不,霍华德——”
“我看到它了。就在昨天晚上。”
费丝抽搐了一下,低头望着霍华德诚挚的圆眼睛。她被一种强大的想象力紧紧把控,仿佛猛地环顾四周,就能看到父亲正默默注视着自己。这样的想法本应让她感到安慰,可她的心里却产生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虽然她尽力了,但她依然无法想象父亲露出和蔼或理解的眼神。
“在哪儿?你是在哪儿看见它的,小霍?”
霍华德转过身去,指了指温室。
“它带着亮光。”他耳语道,“我是从窗户里看到它的。”
费丝牵起霍华德的手,朝温室缓缓走去。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草坪依旧是湿漉漉的,浸湿了她的裙褶。温室的窗户都蒙着水汽。她提起门闩,走了进去。
几株盆栽被人微微移动过了。一团一团新鲜的黑色土壤被撒得到处都是。在地板的正中央,费丝找到了一小团黏糊糊的黄色烛蜡。
“它长什么样子,小霍?”她轻声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它看上去像个男人。穿着大大的黑色外套。”
“你看到它的脸了吗?”
霍华德摇了摇头,看上去有些固执。“它在四处乱看。我想它正在找我,但它不知道我就站在窗户边上。后来它就绕到房子后面去了。”
费丝领着霍华德离开温室,朝着他所指的方向走去。经过一座花床,他们来到了通往她的屋顶花园的台阶脚下。
有个台阶上印着一个沾着泥土的巨大脚印。
“待在这里,小霍。”费丝走上台阶。迈进花园里,她又在石板上找到了两个淡淡的印记。这里的花盆也被微微挪动了一下,就连石像小童的脸也被转向了不同的方向,看上去仿佛是被眼前的东西吓到了一样。也许,就在她躺在几码外的地方熟睡时,有人不声不响地踩在了铺路石上。有人在这里寻找着什么,而这一过程把他们引到了她的门口。
不过他们不是来找我的。
她在缓缓走下台阶时突然意识到这一点。“鬼魂”翻遍了温室、花床和她的屋顶花园。他们在找一株植物。
她终于明白温室里为什么会丢掉一株植物了。有人在夜里匆忙中偷错了植物。迈尔斯舅舅要将父亲的文件和标本占为己有的决心也有了更深的含义。
有人知道谎言树的事情,还想要得到它。她的父亲把它藏起来是对的,害怕有人会来夺走它的想法也是对的。的确有人想偷走这棵树,还要求迈尔斯舅舅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它。
一棵能够告诉你无人知晓的秘密、揭开这个世界上所有谜团的树。一棵能够向政府展示敌人的计划、向科学家揭露衰老的秘密、向记者告发权势之人恶行的树。它不仅在科学意义上令人神往,还是个值钱的宝贝。强大,无价。
有人愿意为了这株植物大开杀戒。
在将秘密的线索再一次串联起来、以全新的方式审视这一切时,费丝感到脸部有些刺痛。前往维恩岛的邀请函将牧师带到了这座岛屿上,却也带来了谎言树。他无法把这个秘密托付给任何人,而凶手们期盼的也许正是这一点。这些日子费丝一直在思考父亲的一生,想弄明白对他如此羡慕、愤怒、嫉妒或报复心很重的人是谁,非要置他于死地。他的死也许只是因为他拥有一株别人想要的植物。
如今……它已经属于她了。
费丝在楼梯脚下踌躇,突然又有了另一个想法,吓得她匆忙环顾了一下四周。
如果凶手们正在寻找那棵树,那么他们可能就会知道它是依靠谎言为生的。他们甚至正在搜寻如野火般散播的诡异谎言。比方说,鬼故事或是令人感到好奇的莫名宝藏。如果他们追查近期有关亨特小姐的八卦,早晚会发现有人记得两个男孩曾经提到过自己与费丝·桑德利说过话……
她想起了自己看到的幻象,记得自己曾惶恐地平躺在地上。她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傀儡师。她只不过是一个纸做的女孩,如果被人发现,就会被撕成两半。
“鬼魂可能已经死了。”霍华德满怀希望地说道,还用一只手环抱住她的手臂,“我用我的枪击中了它。”
“哦。”费丝想起了他那把木头小手枪,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深信不疑,“是吗?”
“是的!”霍华德来回甩动她的手臂,“砰!只不过……它没有发出砰的声音,而是咔嗒一声。不过鬼魂跑掉了,所以我想它被击中了。”
咔嗒。
霍华德的木头手枪是绝不可能发出任何声响的。
“霍华德。”费丝缓缓问道,“你用来击中鬼魂的是哪一把枪?”
“猎鬼枪。”霍华德马上答道,“就是我们在树林里找到的那把枪。”
“我们找到的那把……”费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他们是一起去林间谷地中寻找猎鬼枪的,而她一直忙着盯着那些车辙看,并没有留意霍华德。
费丝,快看!快看这个!他曾经找到过什么,还朝她大叫,她却没有看过去。
“那把枪大吗?”她问道,简直不敢呼吸,“是不是铁做的,带着泛黄的白色手柄?”看到霍华德点了点头,费丝蹲下身子,直到两人的视线齐平。“霍华德,听着。那是一把真枪。一把危险的枪。你得把它给我!”
“不!”霍华德松开她的手,退了几步,“我需要它!我要用它来猎鬼!”
费丝一把抓住他的手,但霍华德转身逃回了家。她跟在他身后回了家,不过并没有在育儿室里找到他。
“霍华德少爷准备好喝牛奶了吗?”瓦列特太太在楼梯上与费丝擦肩而过时问道。
“差不多准备好了——我们在玩睡前的捉迷藏游戏呢。”费丝草草答道。如果她把整个故事都解释出来,全家就会一起出动,寻找霍华德,而那把手枪也会被找出来没收。她最不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了。
“好吧,稍微累一点对他有好处。”瓦列特太太回答。管家看上去格外疲惫,忧心忡忡。
费丝早就找出了这座房子里所有的藏身地点,但霍华德那么娇小,可以弯下腰藏进任何一个角落。不仅如此,天色已经越来越昏暗了,还有更多的阴暗处可以藏下一个倔强的小人儿。
“霍华德。”她一边寻找一边用嘶哑低沉的声音说道,“求你了,出来吧!”
最后,费丝在经过走廊时听到藏书室里传来了模糊不清的动静。她缓缓走过去,把一只眼睛贴到了锁孔处。
起初,她并没有看到什么异常的东西,只能勉强看到被微弱烛光照耀着的书架。不过,她能够听到抽屉被人鬼鬼祟祟拉开的刺耳声音,还有布料撕裂的微弱声音,以及不时传来的低沉嘎吱声。
紧接着,脚步声靠近了,一个影子缓缓爬上了书架。进入她视野的是一个男人。他把书架上的书一本本拽了出来,抖动着它们,仿佛是在寻找什么夹在里面的纸张,随即又失望地把它们丢掉。
他把手伸到书本后面,敲击着书架的背面,好像是在探测后面有没有空心的地方。就在这时,他把脸转向了房门的方向。
是迈尔斯舅舅。 谎言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