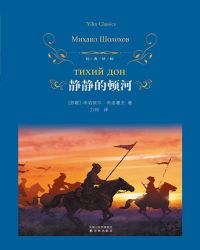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六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六章
羽茅草长成了。几十里的草原上晃动着一片银白色。风吹得羽茅草歪歪倒倒的,吹得那灰白色的草浪沙沙直响,一起一伏,时而向南倒,时而向西歪。气流经过处,羽茅草都像祷告似的一齐弯下身去,在那白色的浪顶上,很久都留着一道黑黑的印子。
各种各色的野花都开过了。冈头上的野蒿晒得无精打采地垂下了头。短短的夜过得很快。每天夜里,漆黑的天上都闪烁着无数的星星;一弯新月,这哥萨克的小太阳,放射着微弱的白光;宽宽的银河与其他一些星群纵横交错。酸涩的空气浓浓的,风又干,又带有野蒿气味;土地也吸饱了到处称霸的野蒿的苦味,很希望凉爽凉爽。一条条星路不停地闪烁着,一副高傲的神气,因为既没有马蹄践踏,又没有人足去踩;星星就像麦粒儿撒在天空干燥的黑土里,不发芽也不吐穗,撒过就没有了;月亮泛着干碱土颜色,草原上到处干透了,到处是枯萎的野草,到处有鹌鹑闹闹嚷嚷、拼死拼活地打架,还有又尖又响的蝈蝈叫声……
白天里,又热又闷,到处烟雾蒙蒙。淡蓝色的天上,是火辣辣的太阳,万里晴空,再就是像一张棕色铁弓似的张大了翅膀的老鹰。草原上到处是银光闪闪的羽茅草,到处是没有光泽的、像褐色骆驼毛似的、晒得发烫的杂草;老鹰侧歪着身子在蓝天中盘旋,它的巨大的影子在下面草地上无声无息地滑过。
金花鼠懒洋洋地嗄声叫着。土拨鼠在洞口新翻出来的黄黄的土堆上打盹。草原上燥热,然而死静,四周的一切是明净的,一动也不动。就连天边那座古冢也蓝幽幽的,又神秘,又朦胧,就像在梦里一样……
故乡的草原呀!带苦味的风一股劲儿地吹拂着马群里的骒马和公马的马鬃。干燥的马鼻子都被风吹咸了,马闻着又咸又苦的气味,觉得嘴上有风和太阳的味道,就吧嗒起那光溜溜的嘴唇,并且不时地叫上几声。低低的顿河天空下的故乡草原呀!一道道的干沟,一条条的红土崖,一望无际的羽茅草,夹杂着斑斑点点、长了草的马蹄印子,一座座古冢静穆无声,珍藏着哥萨克往日的光荣……顿河草原呀,哥萨克的鲜血浇灌过的草原,我向你深深地鞠躬,像儿子对母亲一样吻你那没有开垦过的土地!
这匹马的头又小又瘦,就像蛇头。两只耳朵又小又灵活。胸部肌肉异常发达。四条腿细细的,非常有力,蹄腕骨十分端正,蹄子光溜溜的,就像河边的小石头。屁股微微下溜,尾巴就像一捆麻。这马是顿河良种马。不但是良种,而且是真正的纯种,血管里连一滴杂血也没有,因此处处都可以看出是纯种马。这马的名字叫“长尾猴”。
在喝水的时候,“长尾猴”为了保护自己的骒马,和另外一匹更强壮的老种马打了一架,尽管种马在牧场上都是不钉马掌的,那匹马还是把“长尾猴”的左前腿踢伤了。两匹马都直立起来,用嘴乱咬,用前腿乱踢,又是扯毛,又是撕皮……
马倌不在旁边。马倌大叉开穿着落满尘土、晒得发烫的靴子的两腿,背对着太阳,趴在草地上睡觉呢。老种马把“长尾猴”踢倒在地上,后来又把“长尾猴”撵得远远的;老种马把流血不止的“长尾猴”撇在那里,自己就带着两群马,顺着“泥沟”朝前走去。
把受伤的“长尾猴”送到马棚里,兽医治好了那条受伤的腿。到第六天,米沙·柯晒沃依来向场长汇报情况,就看见生性强悍的“长尾猴”咬断了缰绳,从马架子里跑了出来,带上在附近吃草的场长、兽医和马倌们骑的几匹骒马,朝草原上跑去,起初是小跑,后来就去咬落后的骒马,催着快跑。场长和马倌们从房子里跑出来,只听见绊马索劈劈啪啪的断裂声。
“叫咱们骑不成马啦,该死的畜生!……”
场长骂着,但是他望着越跑越远的马,心中却在暗暗地称赞。
晌午时候,“长尾猴”领着几匹骒马去喝水。步行赶来的几个马倌才把几匹骒马带开了。米沙给“长尾猴”上了鞍,骑到草原上去,放进了原来的马群。
米沙担任马倌两个月以来,很用心地研究了马在配种时期的生活;研究了马的智慧和高尚的动物习性,并且感到深深的敬佩。骒马就当着他的面跟公马交配;这种自古就有的原始举动是那样朴素自然,那样单纯,使米沙不由地将它们跟人相比,觉得人就不如了。但马在彼此相处中也有许多像人的地方。比如,米沙就发现,老公马巴哈尔对待骒马一向很凶、很粗暴,但是对一匹白额头、火眼睛、四岁口的漂亮的枣红色小骒马却另眼相看。巴哈尔在这匹小骒马跟前总是心神不定、激动异常,总是带着一种特别的、又小心又热情的哼哼声去闻它。巴哈尔在休息的时候,很喜欢把自己那一副凶相的头放到小骒马的屁股上,就这样睡上很久。米沙在一旁看着巴哈尔,就看见巴哈尔那一条条的肌肉在薄薄的一张皮下缓缓蠕动着,米沙就觉得,巴哈尔爱这匹小骒马,就像老年人爱孩子那样,又深沉,又无微不至,又不指望报答。
米沙工作很认真。看样子,他热心工作的事,乡长也知道了。八月初,场长接到通知,说要把米沙·柯晒沃依调到乡公所去。
米沙马上收拾行装,把公家的东西都交还了,当天下午就动身。他不停地抽打自己的骒马。太阳落山的时候,已经过了卡耳根,而且在冈头上撵上了一辆往维奥申方向去的马车。
赶车的乌克兰人赶着两匹汗淋淋的大肥马。这是一辆带弹簧座的轻便马车,座位上半躺着一个体态匀称的宽肩膀男子,穿着一件城里式样的西服上衣,后脑勺上扣着一顶灰色细呢帽。米沙跟在马车后面走了一会儿,望着戴呢帽的人那颠得直哆嗦的耷拉着的肩膀,望着那落满尘土的白领子。那人脚边放着一个黄皮包和一个大口袋,上面盖着一件折叠起来的大衣。米沙还闻到一股刺鼻子的陌生的雪茄烟气味。“一定是个当官的到镇上来有事。”米沙心里这样想着,驱马跟马车走齐了。他侧眼朝呢帽帽檐底下一看,就半张着嘴愣住了,觉得又害怕又惊愕,背上好像有许多蚂蚁乱爬。原来半躺在马车上、眯缝着很厉害的浅色眼睛、不耐烦地咬着黑黑的雪茄烟头的是司捷潘·阿司塔霍夫。米沙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朝这位同村人那十分熟悉、然而变得很厉害的脸打量了一遍,这才认准,马车上躺着的确确实实就是司捷潘,他激动得冒出汗,咳嗽一声,问道:
“对不起,先生,您是不是阿司塔霍夫?”
马车上的那人点了点头,这一点头,帽子就摔到了额头上;他扭过头来,抬眼看了看米沙。
“是的,我是阿司塔霍夫。怎么啦?您莫非……等一等,你是柯晒沃依吧?”他欠起身来,只用嘴唇在剪得短短的栗色胡子底下笑着,眼睛里和一张苍老了的脸上保持着不可接近的严肃神情,并且又慌乱又高兴地伸出一只手来。“是柯晒沃依吧?是米沙吧?咱们又见面啦!……真高兴……”
“怎么回事儿呀?怎么搞的呀?”米沙扔掉缰绳,大惑不解地把两手一摊。“都说你死啦。可是我一看:是阿司塔霍夫嘛……”
米沙喜笑颜开,在马鞍上转来转去地坐不住了,可是司捷潘的外表和那低腔低调的一口官话,使米沙觉得很不自在;他改变了称呼,后来在说话时一直称司捷潘为“您”,模模糊糊感觉到他们之间出现了一条无形的分界线。
他们谈了起来。马匹小步走着。西边的晚霞像火一样,淡蓝色的云彩在天上飘着,渐渐投入夜的怀抱。大道旁边的黍子地里,有一只鹌鹑高声叫着,挨过了白天的忙乱和喧嚣、挨到了黄昏时候的草原,渐渐晦暗,渐渐安静下来。在通往楚卡林镇和克鲁日林镇的岔路口上,在淡紫色天空背景上,出现了淡淡的小教堂的侧影;聚拢在一起的一大堆砖红色云块沉甸甸地悬挂在小教堂的上空。
“司捷潘·安得列耶维奇,您这是打哪儿来?”米沙高高兴兴地问道。
“从德国回来。好不容易回来呀。”
“咱们村里有些哥萨克说,亲眼看见司捷潘阵亡啦,那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司捷潘回答得很沉着,很平静,好像问得他很不痛快:“挂了两处花,可是弟兄们……算什么弟兄们?他们把我扔下啦……我就当了俘虏……德国人给我治好了伤,就送我去做工……”
“好像没接到过您的什么信啊……”
“我没有什么人好写信啦。”司捷潘扔掉烟头,接着又抽起一支雪茄。
“不是有太太吗?您太太还活着呢。”
“我跟她早就不在一起过啦——这事儿大家都知道。”
司捷潘的声音干巴巴的,没有一点儿热和味道。提到妻子,他一点也不动心。
“怎么,您在人家的地方,就不想家吗?”米沙一个劲儿地追问,胸膛几乎要贴到鞍头上了。
“起初是想的,后来就习惯啦。我在那里过得挺好。”他顿了一下,又说:“本来我想永远留在德国,加入德国籍。可是现在又想家啦,就什么都扔下,回来啦。”
司捷潘第一次弯了弯眼角上那僵硬的鱼尾纹,笑了笑。
“可是咱们这儿,您瞧,乱成什么样子啦?……自己人打起来啦。”
“是啊——啊……我听说啦。”
“您走哪条路回来的。”
“我是从法国的马赛——一个老大的城市——坐轮船到诺沃罗西斯克的。”
“会不会也叫您去当兵呢?”
“也许会……村子里有什么新闻吗?”
“一下子哪能全都说得清呢?新鲜事儿多着呢。”
“我的房子还在吗?”
“风吹得直晃荡……”
“街坊邻居呢?麦列霍夫家两个儿子还活着吗?”
“都还活着。”
“我以前的老婆,您听说过吗?”
“她还在亚戈德庄上。”
“格里高力呢……还跟她在一块儿吗?”
“不啦,他跟自己老婆在一块儿。不跟您那阿克西妮亚过啦……”
“原来这样……我还不知道呢。”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米沙还在拼命地打量司捷潘。他怀着敬意称赞说:
“看样子,司捷潘·安得列耶维奇,您过得真不坏。您穿得挺阔气,就像个大人物。”
“人家那里都穿得很讲究嘛。”司捷潘皱了皱眉头,捅了捅车把式的肩膀:“喂,快点儿。”
赶车的很不高兴地甩了两鞭,两匹疲劳的马很不整齐地用猛劲儿拉了几下。马车轻轻摇晃着轮子,在坑洼不平的大路上猛烈颠簸起来。司捷潘不想再谈下去,便转过身去,背朝着米沙,问道:
“你是回村子里去吗?”
“不,我到镇上去。”
来到岔路口,米沙往右拐弯,在马镫上站起来,说:
“再见啦,司捷潘·安得列耶维奇!”
司捷潘懒懒地用手指头摸了摸落满尘土的呢帽帽檐,冷冷地回答,就像外国人说俄语一样,每一个音节都说得十分清楚:
“一路平安!”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