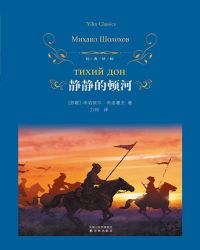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二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章
快到夏天的时候,撤退的哥萨克中有三十来个回到了鞑靼村里。其中大多数是老头子和上了年纪的当兵的,至于青年和中年的哥萨克,除了生病的和受伤的以外,几乎都没有回来。他们有一部分参加了红军,其余的都加入弗兰格尔的各个团里,躲在克里米亚,准备重新向顿河进攻。
大多数撤退的人永远留在异乡了:有些人死于伤寒,有些人在库班的最后几场战斗中战死,有几个人脱离了撤退的队伍,在马内契的草原上冻死了,有两个人被红绿军俘了去,不知去向……鞑靼村里有很多哥萨克不见了。妇女们在又紧张又担心的盼望中过着日子,每一次在村口迎接回来的牛群,都要站上很久,把手搭在眼上朝远处眺望:在笼罩着淡紫色暮霭的大道上,是不是有迟归的出门人呢?
一个衣服褴褛、满身虱子、骨瘦如柴、但是家里人盼了很久的当家人回到家里,家里都要欢欢喜喜地乱忙一阵子:给身上脏得发了黑的当兵人烧水洗澡,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为父亲效劳,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女主人一会儿端饭拿酒,一会儿跑到柜子跟前去给丈夫拿干净衬衣。偏偏衬衣又需要修补,可是女主人那哆哆嗦嗦的手指头怎么也不能把线穿进针眼儿里……在这欢天喜地的时刻里,就连那老远就认出主人、舔着主人的手一直跟到门口的狗也准许进屋子了;孩子们打碎碗碟或者洒掉牛奶也不挨打了,而且不管怎样淘气都没有事了……回来的当家人洗过澡以后还没有穿好衣服,屋子里已经挤满了妇女。她们来打听亲人的下落,战战兢兢而又如饥似渴地倾听着当兵人的每一句话。过一会儿,就会有妇女用手捂着眼泪汪汪的脸跑到院子里去,像瞎子一样踉踉跄跄地朝小胡同里走去,于是在一座房子里又有一个新寡妇哭起了死人,还有尖细的孩子们的哭声伴随着。在那些日子里,鞑靼村里就是这样:欢乐进入一家的时候,往往给另一家带来无法忍受的悲痛。
第二天早晨,脸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年轻了的当家人天一亮就起身,在家里到处看上一遍,看看首先需要干什么。吃过早饭,他就干起来。在棚子底下,凉荫里,响起欢快的刨子哧哧声,或者丁丁的斧子声,好像是在告诉大家,这一家又有勤快而能干的男子汉在干活儿了。可是在昨天听到丈夫和父亲的噩耗的人家里,房子里和院子里都是一片死静。悲痛欲绝的女主人一声不响地躺着,一夜之间就成了大人的孤儿们挤成一堆,围在她的身旁。
伊莉尼奇娜一听说村子里有人回来,就要说:
“咱们家的人啥时候回来呀?人家都回来了,可是咱们家的人连一点儿音信都没有。”
“不叫年轻哥萨克回来嘛,妈妈,您怎么连这都不明白呀!”杜尼娅不耐烦地说。
“怎么不叫回来?季洪·盖拉西莫夫不是回来了吗?他比格里沙还小一岁呢。”
“他挂花了嘛,妈妈!”
“他算挂的什么花!”伊莉尼奇娜反驳说。“昨天我在铁匠铺旁边看见他,他走起路来精神抖擞的。没见过这种挂花的。”
“他是挂花来,这会儿是在休养呢。”
“咱们格里沙挂的花还少吗?他全身都是伤疤,照你说的,他不也需要休养吗?”
杜尼娅想方设法要对妈妈说明白,指望格里高力回来现在是不可能的,但是说服老人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住嘴吧,混账丫头!”她厉声对杜尼娅说。“我知道的事儿不比你少,你想教训妈妈,还早着呢。我说他能回来,就是能回来。滚吧,滚吧,少给我啰嗦!”
老人家急不可待地盼望儿子回来,并且不论遇到什么事都会想起他来。米沙特卡一不听她的话,她就吓唬他说:“你等着吧,小毛崽子,等你爹回来,我要告诉他,叫他好好收拾你!”她要是看见从窗外路过的大车的车帮子是新的,就要叹气,而且一定要说:“看样子,人家的男子汉在家里呢,可是我们家的就是不知道回来……”伊莉尼奇娜一向不喜欢抽烟的气味,常常把抽烟的从厨房里撵出去,可是最近这个时候,她在这方面也变了。她不止一次对杜尼娅说:“去把普罗霍尔叫来,叫他来这儿抽抽烟,要不然这儿有一股死尸臭味儿。等格里沙当完兵回来,那时候咱们家就有男子汉的活人气味了……”每天做饭,她都要多做些,吃过饭以后,她还要把盛菜汤的铁罐子放进炉膛里。杜尼娅问她,这是干什么,她很惊异地回答说:“不放进去怎么行呢?咱们家当兵的也许今天回来,那他马上就能吃热的,要不然等到热好了,又这样又那样,恐怕他都饿坏了……”有一天,杜尼娅从瓜地里回来,看见厨房里的钉子上挂着格里高力的一件旧衣服,还有帽箍退了色的一顶制帽。杜尼娅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老人家,老人家就带着不好意思和可怜巴巴的笑容说:“杜尼娅什卡,这是我从柜子里拿出来的。从外面走进来,看见了,心里不知怎么就觉得好受些……好像他已经在家了……”
天天没完没了地谈格里高力,杜尼娅都觉得厌烦了。有一天,她忍不住数落起母亲来:
“妈妈,您天天唠叨过来,唠叨过去,不觉得烦吗?您这样唠叨,谁听了都烦。就听见您叨咕:格里沙,格里沙……”
“我说自个儿的儿子,怎么会烦呢?你自个儿生一个看看,那时候就知道了……”伊莉尼奇娜小声回答说。
这以后,她把格里高力的衣服和帽子从厨房里拿到自己住的上房里去了,而且有好几天她没有提到儿子。但是快到开镰割草的时候,她对杜尼娅说:
“我一提格里沙,你就生气,可是咱们没有他,日子怎么过呢?这事儿你想过没有,糊涂东西?眼看要割草了,可是连个修修耙子的人都没有……你看,家里什么都乱糟糟的,咱们两个可是没法子弄好。没有当家人,连东西也受罪……”
杜尼娅没有做声。她十分明白,母亲并不多么操心家业方面的事,这只不过是要说说格里高力、说说心里话的借口。伊莉尼奇娜更加想念儿子了,而且也无法掩饰这一点了。有一天晚上,她没有吃晚饭,杜尼娅问她是不是病了,她很勉强地回答说:
“我老啦……我想格里沙想得心里难受死了……难受得不得了,觉得什么都不亲,眼睛什么都怕看了……”
然而到麦列霍夫家来当家干活儿的却不是格里高力……就要开镰割草的时候,米沙·柯晒沃依从前方回到村里来了。他在远房亲戚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麦列霍夫家里来了。伊莉尼奇娜正在做饭,米沙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因为没有人应声,就一直走进厨房,摘下破旧的军帽,对伊莉尼奇娜笑了笑。
“你好啊,伊莉尼奇娜大婶儿!没想到我会来吧?”
“你好。你是我的什么人,会叫我想到你来?跟我们家沾什么边儿?”伊莉尼奇娜气嘟嘟地望着她十分痛恨的米沙的脸,很不客气地回答说。
米沙受到这种对待,毫不在乎,又说:
“说什么边儿不边儿……不管怎么说,总是熟人吧。”
“也就是这样嘛。”
“我是来看看,再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是上你们家来住。”
“想住还够不上呢。”伊莉尼奇娜说过,也不看客人,又做起饭来。
米沙也不理会她的话,仔细打量着厨房说:
“我来看看,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样……咱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
“我们可不怎么想见你。”伊莉尼奇娜气呼呼地在炉膛里掏着铁罐子,嘴里嘟哝说。
杜尼娅正在上房里收拾东西,一听见米沙的声音,脸一下子就白了,一声不响地把两手一扎煞。她坐到大板凳上,一动也不动,仔细听着厨房里的谈话。杜尼娅的脸上忽而浮起一阵浓浓的红晕,忽而泛起一阵灰白,直到那细细的鼻梁上出现两道长长的白条子。她听见,米沙在厨房里冬冬地走了一阵子,就在椅子上坐下来,坐得椅子咯吱咯吱响了两声,然后就划起火柴。一阵纸烟的烟气冲进上房里。
“听说,老头子去世啦?”
“去世了。”
“格里高力呢?”
伊莉尼奇娜半天没有做声,后来十分勉强地回答说:
“当红军呢。也和你一样,帽子上戴上这号儿星了。”
“他早戴上这号儿星就好了……”
“那就是他的事了。”
米沙的声音中带着十分惴惴不安的意味,问道:
“叶福杜吉娅·潘捷莱芙娜呢?”
“她在收拾屋子呢。你这个客人来得太早了,好人是不会一大早就出门的。”
“就算是坏人吧。我很想她,所以就来了。这用不着挑选吉日良辰。”
“哼,米沙,你别叫我生气吧……”
“大婶儿,我有什么叫您生气的呢?”
“有的!”
“您究竟气的是什么?”
“气的就是你说的这话!”
杜尼娅听见米沙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她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跳起来,理了理裙子,就朝厨房里走去。脸色焦黄、瘦得变了样子的米沙坐在窗前,抽着纸烟头儿。他一看见杜尼娅,无神的眼睛顿时放射出光彩,脸上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红晕。他连忙站起来,沙哑地说:
“哦,你好啊!”
“你好……”杜尼娅小声说。
“你挑水去吧。”伊莉尼奇娜匆匆看了女儿一眼,立刻吩咐说。
米沙耐心地等着杜尼娅回来。伊莉尼奇娜没有说话。米沙也不做声。后来他捻灭了烟头儿,问道:
“大婶儿,您怎么这样恨我呀?是我碍您的事了,还是怎的?”
伊莉尼奇娜就像叫蜂子蜇了一下似的,在灶门口猛地转过身来。
“你怎么有脸上我们家来呢,你这没良心的东西?!”她说。“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你这刽子手……”
“我怎么是刽子手呀?”
“就是刽子手!是谁打死彼特罗?不是你吗?”
“是我。”
“那就行了!你打死了人,不是刽子手,又是什么呢?你还上我家来……坐在那儿,就像是……”伊莉尼奇娜气得喘不上气来,顿住了,但是缓了缓气,又继续说:“我是他的亲娘不是?你怎么还有脸来见我?”
米沙的脸煞白煞白的。他正等着她说这种话呢。他激动得有点儿结结巴巴地说:
“我做的事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要是彼特罗把我抓住了,他会怎样呢?你以为他会亲我的脑袋瓜儿吗?他也会把我打死嘛。我们不是在山坡上打着玩儿的!打仗就是要死人嘛。”
“那柯尔叔诺夫亲家公呢?打死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头子,那也是打仗吗?”
“怎么不是呢?”米沙惊异地说。“当然是打仗!我可是知道这些老实人!这种老实人坐在家里,手里提着裤子,可是干的坏事,比有的人在战场上干的还要多……格里沙加老爹就是这样的人,他鼓动哥萨克反对我们。就因为他们,才打起仗来!是谁散布谣言反对我们?就是他们这些老实人!你还说什么‘刽子手’……哪儿有这样的刽子手?以前我连羊和猪都不敢杀,就是现在,我知道,还是不敢杀。我连杀畜生都下不得手。以前别人宰畜生,我都要把耳朵捂起来,跑得远远的,怕听到,也怕看到。”
“可是你把亲家公……”
“别提您那亲家公吧!”米沙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话。“他的好处就像山羊的奶那样少,可是害处就多了。我对他说:你从屋里出去,你要是不走,要叫你躺在这儿。我恨死了这些老家伙!我虽然不敢杀畜生,可是如果恨起来的话,对不起,像你家亲家公那样的坏蛋,或者别的什么敌人,我杀多少都可以!对付那些在世上活着无益的敌人,我的手是很辣的!”
“就因为你手辣,浑身都瘦干啦。”伊莉尼奇娜挖苦说。“亏了良心,恐怕心里不会舒坦……”
“才不是呢!”米沙和善地笑了笑。“我的良心才用不着为这样的老坏蛋难受呢。我是打摆子,把我折腾坏了,要不然呀,妈妈……”
“我是你的什么妈妈?”伊莉尼奇娜火了。“你去叫母狗妈妈吧!”
“哼,你对我别太过分了!”米沙低声说,并且恶狠狠地眯起了眼睛。“我不能担保忍受你的一切。大婶儿,我老实对你说吧:你不要因为彼特罗的事恨我。他是自作自受。”
“你是刽子手!刽子手!给我滚出去,我见不得你!”伊莉尼奇娜又一次声明说。
米沙又点起一根烟,很镇静地问道:
“你们家的亲戚米佳·柯尔叔诺夫不是刽子手吗?格里高力又是什么呢?你不说你的儿子,可是他才是真正的、道道地地的刽子手呢!”
“你别胡说!”
“我从来就不胡说。那么,依你看,他是什么呢?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回事儿呀!大婶儿,如果你把这种外号送给所有打过仗的人,那我们就都是刽子手了。问题是为什么杀人和杀的是什么人。”米沙意味深长地说。
伊莉尼奇娜没有做声,但是看到客人还是不想走,就冷冷地说:
“够了!我没有工夫和你说话,你回家去吧。”
“我的家就像兔子的窝一样了,到哪儿,哪儿就是家。”米沙冷冷一笑,站起身来。
想用这一套和这样的话把他赶出去,那是休想!米沙才不是那种感情脆弱的人,才不理会气得发了疯的老婆子那些很不客气的言语举动呢。他知道,杜尼娅是爱他的,至于其他,包括老婆子在内,他全不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晨,他又来了,就像什么事都不曾有过似的,问了问好,就在窗前坐下来,用眼睛注视着杜尼娅的每一个动作。
“你倒成了常客了……”伊莉尼奇娜也不回答米沙的问候,随口说。
杜尼娅的脸一下子红了,用生气的目光看了看母亲,就垂下眼睛,一句话也没有说。米沙冷笑着回答说:
“我不是来看你的,伊莉尼奇娜大婶儿,你用不着生气。”
“你顶好压根儿别上我们家来。”
“那我又上哪儿去呢?”米沙正色问道。“多亏你家的亲戚米佳,我剩了孤单单一个人,就像独眼龙的眼睛,在空房子里就是狼也呆不住。大婶儿,您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反正是要上你家来。”他说完了,又把两腿叉了开来,坐舒服些。
伊莉尼奇娜仔细看了看他。是的,看样子,这样的人是不那么容易撵走的。米沙那微微弯着的身子,那歪着的脑袋,那闭得紧紧的嘴唇,都显示出一种像牛那样的倔劲儿……
等他走了以后,伊莉尼奇娜把孩子们支到院子里,对杜尼娅说:
“叫他以后别进咱家的门。明白吗?”
杜尼娅眼睛连眨都不眨,看了看母亲。麦列霍夫家的人都有的那种神气霎时出现在她那气得眯缝起来的眼睛里,她好像咬着每一个字说:
“不!他要来的!您拦不住!他要来!”她再也憋不住,用围裙捂住脸,跑到过道里去了。
伊莉尼奇娜重重地喘着气,在窗前坐了下来,坐了很久,一声不响地摇着头,用视而不见的眼睛望着草原上的远方,远方有一道由嫩蒿镶成的、被太阳照得银光闪闪的边儿,把天和地分了开来。
快到黄昏时候,还没有和解而且都不说话的杜尼娅和妈妈在河边菜园里栽已经倒掉的篱笆。米沙走了过来。他一声不响地从杜尼娅手里接过铁锹,说:
“挖得太浅了。风一刮,你家的篱笆又要倒了。”于是他把坑挖深些,栽好桩子,帮着把篱笆竖起来,捆在桩子上,然后才走。第二天早晨,他拿来两把刚刚刨好的耙子和一根草叉把子,放在麦列霍夫家的台阶旁边;他向伊莉尼奇娜问过好,就一本正经地问道:
“要上草甸子上去割草吧?人家已经过河去了。”
伊莉尼奇娜没有做声。杜尼娅替妈妈回答说:
“我们没法子过河。小船从秋天就放在棚子底下,都开缝了。”
“春天就应该把船放到水里去嘛。”米沙用责备口气说。“要不要塞塞船缝呢?你们没有船可不方便。”
杜尼娅用恭顺和等待的目光看了看妈妈。伊莉尼奇娜一声不响地在和面,装出不理睬的样子,好像这些话都和她无关。
“你们家有麻吗?”米沙微微笑着,问道。
杜尼娅到储藏室里去,抱来一捆麻披子。
快到吃午饭的时候,米沙把小船收拾好了,来到厨房里。
“行了,我把船放到水里去了,在水里泡泡吧。还要把船锁在桩子上,要不然会叫人拖走的。”他又问:“大婶儿,割草的事怎么样呢?是不是要我帮你们割割?反正我闲着没事儿干。”
“你去问她吧。”伊莉尼奇娜用头朝杜尼娅点了点。
“我要问当家的呀。”
“看来,我在这儿当不了家了……”
杜尼娅哭起来,跑进上房去了。
“那我就来帮帮忙吧。”米沙哼哧了两声,就毅然决然地说。“你们家的木匠家什在哪儿?我想给你们做两把耙子,要不然旧耙子太不好用了。”
他走到敞棚底下,一面吹着口哨,一面刨起耙齿来。小米沙特卡在他身边转悠着,带着央求的神气望着他的眼睛,说:
“米沙叔叔,给我做一把小耙子吧,要不然没有人给我做呀。奶奶不会做,姑姑也不会做……就是你会做,你做得很好!”
“我给你做,咱们俩同名嘛,真的,我做,不过你要离远一点儿,别叫刨花迸到你眼睛里去,”米沙一面笑哈哈地劝他,一面惊讶地想道:“嘿,这小东西长得真像……跟他爹一模一样!眼睛也像,眉毛也像,上嘴唇也是那样往上翘……真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他开始做小孩子玩的小耙子,但是还没有做好,他的嘴唇就发了青,黄黄的脸上就露出恶狠狠的、同时又是服服帖帖的表情。他不吹口哨了,把刀子放下,肩膀瑟瑟缩缩地抖了起来。
“米沙特卡,同名字的人,给我拿块麻布来,我要躺一躺。”他央求说。
“干什么?”米沙特卡问。
“我要病啦。”
“干吗要生病?”
“唉,你干吗钉着问起来没有完……唉,到了生病的时候,就要生病嘛!快去拿来!”
“那我的耙子呢?”
“等会儿就做好。”
米沙浑身抖得厉害了。他咯咯地磕打着牙齿,躺在米沙特卡拿来的一块麻布上,摘下帽子,用帽子盖住脸。
“你这是已经病起来了吗?”米沙特卡很难受地问道。
“是的,病起来了。”
“那你干吗老是哆嗦呀?”
“我打摆子嘛。”
“你干吗要磕打牙齿呀?”
米沙用一只眼睛从帽子底下看了看问起来没有完的小小的同名人,微微笑了笑,不再回答他的问题了。米沙特卡很害怕地看了看他,就朝屋里跑去。
“奶奶!米沙叔叔在棚子底下躺下了,他使劲哆嗦,使劲哆嗦,哆嗦得要跳起来啦!”
伊莉尼奇娜朝窗外看了看,便走到桌子旁边,沉思起来,老半天没有做声……
“你干吗不说话呀,奶奶?”米沙特卡扯着她的小褂袖子,焦急地问道。
伊莉尼奇娜转过脸来朝着他,硬邦邦地说:
“乖孩子,去拿条被子给这个坏小子,给他盖上。他这是打摆子,是这样一种病。你能把被子拿去吗?”她又走到窗前,朝院子里看了看,急忙说:“你等等,等等!别拿了,不用了。”
杜尼娅正拿自己的羊皮袄往米沙身上盖,并且弯下身子在对他说话呢……
等摆子发作过以后,米沙为准备割草一直忙活到天黑。他很没有力气了。他的动作又缓慢,手又不听使唤,但是他还是把米沙特卡的小耙子做好了。
黄昏时候,伊莉尼奇娜摆好了晚饭,叫孩子们在桌边坐下来后,也不看杜尼娅,说:
“去,叫那个……叫他什么呢……来吃晚饭。”
米沙也不画十字,无精打采地弯下身子,在桌边坐了下来。他那黄黄的、一道道肮脏的干汗迹的脸上显出十分疲惫的神情,他把调羹往嘴里送的时候,手还在轻轻地打哆嗦。他小口小口地吃,吃得很勉强,偶尔淡淡地打量一下坐在桌旁的人。但是伊莉尼奇娜很惊异地看到,这个“刽子手”在看米沙特卡的时候,那无神的眼睛就显得热和起来,有了精神,一种欢喜和亲切的光彩在眼睛里亮了一会儿,又熄灭了,但是在嘴角上有老半天还隐隐荡漾着微笑。后来,他把目光移到别处,他的脸又罩上一层像阴影一样的呆呆的冷淡神情。
伊莉尼奇娜偷偷观察起米沙,这时候才看到,他生病生得太瘦了。在那脏得变成了灰色的军便服底下,半圆形的肩胛骨又尖又凸出,瘦成了尖角形的宽肩膀头耸得高高的,那长满红胡楂子的喉结在细得像小孩子一样的脖子上显得十分奇怪……伊莉尼奇娜对这个“刽子手”那佝偻着的身子、对他那蜡黄的脸看得越仔细,她的心里越是不自在,心里越是矛盾得厉害。忽然在伊莉尼奇娜心中不由地萌发了对她痛恨的这个人的怜惜之情,这种炽烈的母性怜惜心连最刚强的女人都能征服。她无法克制这种新的感情了,就把满满的一碗牛奶推给米沙,说:
“为了上帝,你多吃点儿吧!看你瘦成什么了,叫我看着都恶心……还想做女婿呢!”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