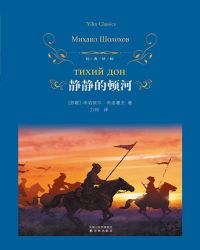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十三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三章
积雪的山冈脊部,被明丽的阳光和万里无云的蓝天映照得白得耀眼,像白砂糖一样亮晶晶的。山冈下面的赤杨疙瘩村,就像用布头拼成的一条大花被。左边是蓝蓝的司维纽哈河,右边是零零落落的许多小村庄和德国人的居住区,就像许多模糊不清的小点儿,河湾过去,那灰蒙蒙的一片便是捷尔诺夫镇。赤杨疙瘩村东面,有一道小一些的山冈曲曲弯弯地向上游伸去,这道山冈坡度平缓,到处是山沟。山冈上有一排像栅栏一样的电线杆子,是通往卡沙尔去的。
这一天格外晴朗,格外寒冷。太阳周围有许多朦朦胧胧的彩虹般的光带。风从北方吹来。吹得草原上的积雪到处飞舞。但是茫茫的雪原,直到天边,都是明朗的,只有东方,大地尽头处,朦朦胧胧,笼罩着淡紫色的雾气。
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拉着格里高力离开了米列洛沃,决定不在赤杨疙瘩村停留,径直把爬犁赶到卡沙尔,就在那里过夜。他是接到格里高力的电报后从家里出来的,一月二十八日傍晚时候来到米列洛沃。格里高力住在小客店里等着他。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大约在十一点左右就过了赤杨疙瘩村。
格里高力在格鲁博克附近作战受伤以后,在米列洛沃的行军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腿部的伤好一点了,就决定回家。同乡的哥萨克已经把马给他送了来。格里高力是带着既遗憾又高兴的复杂心情上路的。遗憾的是,他在为建立顿河区政权而斗争的关键时刻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可是他一想到就要见到家里人,就要回到自己的村里,他又十分高兴;他自己都不肯承认他是想见见阿克西妮亚,但是他时常想着她。
他跟父亲见了面,有些疏远了。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彼特罗已经在背地里对他叨咕了不少)沉着脸一个劲儿地打量着格里高力,在他那直勾勾、滴溜溜的目光中充满了不满和担心。晚上在客店里住下以后,他向格里高力问起顿河地区发生的一些大事,问了很久,儿子的回答显然使他很不满意。他嚼着发了白的大胡子,看着自己那缝了皮底的毡靴,鼻子眼儿哼哼着。他很不情愿地和儿子争论起来,可是一提卡列金,他就替卡列金分辩,劲头儿就来了,在火气上来的时候,他又像从前那样对格里高力训斥起来,甚至还跺起那只跛脚。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卡列金秋天到咱们村上来过!在广场上召开过村民大会,他趴到桌子上,跟老头子们聊了半天,他就像《圣经》上说的那样,预言庄稼佬要来啦,要打仗啦,如果咱们摇摆不定的话,他们就把什么东西都抢去,而且就占住顿河地区不走了。他在那时候就知道要打仗啦。你们他妈的怎么样?他还不如你们有见识吗?他是个有学问的将军,带领过千军万马,见识还能不如你们吗?卡敏镇上那一伙人都像你一样,都是一些没有学识的二百五,只会搅得人心不安。你们那波得捷尔柯夫是什么出身?是个司务长吧?……噢!官衔和我一样嘛。就这么一点儿根底嘛!……赶上这种年头儿……真没办法!”
格里高力和他争论很不带劲儿。他还没有见到父亲的时候,就知道父亲是什么态度了。再说,现在又增添了新的因素:对于砍死柴尔涅曹夫和不经审判就枪杀俘虏的军官,格里高力怎么也不能原谅,怎么也不能忘记。
驾辕的两匹马轻快地拉着像簸箩一样的爬犁前进着。格里高力那匹上了鞍的战马用缰绳拴在爬犁后头,在后头小跑着。一路上经过的都是从小就熟悉的一些村镇:卡沙尔、波波甫卡、卡敏卡、下亚布洛诺夫村、格拉乔夫村、亚辛诺夫卡。直到回到自己的村子,格里高力不知为什么总是毫无头绪地、乱糟糟地想着不久前的事情,他几次要多多少少想一想以后的事,但是一想到回家休息,就再也想不下去了。“等回到家里,休息休息,养养伤,以后……”他想着,并且在心里满不在乎地说:“以后会有办法的。船到桥头自会直……”
他打仗也打厌了。真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充满了仇恨和敌视的难以理解的世界。过去的一切都稀里糊涂,矛盾重重,探索一条该走的路是很难的;就好像走在一条遍地泥沼的小路上,脚底下的土不住地摇晃着,走着走着,小路又分成了两条,于是就没有把握了,不知道该走哪一条。他拥护过布尔什维克,自己跟着走,还带领别人跟着走过,可是后来他有了一些想法,心渐渐冷了。“真的让伊兹瓦林说对了吗?究竟该依靠谁呢?”格里高力靠在爬犁后背上,模模糊糊地想着这个问题。但是他想到在家乡的情景,想到怎样修理犁耙和大车准备春耕,怎样用柳条儿编牲口簸箩,等土地解冻和晒干之后,就要到田野上去,用老早就想干活儿的手抓住犁把,跟在犁后面走,感觉着铁犁不住地跳动和前进;他想到他就要呼吸到嫩草的芳香和刚刚犁起来、还带着融雪潮气的黑土的香味——想到这一切,心里就暖洋洋的。真想照料照料牲口,堆堆干草垛,闻一闻苜蓿、冰草萎蔫时的气味和牲口粪的臭味。他希望太平,希望安静,因此,格里高力四下里望着,望着马匹,望着父亲那裹在皮袄里的扁平的脊背,严肃的眼睛里就流露出不好意思的喜悦神情。那皮袄上的羊臊味,没有洗刷的马匹那种家常样子,还有村子里那只站在地窖上高声啼叫的大公鸡——这一切都使他想起差不多已经忘掉的往日的生活。这时候他觉得这僻静的村庄里的生活就像一支啤酒花儿,又甜,香味又浓。
第二天傍晚时候来到鞑靼村外。格里高力在山冈上就放眼朝顿河望去:那是老婆沟,沟边的芦苇就像镶上的黑貂皮;那是那棵干杨树,可是渡口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那是鞑靼村,熟悉的街道、教堂、广场……格里高力一看见自己家的房子,心就猛烈地跳了起来。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院子里井边的提水吊杆,把它那柳木胳膊举得高高的,好像在招手呢。
“眼睛不发酸吧?”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回头看着,笑着说。格里高力也不装假,坦率地承认说:
“是有些酸……当然要发酸啦!……”
“这就是说,家乡嘛!”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非常满意地叹了一口气。
他把爬犁朝村子中央赶去。几匹马轻快地朝冈下跑,爬犁摇来摆去地往冈下滑。格里高力猜出父亲的用意,但他还是问道:
“干吗要往村子里面赶?一直进咱们的胡同好啦。”
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转了转身,偷偷地笑着,说:
“我送儿子去打仗的时候,儿子还是一个普通的哥萨克,可是现在当上军官啦。怎么,我就不能把头昂得高高的,拉着儿子在村子里转转?叫大家都看看,眼红眼红。伙计,我的心里舒坦呀!”
在大街上,他很沉着地吆喝着马,身子朝一边歪着,晃悠着打着起了毛的鞭子,几匹马感觉到离家近了,就好像没有跑过一百四十里路似的,精神抖擞地、飞快地跑了起来。迎面遇到的哥萨克都对他们行礼,妇女们都手搭凉棚,从院子里和窗户里往外看;一群群的母鸡惊得在大街上咕哒咕哒地乱跑。一切都顺顺当当,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他们穿过了广场。格里高力的那匹马眼睛一斜,看见不知是谁拴在莫霍夫家棚子边的一匹马,就高高地昂起头,叫了起来。村庄的尽头和阿司塔霍夫家的房顶已经可以看得见了……但是这时候,爬犁来到十字路口,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一头小猪从街上跑过,慢了一步,落到了马蹄底下,压伤的小猪哼了一声就滚到了一边,一个劲儿地尖叫着,那压断的脊梁骨怎么都挺不起来了。
“哼,你他妈的偏要来捣蛋!……”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骂着,照压伤的小猪抽了一鞭。
糟糕的是,这小猪偏偏是阿丰卡·奥捷洛夫的遗孀安纽特卡的。这娘们儿又泼辣,嘴又厉害。她毫不怠慢地跑了出来,一面披头巾,一面破口大骂起来,骂的话十分难听,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只好勒住马,转过身来。
“住嘴,浑蛋娘们儿!你叫什么?赔你的癞猪好啦!……”
“你这妖魔!……老鬼!瘸狗,你才是癞猪呢!……我送你去见村长!……”她挥舞着双手,大声叫喊着。“我×你娘,我要教训教训你,看你还敢压孤儿寡妇的畜生!……”
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被她骂得上了火,红着脸喊叫道:
“骚娘们儿!”
“该死的土耳其佬!……”安纽特卡立即回骂道。
“母狗,我把你娘×个稀烂!”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提高了他那粗嗓门儿。
但是安纽特卡骂起人来是从来不用打草稿的。
“外来的杂种!老不死的!老贼!偷鸡摸狗!……搞破鞋!……”她就像喜鹊那样吱吱喳喳叫了起来。
“我用鞭子抽你,母狗!……闭上你的狗嘴!”
但是安纽特卡骂的话更难听了,就连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这样一个老于世故的人,都窘得红了脸,并且一下子浑身都冒了汗。
“走吧!……干吗和她骂起来没个完?”格里高力看见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都很注意地听着麦列霍夫老汉和清白的寡妇安纽特卡之间偶然发生的口角,就很生气地说:
“哼,那舌头……有缰绳这么长!”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使劲吐了一口唾沫,恶狠狠地赶了一下子马,好像要把安纽特卡压死。
已经走过了一个街口,他才提心吊胆地回头看了看。
“一张死嘴骂起人来好厉害!……哼,你这乱咬人的东西……真该把你他妈的压成两截!”他发狠地说。“把你和你的小猪一起压烂!谁要是遇上这种泼辣货,八辈子都倒霉!”
爬犁从自己家蓝蓝的护窗前驶过。彼特罗帽子也没戴,军便服也没有系腰带,就跑出来开了大门。杜尼娅那白白的头巾和忽闪着两只黑眼睛的、笑盈盈的脸从台阶上飞了下来。
彼特罗亲着弟弟,匆匆地对着他看了一眼。
“还好吗?”
“挂花啦。”
“在哪儿挂花的?”
“在格鲁博克。”
“压根儿就用不着在那儿受罪!早就该回家来。”
他亲亲热热地把格里高力摇晃了几下,就让给杜尼娅去亲。格里高力抱住妹妹的丰满、成熟的肩膀,亲过她的嘴唇和眼睛,一面往后仰着,很惊讶地说:
“是你呀,杜尼娅,真认不出来啦!……出落成这么一个大姑娘啦,可是我一直以为你还是那个傻里傻气的毛丫头呢。”
“瞧你说的,小哥!……”杜尼娅被哥哥抱得好疼,挣了开来,也和格里高力一样,龇着一口白牙笑着,走到一边。
伊莉尼奇娜抱着两个孩子走来;娜塔莉亚是跑的,赶到了婆婆的前头。她一下子变得格外有神采,格外漂亮。她那梳得光光的、在脑后挽成一个大鬏儿的黑油油的头发,使她那高兴得发了红的脸显得格外红。她紧紧贴到格里高力身上,用嘴唇慌乱地在他的脸上、胡子上亲了好几下,便急忙从婆婆手里接过儿子,递给格里高力。
“你瞧,儿子长得多好!”她得意洋洋地高声说。
“快让我看看我的儿子!”伊莉尼奇娜十分激动地把她推开。
母亲把格里高力的头扳得低低的,亲了亲他的额头,用粗糙的手一下一下地抚摩着他的脸,又激动又高兴地哭了起来。
“还有女儿哩,格里沙!……给你,抱一抱!……”
娜塔莉亚把裹着头巾的女儿放到格里高力的另一只胳膊上,格里高力没有了主意,不知道该看谁才好:他忽而看看娜塔莉亚,忽而看看妈妈,忽而看看孩子们。眼神抑郁、双眉紧锁的儿子完全是麦列霍夫家的模样:有点儿凌厉逼人的黑眼睛也是那样长长的、细细的,两道眉毛也是离得远远的,眼白也是鼓鼓的、蓝蓝的,皮肤也是黑黑的。他把一只肮脏的小手放在嘴里,歪着头,怯生生地、一个劲儿地盯住父亲。格里高力只看见女儿两只凝神的、也是那样黑的小眼睛,她的脸蛋儿裹在头巾里了。
他抱着两个孩子,正想朝台阶走去,但是腿上一阵钻心的疼痛。
“娜塔莎,把他们抱去吧……”格里高力咬着牙歪着嘴笑了笑,歉疚地说。“要不然我连门槛都跨不过去啦……”
妲丽亚理着头发,站在厨房正中。她满面笑容,十分随便地走到格里高力跟前,合上两只笑盈盈的眼睛,把两片热乎乎的、湿润的嘴唇紧紧贴到他的嘴唇上。
“一股子烟臭味!”她笑嘻嘻地挑了挑那两道弯弯的、好像用墨描成的眉毛。
“来,让我再看看你!唉,我的心肝儿,好孩子呀!”
格里高力笑着,靠在母亲的肩上,心里觉得热辣辣的。
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在院子里卸爬犁,一瘸一拐地在爬犁周围转悠着,他那红红的腰带和红红的帽顶闪来闪去。彼特罗已经把格里高力的战马牵进马棚里,这会儿正把马鞍往过道里送,一面走,一面转过身去和杜尼娅说话,杜尼娅正要去拿爬犁上的煤油桶。
格里高力脱掉衣服,把皮袄和军大衣搭到床背上,又梳了梳头发。他在板凳上坐了下来,便招手叫儿子过来:
“米沙特卡,上我这儿来。来,你怎么,不认识我吗?”
米沙特卡嘴里还是咬着小手,侧着身子走过来,在桌子跟前停了下来。妈妈在炕边上用心爱和得意的目光看着他。她又对着女儿的耳朵小声说了两句话儿,把她从手上放下来,轻轻地推了推她。
“你也去呀!”
格里高力把两个孩子一起搂到怀里,分别放到两个膝盖上,问道:
“两个小东西,你们不认识我吗?波柳什卡,你也不认识爸爸吗?”
“你不是爸爸。”儿子小声说(有妹妹在一起,他的胆子大些了)。
“那我又是什么人呢?”
“你是一个外人。”
“这就热闹啦!……”格里高力哈哈大笑起来。“那你爸爸又在哪儿呢?”
“俺爸爸当兵呢。”女儿歪着头,很有把握地说(她的胆子要大些)。
“孩子们,就别认他!叫他以后记住自己的家。要不然他一年到头在外头跑,叫人都不认识啦!”伊莉尼奇娜故作严厉地插嘴说;她见格里高力在笑,也笑了笑,说:“你老婆差点儿都不要你啦。我们正打算给她招一个女婿呢。”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娜塔莉亚?嗯?”格里高力用开玩笑的口气向妻子问道。
她的脸一红,克制着在家里人面前不好意思的心情,走到格里高力跟前,坐在他身边,用无限幸福的目光把他浑身上下打量了半天,用热乎乎、硬邦邦的手抚摩着他那干瘦的棕色的手。
“妲丽亚,把饭给他端来!”
“他自己有老婆嘛。”妲丽亚笑着说了一声,就袅袅婷婷,还是迈着那样轻盈的步子,朝灶前走去。
她还是那样苗条,那样爱打扮。那细细的秀腿上穿着紧绷绷的淡紫色毛袜,脚上穿着端端正正的短靴,就好像是雕成的;带褶儿的红裙子紧紧绷在身上,绣花围裙白得耀眼。格里高力又转眼去看妻子,就发现她的穿戴有一些变化。她知道他要回家,也换了换衣裳;一件袖口镶着窄窄的花边的天蓝色仿绸女褂勾勒出健美的腰身,柔软的乳房将上衣支得高高的;绣着花边的蓝裙子下部很肥大,上部紧紧裹在身上。格里高力从旁边打量了一下她那圆滚滚的双腿、紧绷绷的肚子和像肥壮的母马那样的大屁股,心里想:“哥萨克娘们儿和所有的娘们儿都不一样。穿衣服有一定的习惯,就是让所有的地方都显露出来,看不看由你。庄稼佬他们的娘们儿不一样,前身后身叫人分不清,就像装在一条麻袋里……”
伊莉尼奇娜发现他在打量妻子,就特意用赞赏的口气说:
“你瞧咱们家两位军官太太穿得多漂亮!连城里的太太们都要眼红啦!”
“妈,瞧您说的!”妲丽亚接话说。“我们哪儿能赶得上城里太太?!你瞧,这耳环子都坏啦,再说,这都是便宜货!”最后一句话她说得很伤心。
格里高力把一只手放在妻子那宽宽的、干惯了活儿的脊背上,第一次这样想:“是个漂亮娘们儿,很招人喜欢……我不在家,她是怎么过的呢?恐怕有些男人眼馋过她,也许她也眼馋过什么人。万一她有不三不四的事,那可怎么办呢?”他忽然想到这一点,心突突地跳起来,脑子里乱了。他用探询的目光看了看她那红扑扑、光油油、散发着香粉气味的脸。娜塔莉亚被他这样盯着看,脸一下子全红了,她克制着不好意思的心情,小声问:
“你干吗这样看我?怎么,你想我了吧?”
“当然想啦!”
格里高力驱走一些不应有的念头,但是这时候对妻子产生了一种不自觉的敌对心情。
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哼哧哼哧地走进门来。他对着圣像祷告了一阵子,快活地说:
“哦,再向你们问一次好!”
“托福托福,老头子……冻坏了吧?我们等着你呢;汤是热的,刚从火上端下来。”伊莉尼奇娜忙活起来,丁丁当当地用勺子在舀汤。
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一面解脖子上的大红围巾,一面跺着冻得硬邦邦的、缝了皮底的毡靴。他脱掉皮袄,把胡子上的冰凌捋下来,靠着格里高力坐下来,说:
“真冻坏啦,可是到了村子里就热和起来啦……把安纽特卡的小猪压坏啦……”
“谁家的小猪?”妲丽亚正在切一大块白面包,她停下来,很带劲儿地问道。
“安纽特卡家的。这个该死的娘们儿,她跑出来,大骂一通!又骂我这个,又骂我那个,又是老贼,又是偷鸡摸狗。我偷谁家的鸡,摸谁家的狗来,真是她娘的胡扯!”
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一一数着安纽特卡送给他的那些外号,只有一点他没有说,那就是她骂他老不正经,搞破鞋。格里高力笑了笑,坐到饭桌前。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想对格里高力解释解释,就又气呼呼地说了几句:
“她骂得非常难听,简直叫人说不出口!我当时真想转回去,拿鞭子抽她一顿,可是有格里高力在场,这样做总是有点儿不大合适。”
彼特罗开了门,杜尼娅用腰带牵进来一头白头顶的红牛犊。
“到油饼节,咱们就能吃到奶油烙饼啦!”彼特罗用脚踢着小牛,快活地叫道。
吃过饭以后,格里高力解开大口袋,把带的礼物分给家里人。
“这是给你的,妈妈……”他递给她一条毛披巾。
伊莉尼奇娜像年轻人那样皱着眉头、红着脸,接过礼物。
她把披巾披到肩上,对着镜子转悠起来,肩膀一个劲儿地扭来扭去,把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都惹火了,他骂道:
“老妖精,也照着镜子臭美起来啦!呸!……”
“爹,这是给你的……”格里高力急忙说,并且当着大家的面,转悠着一顶崭新的哥萨克帽,那帽子的帽顶高高的,还镶着火红的帽箍。
“哦,我的天!我就缺帽子呢。今年铺子里就没卖过帽子……夏天不管怎样都好说……戴一顶旧帽子上教堂简直丑死啦。这顶旧帽子给稻草人戴戴,倒是挺不错,可是我还一直戴着呢……”他用生气的语调说,一面瞅着大家,好像生怕有谁走过来,把儿子送的礼物抢了去。
他本来想到镜子跟前去试帽子,可是伊莉尼奇娜拿眼睛盯住了他。老头子发现了她的目光,来了一个大转身,一瘸一拐地朝火壶走去。他把帽子歪戴在头上,对着火壶照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老东西?”伊莉尼奇娜报复说。
但是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涎着脸说:
“哎哟哟!瞧,你真浑!你没看到这是火壶,不是镜子吗?噢,噢,是啰!”
格里高力给妻子的是一段做裙子的呢料;给孩子们一人一盒蜜饯;给妲丽亚的是一副带宝石的银耳环;给杜尼娅的是一段上衣料;给彼特罗的是一盒子纸烟和一磅烟丝。
在女人们嘁嘁喳喳地研究着礼物的时候,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就像黑桃皇后一样在厨房里来来回回地走着,甚至还挺着胸膛说:
“瞧,御林军哥萨克团的哥萨克!得过奖的!皇帝阅兵时得过头奖!得过马鞍和全部军用品!嘿,你瞧瞧!……”
彼特罗咬着小麦色的胡子,欣赏着父亲的高兴样子,格里高力嘻嘻笑着。三个人抽起烟来,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担心地朝窗外看了看,说:
“趁亲戚和街坊都还没有来……你把那边的事讲给彼特罗听听。”
格里高力把手一甩。
“正打着呢。”
“布尔什维克眼下在哪儿?”彼特罗坐舒服些,问道。
“齐霍列茨克、塔干罗格、沃罗涅日——这三方面都有。”
“哦,你们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有什么打算?为什么让布尔什维克来咱们这地方?贺里散福和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回来啦,乱七八糟的话他们说了不少,不过我不相信他们的话。那儿好像有点儿不大对头……”
“革命军事委员会软弱无力。哥萨克们都往家里跑。”
“就是说,因为这样,革命军事委员会就要依靠苏维埃吗?”
“当然,就是因为这样。”
彼特罗沉默了一会儿;他又抽起烟,对直地看了看弟弟,问道:
“你拥护哪一方面呢?”
“我拥护苏维埃政权。”
“混账!”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像火药一样爆炸了。“彼特罗,你教训教训他!”
彼特罗笑了笑,拍了拍格里高力的肩膀。
“他是咱们家的霹雳火,是一匹没有驯服的烈马。爹,你能教训得了吗?”
“我用不着谁来教训!”格里高力生起气来。“我又不是瞎子……咱们村子里当过兵的,有些什么看法?”
“这些当兵的,有什么好说的!像贺里散福这样的糊涂虫,你还不知道吗?他能懂得什么?大伙儿全都迷了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糟透啦!”彼特罗咬起小胡子。“眼看春天就要到啦,一切都还乱糟糟的……咱们在前方也当过一阵子布尔什维克啦,现在该学学聪明啦。‘我不犯人,休来犯我。’——哥萨克应该对一切胆敢侵犯我们的人这样说。你们在卡敏镇搞得很糟。你们和布尔什维克勾勾搭搭,布尔什维克就要推行他们那一套。”
“格里什卡,你要好好想一想。你不是一个糊涂小子。你应该明白,哥萨克既然是哥萨克,就永远是哥萨克。不能叫臭庄稼佬来管咱们。你该知道,外来户这会儿在想什么。他们要把所有的土地按人口平分。这怎么行呢?”
“扎了根的外来户,老早就住在顿河地区的,应该分到土地。”
“分给他们鸡巴!叫他们去啃吧!……”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做了一个瞧不起的手势,把指甲老长的大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在格里高力的鹰钩鼻子前面摇晃了半天。
台阶上响起咚咚的脚步声。冻上了冰的门槛也哒哒地响了一阵。安尼凯、贺里散福和戴着一顶高得出格的兔皮帽的伊凡·托米林走了进来。
“老总,你好!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拿酒来!”贺里散福用老大的嗓门儿喊道。
已经在热炕旁边打盹儿的小牛,听了他的喊叫声,吓得哞哞叫起来。小牛滑滑跌跌地用它那还在打颤的四条腿站了起来,用圆滚滚的眼睛望着进来的人,大概是因为害怕,在地上撒了细细的一道尿。杜尼娅轻轻拍了拍小牛的背,小牛才不撒尿了;她扫了扫那一摊尿,放上一口破铁锅。
“你嗓门儿那么大,把小牛都吓坏啦!”伊莉尼奇娜不高兴地说。
格里高力和他们握过手,请他们坐下来。不久,村子的这一头又来了几个人。大家一面说话,一面抽烟,抽得烟雾腾腾,灯光都暗了,小牛都呛得咳嗽起来。
“你们都滚吧!”伊莉尼奇娜骂道:已经是半夜了,她要撵客人了。“你们都给我出去,到外面冒烟去,烟鬼!走吧,走吧!我们家的老总赶了一天路还没有歇歇呢。快滚吧。”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