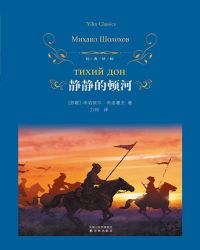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四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四章
司托霍得河下游约四十俄里长的战线上进行着战斗。隆隆的炮声接连不停地响了两个星期。每天夜里,远方紫色的天空被探照灯的灯光划成许许多多的碎块。那探照灯光有如变幻多姿而又不太明亮的闪电,闪来闪去,眨着眼睛,使站在此处观看战争烽烟与火光的人感到无限惊慌。
第十二哥萨克团驻守在一片泥沼的荒凉地段。白天偶尔朝那些在不深的战壕里跑来跑去的奥地利人打几枪,到夜里,靠着泥沼地掩护,就睡大觉或者打牌;只有一些哨兵注视着激战地区那惊心动魄的橙黄色火光。
一个严寒的夜里,远方的火光照耀得天空特别明亮的时候,格里高力·麦列霍夫走出地下室,顺着交通壕爬到战壕后面一座树林子里,那树林子在一座不高的土冈顶上,很像是长在黑头顶上的一撮白毛。他在开阔而芳香的土地上躺了下来。地下室里烟雾腾腾,一片恶臭气,下等烟草的褐色烟雾就像带穗子的桌布,笼罩在一张小桌的上空,桌边围坐着八个哥萨克,正在打牌;可是树林子里,在这小土冈顶上,微风轻轻吹着,轻得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鸟儿飞过时翅膀扇出来的;寒霜打过的野草散发着无限忧郁的气息。炮弹打得乱七八糟的树林子上空黑沉沉的,天上一簇一簇的星星闪闪烁烁,有如篝火熄灭后的余火,北斗星躺在天河的旁边,很像是一辆翻倒在地上、斜翘着辕杆的大板车,只有北面的北极星闪着均匀而耀眼的亮光。
格里高力眯起眼睛望着北极星,这不算明亮、但非常刺眼的星星的冷光一接触到眼睛,睫毛底下就涌出了同样冰冷的泪水。
他躺在这土冈上,不知为什么想起了他从下亚布洛诺夫村回亚戈德庄找阿克西妮亚那一夜;也怀着刀搅一样的痛苦心情想起了她。脑海里出现了那张脸的模模糊糊、经过时间磨蚀的无比亲切而又十分陌生的线条。他怀着突然怦怦跳动起来的一颗心,想重新看看他最后一次看到的、疼得歪歪扭扭、腮上还带着红红的鞭痕的那张脸;但是记忆却硬要把另一种样子的脸送上来,那张脸微微偏着,得意洋洋,笑盈盈的。你看,她慢慢转过头来,用火辣辣的黑眼睛又顽皮又多情地从下面盯着你,两片娇艳而妖媚的红嘴唇悄悄地说着无比亲切和热情的话儿,然后又慢慢将目光移开,转过脸去,那黑黑的脖子上晃悠着两个老大的毛茸茸的发卷儿……他以前就喜欢吻这发卷儿……
格里高力哆嗦着。他觉得,有一会儿他闻到了阿克西妮亚的头发那幽雅醉人的香气;他弯起身子,张大鼻孔闻了闻,哦……不是的!这是陈腐的落叶发出的一股冲鼻子的气息。阿克西妮亚那鸭蛋形的脸渐渐暗淡,渐渐隐没。格里高力合上眼睛,把两个手掌放在疙里疙瘩的地面上,眼睛一眨不眨地对着天边的北极星看了半天,那北极星躲在一棵断松树后面,像一只美丽的蓝蝴蝶抖动着翅膀,在原地飞着。
许多零零碎碎的回忆片段渐渐遮住阿克西妮亚的形象。他想起了他和阿克西妮亚决裂以后,在鞑靼村的家里度过的那几个星期;每天夜里,娜塔莉亚都要如饥似渴、毫无保留地跟他亲热,好像是竭力要补偿以前那种处女般的冷淡;白天,家里人无微不至、几乎像讨好一样地关怀他,村里人见到他这第一个获得乔治勋章的人都十分尊敬。格里高力不论到哪里,也包括在家里,到处都遇到旁边射来的尊敬而惊讶的目光,大家都惊异地望着他,好像不相信他就是那个格里高力,就是当年那个吊儿郎当的小伙子。老年人在集市上跟他说话,就像跟平辈人说话一样,见面时都要脱帽向他还礼;姑娘和媳妇们都带着掩饰不住的钦佩神情打量他那雄赳赳、微微有点弯曲的身姿,打量军大衣上那系在绦带上的十字勋章。他看出来,父亲有时同他上教堂或者到操场上去,跟他走在一起,显然觉得脸上十分光彩。所有这些讨好、尊敬、钦佩构成的又复杂又精致的毒素,把贾兰沙在他心里种下的真理的种子渐渐毒死,渐渐从他思想上消除。格里高力从前方回来时是一个人,走的时候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了。他从吃娘奶的时候就养成、又培育了二十几年的哥萨克气质,战胜了伟大的人类真理。
“格里什卡,我知道嘛,”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在格里高力要走的时候,喝过几杯酒,摩弄着那一头间有黑斑的银发,激动地说:“我早就知道,你会出息成一个好样的哥萨克。在你满一周岁的时候,我就按照哥萨克的老风俗,把你抱到院子里——你还记得不,老婆子?——让你骑到马上。你这个鬼东西用小手一把就抓住了马鬃!……那时候我就猜到,你一定会大有出息。果然出息成人啦。”
格里高力作为一个好样的哥萨克又上了前方;他一面在心里咒骂战争的荒谬,一面忠实地保持着哥萨克的声名。
一九一五年。五月。在奥里霍甫琪克村附近碧绿的草地上,德军第十三钢铁团徒步向俄军攻来。机枪哒哒响着。架在小河边的俄军的一挺重机枪沉重有力地扫射着,第十二哥萨克团投入了战斗。格里高力跟同连的哥萨克们一起排成散兵线前进着,有时回头看看,看到一轮火热的太阳高挂在中午的天空里,又看到另外一个同样的太阳在河湾里,那河湾边上长满一丛丛的藤蔓,好像一张黄黄的羊羔皮。河那边白杨树丛中隐藏着看守马匹的士兵;往前看,便是德国人的散兵线和钢盔上的铜鹰射出的黄黄的亮光。微风吹动着带有野蒿气味的灰白色硝烟。
格里高力不慌不忙地射击着,瞄准瞄得很细心,在射击的间隙里,一面听着排长高喊瞄准的口令,一面从容不迫地把爬到他的军便服袖子上的一只花大姐拂下去。后来就是冲锋……格里高力用包铁皮的枪托子打倒了一个高个子的德国中尉,缴了三个德国兵的枪,并且朝他们的头顶上打了几枪,吓得他们像兔子一样朝河边跑去。
一九一五年七月,他随着一个哥萨克排在拉瓦鲁斯卡雅附近截回了被奥地利人掳去的一个哥萨克炮兵连。就在那一次战斗的时候,他绕到敌人后方,用手提机枪打得进攻的奥地利人四散逃窜。
过了巴扬涅茨以后,他在一次遭遇战中俘虏了一名肥胖的奥地利军官。他把军官像只绵羊一样横放在马上,就朝前跑,一路上闻着军官裤裆里拉的屎散发出的臭烘烘的气味,并且感觉到那吓得浑身是汗的肥胖身体一直在打哆嗦。
格里高力这会儿躺在黑黑的土冈顶上,特别鲜明地想起那一回他跟他的死对头司捷潘·阿司塔霍夫在战场上相遇的情形。那是在第十二团从前线撤下来,调到东普鲁士以后。哥萨克的战马践踏着德国人精耕细作的土地,哥萨克焚烧着德国人的房屋。他们所到之处,火焰红成一片,熏黑的断垣残壁冒着青烟,瓦屋顶劈啪作响。来到司托雷平城下,他们这个团和第二十七顿河哥萨克团一起发动进攻。格里高力仓促中看见瘦了的哥哥、脸刮得很光的司捷潘和其他一些同村的哥萨克。两个哥萨克团打败了。德国人把他们包围起来,十二个连队便一个紧跟着一个勇猛地发起冲锋,想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就在这时候,格里高力看见司捷潘从被打死的大青马身上跳下来,像陀螺一样打起转转儿。格里高力被突然来临的可喜的决心激励着,使劲勒住了马,这时候最后一支连队跑了过来,几乎把司捷潘撞倒,等到这一支连队跑过去,格里高力驱马跑到他跟前,喊道:
“抓住马镫!”
司捷潘紧紧抓住马镫的皮带,跟格里高力的马并排跑了有半俄里。
“别跑得太快!行行好,别这样跑!”他气喘吁吁地恳求道。
他们平平安安地冲出了缺口。离冲出重围的连队下马休息的树林子不过一百丈远了,但就在这时候,一颗子弹打在司捷潘的腿上,他把马镫一松,仰面倒在地上。一阵风吹掉了格里高力的制帽,一绺头发耷拉到眼睛上。格里高力撩开头发,回头看了看。司捷潘正一瘸一拐地朝乱树棵子里跑去,把哥萨克制帽扔进树棵子里,又坐下来,急急忙忙地往下脱那带红绦的军裤。德国人的散兵线正一组一组地从高地下面往上跑,格里高力明白:司捷潘是想活,所以才脱掉哥萨克军裤,这样就可以冒充步兵:因为那时候德国人见到哥萨克就打死,绝不生俘……格里高力受良心驱使,掉转马头,朝树棵子跑去,一面跑一面跳下马来。
“骑上去!……”
司捷潘的眼睛匆匆地扬了一下,那是格里高力永远忘不了的。他扶着司捷潘上了马,自己抓住马镫,跟着满身大汗的马跑起来。
啁啁啁……子弹带着火辣辣的啸声飞来,飞过时又发出啸声:嗖嗖!
在格里高力的头顶上,在司捷潘那煞白的脸的上方,在他们的两旁——都是这种钻和刺的声音:啁啁——嗖嗖,啁啁——嗖嗖;后面是枪声,就像熟透了的槐树荚在爆炸:
砰啪!砰啪!哒哒哒哒!
跑到树林子里,司捷潘下了马,疼得歪着嘴;他扔掉马缰,一瘸一拐地走到一旁。左边的靴筒里往外流着血,每走一步,受伤的腿一用劲,脱落的靴底缝儿里就涌出细细的一股樱桃色的血。司捷潘靠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橡树树干上,朝格里高力招了招手。格里高力走了过去。
“靴子里血都流满啦。”司捷潘说。
格里高力没有做声,朝一旁看着。
“格里什卡……咱们今天往前进攻的时候……听见吗,格里高力?”司捷潘说着,用瘪进去的眼睛寻找格里高力的眼睛。“咱们进攻的时候,我从后面打了你三枪……老天爷没有叫打中。”
他们的眼睛碰到了一起。司捷潘那瘪进去的眼窝儿里气汹汹地射出利钻一样的光芒。他几乎没有张开咬紧了的牙齿,说:
“你救了我的命……谢谢……可是阿克西妮亚的事,我不能饶恕你。心里咽不下这口气……你别强求我,格里高力……”
“我不想强求。”格里高力这才回答说。
他们分手了,依然没有和解……
还有……五月里,他们这个团和布鲁西洛夫军团其余各部一起,在卢次克附近冲破敌军防线,到敌后作战,打击敌人,自己也挨了不少打。在里沃夫附近,格里高力擅自率领一个连去进攻,截获了奥地利人的榴弹炮及其炮手。又过了一个月,有一天夜里,他蹚过布戈河去捉“舌头”。他把一个站岗的哨兵打倒在地,那个矮墩墩的、强壮的德国人把光着半截身子、压在他身上的格里高力转悠了半天,拼命地喊叫,怎么都不肯束手就缚。
格里高力微笑着想起了这件事。
在不久以前和很久以前战斗过的战场上,这样的日子过的还少吗?格里高力牢牢地保持着哥萨克的声名,寻找机会表现舍己忘我的勇敢精神,出生入死,奋勇拼搏,乔装以深入奥地利人后方,偷袭敌人岗哨,多次大显身手,他觉得战争初期压在他心中的那种痛惜人的心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的心变硬了,变得无情了,心就像干旱时候的盐土,水侵不进盐土,怜悯也进不了格里高力的心。他拿别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当儿戏,丝毫也不在乎;因此他成了出名的勇士,得到了四颗乔治十字勋章和四颗奖章。在难得的几次阅兵典礼中,他都站在被多次战争的硝烟熏过的团旗下面;但是他知道,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地笑了;他知道,他的眼睛已经陷下去,两边颚骨已经尖尖地凸了出来;他知道,他很难一面吻着孩子,一面坦然地看着孩子那清亮的眼睛了;格里高力知道,为一大串十字章和几次提升,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他趴在土冈上,把大衣的大襟垫在腰底下,用左胳膊肘支住上身。回忆殷勤地捧献出一样一样的往事,那遥远的童年的往事,就像一根细细的蓝纱,总是跟没有多少滋味的片段战争回忆交织在一起。格里高力带着恋恋不舍和感伤的心情凝神想了一会儿童年的事情,随后又想起不久前的事情。在匈牙利人的战壕里有人熟练地弹着曼陀铃。那细细的、被风吹得悠悠荡荡的声音迅速地飞了过来,飞过司托霍得河,轻轻地飘荡在多次洒过人血的土地上。高空的星星更亮些了,夜色更浓了,沼地上已经升起深夜的雾气。格里高力一连抽完两支烟卷,十分亲昵地抚摩了几下步枪皮带,就用左手的手指头撑着,从殷勤好客的土地上站起来,慢慢朝战壕走去。
地下室里还在打牌。格里高力倒在铺上,还想在回忆中沿着熟悉的、铺满往事的小路漫游一番,但是睡劲儿已经上来;他就着躺倒时很不舒服的姿势睡着了,他梦见无边无际、干旱风吹焦了的原野,梦见一丛丛紫红色的蜡菊,梦见没有钉掌的马蹄在毛蓬蓬的紫薄荷丛里踩出的一个个马蹄印子……原野上空空荡荡,静得不得了。格里高力在硬邦邦的沙土地上走着,但是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因此他害怕起来……格里高力醒了过来,抬了抬头,因为睡得不舒服,腮上印了好几道斜斜的印子,他吧嗒了半天嘴,就好像一匹马刚刚闻到一种特别好闻的草香,忽然这香味又没有了。后来他睡熟了,再没有做梦。
第二天,格里高力起得身来,心里说不出的苦闷。
“你今天怎么愁眉不展的?梦见家乡了?”“秃子”问道。
“你猜对啦。梦见草原啦。所以心里闷得慌……能回家去看看才好哩。给皇上当兵真当够啦。”
“秃子”大大咧咧地笑了笑。他一直跟格里高力住在一个地下室里,他对格里高力十分尊敬,就像一只猛兽尊敬跟它一样凶猛有力的野兽那样;自从一九一四年那一次争吵以后,他们之间再没有发生过冲突,而且,“秃子”的影响已经在格里高力的性格和心理上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战争大大地改变了“秃子”的世界观。他慢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转到反对战争的立场上,他经常议论卖国的将军们和潜伏在皇宫里的德国人。有一回他无意中说出这样的话:“既然皇后本人就是日耳曼血统,就别想有什么好结果。一旦时机来到,有人出一个铜板,她就能把咱们卖掉……”
有一回格里高力对他说了贾兰沙的主要论点,“秃子”却很不赞成。
“歌儿倒是挺美,就是嗓门儿哑啦。”他嘲讽地笑着,拍着他那灰白色的秃顶说。“米沙·柯晒沃依也像一只站在篱笆上的公鸡,天天在唱这种调调儿。这种革命毫无意思,全是胡闹。你要明白,咱们哥萨克需要的是自己的政府,而不是别人的政府。咱们需要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那样刚强的皇帝,咱们跟庄稼佬不能走一条路,猪鹅不能同群嘛。庄稼佬一心想抢夺土地,工人是想给自己增加工资,有什么好处给咱们呢?土地咱们有的是!此外还要什么呢?没有什么好要的,皇上是个昏君,这没有什么好瞒的。他的老子比他强些,他可是胡搞,要搞出像一九〇五年那样的革命,那时候就要把一切弄个天翻地覆。这对咱们没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们把皇上赶走了,下一步就轮到咱们了。他们要报旧仇,还要把咱们的土地分给庄稼佬。要当心……”
“你老是往偏处想。”格里高力皱着眉头说。
“你净说没意思的话。你还年轻,没有磨炼出来。你等着瞧吧,等到你吃了大亏,那时候你就知道谁对谁不对啦。”
谈到这里,谈话一般都要结束了。格里高力一声不响,“秃子”找点别的话来说。
那一天,格里高力卷入了一桩很不愉快的事件。那一天中午,跟往常一样,从土冈那边过来的随军灶车停了下来。哥萨克们你追我赶地顺着交通壕朝灶车跑去。米沙·柯晒沃依打的是第三排的饭。他用一根长棍子挑着许多热气腾腾的锅子,一跨进地下室的门,就叫喊起来:
“弟兄们,这样可不行!怎么,难道咱们是狗吗?”
“你说什么?”“秃子”问道。
“拿臭东西给咱们吃!”柯晒沃依气愤地叫道。
他使劲一甩头发,把他那像一把乱草似的金发甩到后面,把锅子放到铺上,拿眼睛斜看着“秃子”说:
“你闻闻,这汤什么味道?”
“秃子”趴到自己的锅子上,翻着鼻孔,撇着嘴,柯晒沃依不由地学起他的样子,翕动着鼻孔,脸呆呆地皱了起来。
“臭肉。”“秃子”断定说。
他厌恶地把锅子推开,看了看格里高力。
格里高力一下子从铺上站起来,朝菜汤伸了伸本来已经耷拉得够长的鼻子,身子向后仰了仰,懒洋洋地踢了一脚,把前面的一个锅子踢到了地上。
“这是干什么?”“秃子”迟疑地说。
“干什么——你没看见吗?你就瞧瞧吧。你不是瞎子吧?这是什么玩意儿?”格里高力指了指在脚底下流了开来的黏糊糊的东西。
“啊啊啊啊!……蛆!蛆!……我的妈呀……我还没看见呢!……这伙食真不赖。这不是菜汤,是面条……拿蛆当起牛杂碎来啦。”
在地上,在像脓血一样红红的肉块旁边,有不少雪白的蛆,直挺挺地躺在许多油点子中间,蛆已经煮死了,一个个鼓膨膨、圆滚滚的。
“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柯晒沃依不知为什么小声数了起来。
有一小会儿大家都没有做声。格里高力从牙缝儿里啐了一口。柯晒沃依把刀拔了出来,说:
“咱们带上这菜汤,找连长去。”
“好!说得对!”“秃子”表示赞成。
他忙活起来,一面往下拧刺刀,一面说:
“咱们来押送菜汤,格里高力,你跟在后面。你报告连长。”
“秃子”和米沙·柯晒沃依用刺刀抬着满满一锅菜汤,把大刀也拔出了鞘。格里高力在后面护送,哥萨克们从地下室里跑了出来,跟在格里高力后面,像一道连绵不断的灰绿色波浪,顺着弯弯曲曲的战壕移动着。
“怎么回事儿?”
“有情况吗?”
“是不是有讲和的消息啦?”
“哪儿有这样的好事……你想讲和,不想吃干面包啦?”
“我们押送的是带蛆的菜汤!”
来到军官住的地下室门口,“秃子”和柯晒沃依站了下来,格里高力弯了弯腰,用左手拿着制帽,走进“狐狸洞”。
“别挤!”“秃子”回头看着一个在挤他的哥萨克,凶狠地龇了龇牙。
连长走了出来,一面扣着军大衣,一面大惑不解并且有点儿慌乱地回头看着从地下室里跟了出来的格里高力。
“弟兄们,怎么回事儿?”连长用眼睛朝哥萨克们的头顶上扫了扫。
格里高力跨到他前面,在一片寂静中回答说:
“我们押送犯人来啦。”
“什么犯人?”
“就是这个……”格里高力指了指放在“秃子”脚下的一锅菜汤。“这就是犯人……你闻闻吧,人家给您的弟兄们吃的是什么!”
他的眉毛皱成了不等边三角形,微微颤动了两下之后,就舒展开了。连长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格里高力脸上的表情;又阴沉着脸,把目光移到锅子上。
“叫我们吃起臭肉来啦!”米沙·柯晒沃依愤怒地叫道。
“把军需撤掉!”
“毒蛇!……”
“坏蛋,自己吃肥啦!”
“牛腰子汤他自己喝足啦……”
“给别人喝带蛆的!”旁边几个人附和说。
连长等到闹哄哄的声音静了下来,这才厉声说:
“安静点儿!现在别说啦!都清楚啦。今天就把军需撤下来。我派一个小组调查他的情况。如果他拿变质的肉……”
“把他送军法处!”后面嗡嗡叫了起来。
又是一阵闹哄哄的叫喊声把连长的声音吞没了。
撤换军需是在行军的路上。骚动起来的哥萨克们押解着菜汤去见连长之后,过了几个钟头,十二团团部就接到命令撤离阵地,并且按照命令中所附的路线,以行军的队形向罗马尼亚移动。夜里,西伯利亚的步兵就来接替了哥萨克的防务。团队在伦维契镇检查了一下马匹,第二天早晨就用强行军的速度向罗马尼亚进发。
为了支援节节失利的罗马尼亚人,调动了大批的部队。这在行军的第一天,从一件事情上就看出来了。黄昏前派出去到行军路程表上拟定的宿营村庄打前站的人,空着手回来了:那个村子里已经住满了步兵和炮兵,也都是朝罗马尼亚边境开拔的。十二团为了找地方宿营,只好多走了八俄里。
走了十七天。马匹吃不到草料,都饿瘦了。靠近前线的地区,遭到战争破坏,是找不到饲料的;居民不是跑到俄罗斯内地,便是躲进了大森林,敞着门的一座座阴郁的茅屋里,只剩下黑黑的、光秃秃的四壁,街道上空空荡荡,哥萨克们难得遇上个愁眉苦脸、恐慌万状的居民,即使遇上了,对方一看到是带枪的,就赶快躲起来。哥萨克们因为连续行军,都弄得疲惫不堪,又因为冻得难受,因为自己受罪,马匹受罪,因为种种不顺心的遭遇,憋着一肚子的怨恨,所以掀掉了许多茅屋的屋顶;遇到劫后幸存的村庄,他们就不客气地抢夺那十分可怜的粮食,不管军官们怎样恐吓,都制止不住他们的抢劫和胡作非为。
已经离罗马尼亚边境不远了,在一个富裕的小村子里,“秃子”从一家仓房里偷了一升大麦。主人当场把他抓住,但是“秃子”把那个挺和善的比萨拉比亚老汉狠狠打了一顿,大麦还是送到了马跟前。排长在拴马桩跟前看到了他。“秃子”把饲料袋挂到马嘴前面,自己在旁边转悠着,用哆哆嗦嗦的手抚摩着露出骨头的马肋,看着马的眼睛,就像对着一个人似的。
“乌留宾!狗杂种,把大麦送回去!你这个混蛋,干这种事儿要枪毙!……”“秃子”用模糊的眼睛斜着看了看排长,把制帽叭地朝脚下一摔,进团里以来第一次声嘶力竭地大叫起来:
“惩治我吧!枪毙我吧!你就是马上把我打死,大麦也不送还!……怎么,我的马就该饿死吗?嗯?大麦我就是不还!一颗也不还!”
他忽而抓抓自己的脑袋,忽而抓抓大吃大嚼的马的鬃毛,忽而抓抓马刀……
排长一声不响地站了一会儿,看了看瘦得可怕的马后腿,点了点头,说:
“你怎么给跑得发热的马吃起东西来啦?”
他的声音中明显地流露出激动的心情。
“不要紧,马身上已经凉透啦。”“秃子”几乎用说悄悄话儿的声音回答说,一面把饲料袋里掉下来的麦粒儿扫到手掌上,重新放进去。
十一月初,十二团进入了阵地,特兰斯瓦尼亚山上寒风呼啸,山谷里飘荡着冷雾,霜打过的松林发出浓烈的气息,在山里洁白的初雪地上,常常看到野兽的足迹:狼、麋鹿、野山羊,受到战争的惊吓,纷纷离开荒野的山林,向内地逃去。
十一月七日,十二团向三二〇高地发动了进攻。前一天还是奥地利人守在战壕里,可是就在发动进攻的这一天早晨,刚从德法前线上调来的德国人接替了他们。哥萨克们徒步向山坡上爬去,山坡上到处是石头,蒙着一层薄薄的雪。带冰凌的小石头在脚下乱蹦,一股股的雪粉乱飞。格里高力跟“秃子”并排走着,惭愧地、很不好意思地笑着,对他说:
“我今天有点儿怕……好像是头一次打仗。”
“是吗?……”“秃子”觉得很稀奇。
他攥着步枪皮带,提着磨得光溜溜的步枪,咂着胡子上的冰凌。
哥萨克们排成不整齐的散兵线向山上移动着,还没有开枪。敌人战壕的胸墙阴森可怖地沉默着。在山头后面,德国人这边,有一个萨克森 中尉,脸被风吹得红红的,鼻子也脱了皮,整个身子向后仰着,微微笑着,神气活现地对士兵们喊道:
“伙计们!咱们打蓝衣鬼 不是头一回啦!咱们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叫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沉住气,暂且不要开枪!”
一支一支的哥萨克连队向前冲去。小石子在脚下哗啦哗啦地乱飞。格里高力一面掖风帽的角儿,一面神经质地笑着。他那瘪下去的两腮和鹰钩鼻子泛着青黄色,满腮的胡子就像黑黑的庄稼茬子,挂着白霜的眉毛底下,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就像两块黑炭。他已经失去素有的镇定心情。他克制着突然涌来的可恶的害怕心情,眯着晃动不定的眼睛,凝神望着白白的、雪光闪闪的战壕胸墙,对“秃子”说:
“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是让我们走近些。我害怕,而且也不觉得惭愧……说不定会突然转过身,朝后跑。”
“你今天怎么胡说起来啦?”“秃子”气呼呼地说。“老弟,干这种玩意儿就好比打牌:自己信不过自己,就会叫人吃掉。格里什卡,你的脸都黄啦……你也许是病啦,也许……今天你要遭殃。小心点儿!知道吗?”
有一个穿短大衣、戴尖顶钢盔的德国人挺直身子在战壕里站了一下子,又重新趴了下去。
格里高力左边,是叶兰乡的一个淡黄色头发的漂亮哥萨克,他一面走,一面把右手的手套忽而拉下来,忽而又戴上去。他不停地重复着这种动作,匆匆忙忙地走着,两腿很吃力地打着弯儿,故意大声地咳嗽着。“就像是一个人深夜里走路……故意咳嗽,给自己壮胆。”格里高力听着他咳嗽,心里这样想着。这个哥萨克那边,是马克萨耶夫中士的雀斑脸,再过去,是叶麦里扬·格洛舍夫,他紧紧端着步枪,枪上的刺刀尖歪到了一边。格里高力想起来,几天以前,在行军的路上,叶麦里扬就是用这把刺刀撬开仓房的锁,偷了罗马尼亚人一口袋玉米,差不多紧挨着马克萨耶夫的是米沙·柯晒沃依。他一个劲儿地抽烟,不住地擤鼻涕,擤过了,手指头就在军大衣左襟的外面一擦。
“我想喝水。”马克萨耶夫说。
“叶麦里扬,我的靴子夹脚。走起路来真受罪。”米沙·柯晒沃依抱怨说。
格洛舍夫恶狠狠打断他的话头:
“这会儿别谈靴子啦!忍着点吧,德国人的机枪就要扫过来啦。”
一阵枪声响过,格里高力就中了子弹,哎呀一声,倒在地上。他想要绑扎一下受伤的胳膊,就探手到军用袋里去摸绷带,只觉得袖子里有一股热辣辣的血从肘部汩汩地直往外冒,身子就软了下来。他趴在地上,把沉甸甸的脑袋藏到一块石头后面,用干燥的舌头舔了一下毛茸茸的雪团。他用哆哆嗦嗦的嘴唇拼命啜吸松散的雪粉,倾听着尖利刺耳的子弹啸声和一片轰隆轰隆的枪声,感到非常恐怖,全身哆嗦得非常厉害。他抬起头来,就看见同连的哥萨克们在往山下跑,滑滑跌跌,踉踉跄跄,胡乱地朝后或朝上放着枪。一种无法说明、也无法解释的恐怖,使格里高力站起身来,又使他朝下面参差不齐的松林边缘跑去,他们的团就是从那儿发起进攻的。格里高力跑到了搀扶着受伤的排长的叶麦里扬·格洛舍夫前头。叶麦里扬搀着排长在很陡的山坡上跑着,排长的两条腿摇来晃去,像醉汉一样,有时还趴在叶麦里扬的肩膀上,吐几口黑黑的血块子。一支一支的连队像雪崩一样朝松树林滚去。灰灰的山坡上留下一堆堆灰灰的尸体;没来得及带走的伤号就自己往下爬。机枪在后面对着他们扫射。
呜呜呜咔咔咔咔!……密集的枪声一阵猛似一阵。
格里高力由米沙·柯晒沃依搀扶着,走进了松树林。林边一片平缓的斜坡上,子弹乱飞乱蹦。德军左翼有一挺机枪不住气地扫射着。就好像一只有力的手扔出去的石头在刚冻起来的薄冰上跳动着,发出清脆的声音。
呜呜呜呜咔咔咔咔咔!……
“拼命朝咱们打哩!”“秃子”好像很欢迎似的,叫喊道。
他靠在一棵红红的松树干上,懒洋洋地对着在战壕沿上跑来跑去的德国人打起枪来。
“要教训教训那些糊涂蛋!要教训教训!”柯晒沃依一面从格里高力胳膊底下抽自己的胳膊,一面气呼呼地叫道。“狗东西!比狗还坏!等到他们自己流够了血,就明白为什么挨打了。”
“你这是说的什么?”“秃子”眯起眼睛问道。
“聪明人自己能明白,糊涂蛋吗……拿糊涂蛋有什么办法?你拿钉子都揳不进去。”
“你还记得誓词吗?你宣过誓没有?”“秃子”钉着问。
柯晒沃依没有回答,跪了下去,用两只哆哆嗦嗦的手从地上捧起一大捧雪,狼吞虎咽地吃起雪来,身子轻轻抖着,咳嗽着。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