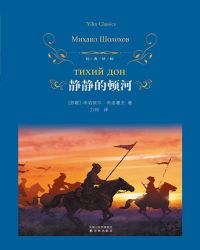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十二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二章
李斯特尼次基的连里有一个布堪诺夫乡的哥萨克,名叫伊万·拉古京。在第一次选举的时候,他当选为团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本团调来彼得格勒以前,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地方,但是在七月下旬,排长就报告李斯特尼次基说,拉古京常常到彼得格勒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军事小组去,大概跟苏维埃有了关系,因为发现他经常跟排里的哥萨克进行谈话,对他们施加有害的影响。排里发生过两次拒绝担任守卫和巡逻的事。排长把这些事都记在拉古京的账上,认为这是哥萨克受了他的影响。
李斯特尼次基认为,他无论如何都要进一步了解一下拉古京,摸一摸他的底。公开把一个哥萨克找来问话,是很笨的办法,也是很不谨慎的,因此李斯特尼次基决定等候机会。机会很快就有了。七月末,轮到第三排担任普梯洛夫工厂附近几条街的夜间巡逻任务。
“我跟弟兄们一块儿去,”李斯特尼次基事先就向排长打招呼说,“请您告诉他们,给我备上那匹大青马。”
李斯特尼次基有两匹马,如他自己说的,“以备万一”。勤务兵服侍他把衣服穿好,他便下了楼,来到院子里。一排人上马出发。在烟雾弥漫、交织着一道道灯光的黑暗中走过了几条街道。李斯特尼次基故意留在后面,从后面叫了拉古京一声。拉古京拉了拉自己那很不起眼的马,走了过来,带着等待的神情从旁边看了看大尉。
“你们委员会里有什么新闻吗?”李斯特尼次基问道。
“什么新闻也没有。”
“你是哪一个乡的,拉古京?”
“是布堪诺夫乡的。”
“哪一个村子呢?”
“米佳金村。”
现在他们的马已经是并排走着了。李斯特尼次基借着路灯的光线斜眼看着这个哥萨克那胡子拉碴的脸。拉古京的制帽下面露出直直的鬓发,鼓鼓的两腮上生着短短的、很不整齐的络腮胡子,两只聪明中透露着狡诈的眼睛,深深地嵌在鼓鼓的眉弓里。
“外表很平常,很不精神,可是他心里究竟怎样呢?大概,他非常恨我,恨一切跟旧制度、跟强权有联系的东西……”李斯特尼次基心里这样想道,并且不知为什么他又很想了解一下拉古京的过去。
“有老婆吗?”
“是的。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
“家业怎么样?”
“我们还有什么家业?”拉古京带着遗憾的语气冷笑说。“日子过得平平常常。一头牛加一个哥萨克,或者是一个哥萨克加一头牛,我们就这样过一辈子……”他想了想,又板着脸补充了一句:“我们的地都是沙土地。”
李斯特尼次基以前上谢列布里亚柯沃车站去,曾经从布堪诺夫乡路过。他清清楚楚地想起了那个远离要道的偏僻的乡。南面是一片平平的、一望无际的草地,旁边环绕着曲曲弯弯的霍派尔河。那时候他在十二俄里以外,在叶兰乡边界的山头上,就看见低洼处那一片绿荫荫的果园,看见一座高大的白色钟楼。
“我们那儿都是一些沙土地。”拉古京叹着气又说了一遍。
“大概很想回家,是吗?”
“当然啦,大尉先生!当然想早点儿回去。打仗受的苦实在不少啦。”
“伙计,恐怕未必很快就能回去……”
“很快就能回去。”
“仗还没有打完啊?”
“快打完啦。回家也快啦。”拉古京硬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还要跟自己人打仗呢。你以为怎样?”
拉古京一直望着鞍头,没有抬眼睛,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问道:
“跟谁打仗呢?”
“要打的人多着呢……至少要跟布尔什维克打。”
拉古京又沉默了老半天,好像是在清脆、轻快的马蹄声中睡着了。他们一声不响地走了有三分钟。拉古京慢慢地、字斟句酌地说:
“咱们跟他们没什么好争的。”
“要是争土地呢?”
“土地够大家种的。”
“你可知道,布尔什维克想干什么吗?”
“听说过一点点儿……”
“要是布尔什维克来打咱们,想夺取咱们的土地,奴役咱们哥萨克,依你看,那又该怎么办呢?你跟德国人打过仗,保卫过俄国呀,不是吗?”
“德国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那么布尔什维克呢?”
“大尉先生,布尔什维克又怎样?”拉古京显然已经拿定了主意,就开口说起来,一面抬起眼睛,对直地寻找着李斯特尼次基的目光。“布尔什维克不会把我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夺走的。我的土地恰好是一个人的份儿,他们不要我的土地……可是,比如说——您可不要生气!——您爹有一万俄亩土地呢……”
“不是一万,是四千。”
“那反正是一样,就算是四千亩吧,难道还少吗?这难道能说是好章程吗?您再往全国看看,像你爹这样的,还多得很。您就想想看,大尉先生,每一张嘴都要吃。您要吃,别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吃。没有一个茨冈人训练马不吃草,说,忍一忍,不吃草也行。于是听话的马就忍,忍呀,忍呀,忍到第十天就死去啦……沙皇时代的章程是很不公正的,对于穷苦老百姓太苛刻啦……割给你爹那么一大块好蛋糕,四千亩,可是他也不是用两个嗓子眼儿吃东西,他也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用一个嗓子眼儿吃东西,当然应该替老百姓抱不平啦!……布尔什维克他们看得很准,可是您还说要跟他们打仗呢……”
李斯特尼次基听着他的话,心里很不平静。到最后他已经明白,他无法提出什么有力的反驳了,他觉得,这个哥萨克已经拿普普通通、简单得不得了的道理把他挤到了墙拐儿上,因此,深深隐藏起来的那种意识到自己不对的感觉又翻腾起来,李斯特尼次基有些慌乱,便发起狠来:
“你怎么,是布尔什维克吗?”
“有没有这样的称号,不算什么……”拉古京冷冷笑着拉长声音回答说。“问题不在于称号,而在于正义。人民需要正义,但是大家都在葬送正义,掩埋正义,说正义早就死啦。”
“你这一套是工农兵苏维埃里的哥萨克教给你的……这么看来,难怪你跟他们结成一伙儿。”
“哎呀,大尉先生,生活本身教给我们这些有耐性的人的东西已经够多啦,布尔什维克不过是点了点灯芯罢咧……”
“用不着开场白!这又不是说书唱戏!”李斯特尼次基已经是怒冲冲地在说话了。“你还是回答我:你说到我父亲的土地,总而言之你说的是地主的土地,然而你要知道,这土地是私人财产。如果你有两件衬衣,我一件也没有,依你看,该怎么办,我就该抢你一件吗?”
李斯特尼次基没有看见,但是从拉古京说话的声音上听出来,他是在笑着。
“我会自动交出多余的那一件。而且在前线我就交出过衬衣,而且还不是多余的,是唯一的一件,我就空心穿军大衣,至于我那一点点土地,好像谁都不想来抢夺……”
“你怎么啦,想要土地吗?你的土地不够种吗?”李斯特尼次基提高声音说。
拉古京脸都白了,激动得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几乎是喊叫着回答道:
“你以为我是为自己操心吗?我们到过波兰,那儿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你看见没有?我们周围的庄稼汉过的又是什么日子?……我可是看见啦!叫人实在痛心呀!……怎么,你以为,我能不可怜他们吗?也许,就因为这个,就因为波兰人,我才心里不是滋味,使我发愁的是他们那点可怜的土地。”
李斯特尼次基本想说几句尖刻的话,可是从灰灰的庞然大物普梯洛夫工厂那边传来尖锐的叫喊声:“抓住!”一阵轰隆轰隆的马蹄声。一声扎耳朵的枪响。李斯特尼次基扬了扬鞭子,放马朝前奔去。
他和拉古京同时跑到聚集在十字路口的本排哥萨克们跟前。一些哥萨克纷纷跳下马来,弄得马刀丁当乱响,一个被他们抓住的人正在当中挣扎着。
“怎么啦?怎么回事儿?”李斯特尼次基喊了两声,一面放马朝人群里冲去。
“这个坏家伙骂我们呢……”
“骂了就跑。”
“揍他,阿尔扎诺夫!”
“哼,你这坏小子!你想找死吗?”
排里的中士阿尔扎诺夫从马上探下身子,抓住那个身材不高、穿着没扎进裤腰的黑衬衣的人的领子。三个下了马的哥萨克把他的手倒剪到背后去。
“你是干什么的?”李斯特尼次基气势汹汹地问道。
被抓住的人抬起头来,在他那灰白色的脸上,两片不说话的嘴唇一撇一撇的,紧紧地闭着。
“你是什么人?”李斯特尼次基又问一遍。“你骂我们吗,坏蛋?嗯?不说话吗?阿尔扎诺夫……”
阿尔扎诺夫从马上跳下来,松开被抓住的人的领子,扬手打了他一个耳光。
“揍他!”李斯特尼次基猛地拨转马头,下命令说。
三四个下了马的哥萨克一面把被捆起来的人往地上按,一面抡起了鞭子。拉古京连忙从马鞍上跳下来,走到李斯特尼次基跟前。
“大尉先生!……您这是怎么啦?大尉先生!”他用打哆嗦的手指头死死地抓住大尉的膝盖,高声叫道:“不能这样!……这是个人啊,您这是干什么呀?”
李斯特尼次基扯了扯马缰,没有说话。拉古京跑到哥萨克们跟前,拦腰抱住阿尔扎诺夫,跌跌撞撞,两腿在马刀上绊来绊去,想把他拉开。阿尔扎诺夫不住地挣着,嘟哝着:
“你别这样好心肠!别这样!他拿石头砸咱们,能饶了他?……放开我!……放开,对你说的是规矩话!……”
一个哥萨克弯下身去,扯下身上的步枪,用枪托子照着倒在地上的那人身上打去,打得叭叭直响。过了一会儿,马路上就响起低低的、像牲口那样粗野的喊叫声。
后来是几秒钟的沉默,然后,依然是那人的声音,但已经有气无力、疼得直抽搭了,那声音在挨打后发出的呼哧声的间隙里,断断续续地喊起来:
“土匪!……反革命分子!……你们打吧!哎哟……啊啊啊啊!……”
叭!叭!叭!……又是一阵毒打。
拉古京跑到李斯特尼次基跟前,紧紧靠在他的膝盖上,用手指甲挠着马鞍的边儿,喘着粗气说:
“做做好事吧!”
“走开!”
“大尉!……李斯特尼次基!……听见没有?你要负责任的!”
“我想啐你一口!”李斯特尼次基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就打着马朝拉古京身上撞。
“弟兄们!”拉古京跑到站在一旁的哥萨克们的面前,高声叫道。“我是团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我命令你们:把人放了,不许打死人!……你们要……要负责任的!……这不是旧时代啦!……”
李斯特尼次基涌起一股强烈的仇恨,顿时失去了理智,什么都不顾了。他照着马的两耳当中抽了一鞭,就朝拉古京冲去。他用乌黑的、散发着枪油气味的手枪抵着拉古京的脸,尖声大叫道:
“住嘴,奸贼!布尔什维克!我毙——了你!”
他极力克制了一下自己,才把手指头从枪机上挪开,把马勒得直立起来,转过马头,跑了开去。
过了几分钟,三个哥萨克也朝他的方向走去。在阿尔扎诺夫和拉宾的两匹马中间,拖着那个穿着紧贴在身上的潮湿衬衣、连脚步也不能迈的人。他的两条胳膊由两个哥萨克架着,身子轻轻摇晃着,两脚划着马路上的石子。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头向后仰着,在高耸着的尖尖的两肩中间摇来摆去,白白的下巴朝上撅着。第三个哥萨克多少走在前面一点。他看见胡同口路灯下面有一辆马车,便在马镫上站起身子,跑了过去,他简短地说了两句什么,又用鞭子拍拍靴筒吓唬了一下,马车夫就连忙乖乖地把马车赶到停在街心里的阿尔扎诺夫和拉宾跟前。
第二天,李斯特尼次基醒来,意识到他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大错误。他咬着嘴唇,想起了殴打那个责骂哥萨克的人的场面,也想起了后来他和拉古京之间发生的事。他皱起眉头,心事重重地咳嗽起来。他一面穿衣服,一面想着主意:目前不应该去动拉古京,以免跟团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关系恶化,最好是等一段时间,等到昨天在场的哥萨克渐渐忘记他跟拉古京的冲突,再悄悄地把拉古京清除掉。
“这就是所说的,跟哥萨克搞好关系……”李斯特尼次基在心里痛苦地嘲笑自己说。并且后来有很多天,他一直很不愉快地想着这件事。
已经是八月初,一个天朗气清、阳光明丽的日子,李斯特尼次基和阿塔尔希柯夫上街闲逛。自从军官们那一天在一起谈过那一次话以后,他们之间出现的隔膜始终没有消除。阿塔尔希柯夫守口如瓶,把没有说出来的那些想法装在心里,李斯特尼次基几次三番想引他推心置腹地谈谈,他都掩着那层厚厚的帷幕,这层帷幕是多数人都很习惯地挂着,用来遮盖自己的真实面貌,不叫别人看出来的。李斯特尼次基常常觉得,有的人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在外表的里面,往往还隐藏着一个叫人一直摸不透的面貌。他坚决相信,剥去任何一个人的表皮,都会露出真诚的、赤裸裸的、没有任何伪装的心灵。因此他总是非常想了解,在各种各样的人那粗鲁的、严肃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蛮横的、心平气和的、愉快的外表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这一回,他想着阿塔尔希柯夫,只猜测着一点:这个人是在现有的矛盾中苦苦地寻找出路,要在哥萨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求调和。他有了这种推测,就不再设法跟阿塔尔希柯夫接近,倒是跟他疏远起来。
他们在涅瓦大街上走着,偶尔地说几句无关紧要的闲话。
“咱们去吃点东西好吗?”李斯特尼次基用眼睛瞟着饭店的大门,说道。
“好吧。”阿塔尔希柯夫表示同意。
他们走进饭店,四下一望,就无可奈何地站住了:所有的桌子都坐满了。阿塔尔希柯夫已经转过身要走了,但是窗户跟前的小桌上有一位衣冠楚楚、由两位妇人陪伴着的胖绅士,仔细看了看他们,便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举着帽子,走了过来。
“请赏光!二位是不是可以到我们的桌子上来坐?我们要走啦。”他笑容可掬,露着稀稀拉拉的熏黄的牙齿,用手势请他们过去。“我很高兴为二位军官先生效劳。你们是我们的光荣。”
坐在桌旁的两个妇人都站了起来。一个高高的、黑头发的撩了撩头发,另一个年轻些的玩弄着小伞,等候着。
两位军官对殷勤让座的绅士道过谢,便走到窗户跟前。一丝丝阳光像黄色的针一样透过放下来的窗帘投射在桌布上。酒菜气味压倒了摆在各个饭桌上的鲜花那幽雅醉人的香味。
李斯特尼次基要的是冰鱼羹,在等待的时候,他若有所思地撕扯着从花瓶里抽出来的一枝橙黄色旱金莲。阿塔尔希柯夫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他那两只疲惫地低垂着的眼睛不住地眨巴着,注视着邻座桌子腿上晃来晃去的太阳光斑。
他们还没有吃完,就有两个军官高声谈着话走进了饭店。
前面的一个在用眼睛找寻空位子的时候,把他那张晒成了均匀的栗色的脸朝李斯特尼次基转了过来。他的两只斜斜的黑眼睛里露出喜色。
“李斯特尼次基!是你呀!……”那个军官一面朝他走来,一面毫不见外、深信不疑地喊叫着。
他的黑胡子下面露出亮闪闪的白牙。李斯特尼次基认出他是加尔梅柯夫大尉,跟着他走过来的是丘鲍夫。他们紧紧地握了握手。李斯特尼次基把两个旧同事给阿塔尔希柯夫介绍过以后,问道:
“哪一阵风把你们吹到这儿来啦?”
加尔梅柯夫捻着胡子,把头向后一仰,斜着眼睛朝两边看了看,说:
“我们是出差来的,详细情形等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你先说说你自己的事吧,十四团里的情形怎么样?”
……他们一同走出饭馆。加尔梅柯夫和李斯特尼次基走在后头,一到胡同口,就拐了进去,半个小时之后,就离开闹市区,一面走,一面小心地四面张望着,小声说着话儿。
“我们的第三军现在在罗马尼亚前线担任后备,”加尔梅柯夫兴奋地说,“一个半星期以前,我接到团长的手令,叫我把连队交出去,跟丘鲍夫中尉一同到师部听候调遣,有意思,我就交出连队。我们一同来到师部。作战处的M.上校,你是认识他的,他很机密地通知我。要我立即去见克雷莫夫将军。我和丘鲍夫一同来到军部。克雷莫夫接见了我,因为他已经知道给他派来的军官是什么人,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下面的话:‘政府里都是一些有意把国家引向死路的人——必须撤换政府的上层分子,可能要用军事专制来代替临时政府。’他还说,接任的人可能是科尔尼洛夫。然后就叫我到彼得格勒来,听候军官联合总会调遣。现在这里已经调集了好几百名可靠的军官啦。你明白,咱们的任务是什么吗?军官联合总会正跟咱们的哥萨克军人联合会密切配合,在一些枢纽站上和一些师里组织突击营。都是在不久的将来要使用的……”
“结果究竟会怎样呢?你是怎么看的?”
“这就怪啦!您住在这里,难道没有弄清局势吗?毫无疑问,政府要来一个大变动,科尔尼洛夫要执政。军队都是拥护他的嘛。我们那儿都这样想:只有两种不同的势力——那就是科尔尼洛夫和布尔什维克。克伦斯基不过是夹在两个磨盘中间,不是这种势力,便是那种势力,会把他碾得粉碎。让他在阿丽萨 的床上暂且睡几天吧。他是一个短命皇帝。”加尔梅柯夫停了一下子,然后,一面若有所思地揪弄着马刀的穗子,说:“我们实际上都是棋盘上的小卒,小卒是不知道下棋人的手把它们往哪儿放的……比如说,我就不完全清楚大本营里目前的情形。我知道,在将军们之间,如科尔尼洛夫、鲁科姆斯基、罗曼诺夫斯基、克雷莫夫、邓尼金、卡列金、爱耳迭里和其他许多将军,在他们之间是有一种秘密的联系和协议的……”
“可是,军队……是不是所有的军队都拥护科尔尼洛夫呢?”李斯特尼次基一面问,一面在加快脚步。
“步兵当然不会。我们可以带动他们嘛。”
“克伦斯基在左派的压力之下,打算撤换最高统帅,你知道吗?”
“他不敢!马上就能叫他乖乖的。军官联合会总会已经相当坚决地把总会对此事的态度告诉了他。”
“昨天哥萨克军人联合会派了几个代表去见他,”李斯特尼次基笑着说,“声明说,哥萨克连撤换科尔尼洛夫的念头都不许有。你可知道,他怎么说:‘这是诽谤。这类的事情,临时政府连想都没想。’他这一面安慰大家,那一面却在向工农兵苏维埃执委会送秋波,就像个窑姐儿一样。”
加尔梅柯夫一面走着,一面掏出一个军官用的战地笔记本,念道:
“‘社会活动家会议特向您——俄罗斯军队的最高领袖致敬。会议声明,一切企图破坏您的军队和俄罗斯的威信的行为都是犯罪的,我们的呼声也就是广大军官、乔治十字章获得者和哥萨克们的呼声。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时刻,俄罗斯一切有头脑的人都怀着期望和信任注视着您。在您重建强大的军队以拯救俄罗斯的伟大壮举中,愿上天多多相助!罗坚柯。’大概,你明白了吧?撤换科尔尼洛夫是根本不可能的……哦,我问你,你看见他昨天进京的场面没有?”
“昨天夜里我才从皇村回来。”
加尔梅柯夫一笑,那整整齐齐的白牙齿和结结实实的红牙花子全露了出来。他那窄窄的眼睛眯了起来,眼角上皱起无数蛛网般的细纹。
“真气派!卫队是一个帖金人的骑兵连。一辆辆汽车上都架着机枪。这都是往冬宫去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警告……嘿嘿嘿。你要是能看见那场面就好啦。嘿,真值得一看!给人的印象真是与众不同。”
他们两人在莫斯科——纳列夫区兜了一个圈子,就分手了。
“叶甫盖尼,咱们应该经常联系。”加尔梅柯夫在分手的时候说。“荒乱年代来到啦。要站稳脚跟,要不然会跌跤的!”
李斯特尼次基已经渐渐走远了,他扭过身子,在背后喊道:
“忘记告诉你啦,你还记得咱们的梅尔库洛夫吗?就是咱们那位画家。”
“他怎么样?”
“五月里他死啦。”
“不可能!”
“他死得实在意外。这种死法顶没意思啦。一个侦察兵的手榴弹在手里爆炸了,把自己的胳膊齐胳膊肘炸掉,可是把梅尔库洛夫炸飞啦,我们只找到他的一部分内脏和一副炸碎的蔡司望远镜。死神只宽限了三年……”
加尔梅柯夫还喊了几句,可是一阵风吹过,卷起一股老大的灰土,送过来的只是模糊不清的尾音。李斯特尼次基挥了挥手,就朝前走去,偶尔地回头望望。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