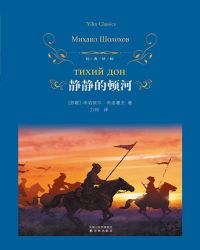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十四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四章
春天里,顿河涨了水,春水淹没了整个河边滩地的时候,鲁别仁村对面高高的左岸有不大的一片地方仍然淹不到水。
春天里,站在顿河边的山上,可以远远地看到一片大水中有一个岛子,岛上生长着密密丛丛的小柳树、小橡树和茂盛的灰白色五蕊柳棵子。
夏天里,那里的树上一直到树顶都缠满了野蛇麻草,下面的地上到处爬满了使人难以下脚的刺莓,一丛丛的树棵子上爬满了浅蓝色的旋花儿,在不多的林中空地上,吸足了肥沃土壤的乳汁的茂草长得比人还高。
夏天里,就是在中午时候,树林里也很安静,很阴暗,很凉爽。打破寂静的只有黄鹂的叫声,再就是布谷鸟争先恐后地不知在对谁诉说难熬的岁月。到冬天里,树林里就空荡荡、光秃秃、一片死静了。参差错落的树头在灰白色的冬日天空映衬下,显得阴沉沉、黑魆魆的。只有狼崽子年年拿密林做可靠的藏身之地,白天就躲在大雪埋住的荒草丛里。
佛明、格里高力·麦列霍夫以及其他几个幸存的佛明匪帮分子就在这个岛上住了下来。他们凑凑合合生活着:吃的是佛明的一个堂弟每天夜里用小船给他们送来的一些可怜的食物,只能吃个半饱,不过睡觉倒是可以枕着鞍垫睡个够。夜里轮流站岗。因为害怕被人发现他们隐藏的地方,所以也不敢生火。
大水绕过小岛,急匆匆地向南流去。大水带着可怕的吼声,穿过一排拦路的老杨树,又带着轻轻的、唱歌般的、安静的淙淙声,摇晃着淹在水里的树棵子枝头。
格里高力对这种一时不停的、很近的水声很快就习惯了。他常常在冲刷得很陡的岸边躺上很久,望着宽阔的水面,望着笼罩在淡紫色阳光中的顿河沿岸的灰白色山岭。在山岭那边,就是自己的村子、阿克西妮亚、孩子们……他的愁闷的心朝那边飞去。他一想起亲人,就心疼如绞,就暗暗地痛恨米沙,但是他尽量压制这种心情,尽量不去看顿河沿岸的山岭,免得又想起来。用不着一个劲儿地去想那些不幸的事。就是不想那些事,他已经够难受的了。就是不想那些事,他的心已经够疼的了。有时候他简直觉得,他的心好像被扎了一刀,心好像都不跳了,直往外流血呢。看来,多次负伤、战争中的苦难和伤寒都在感情上留下了创伤:格里高力每分钟都能听见可厌的心跳了。有时候胸口疼得不得了,疼得嘴唇一下子就干了,他费很大的劲才能忍住,不哼哼出来。不过他想出了一个止疼的好办法:他把左胸压在潮湿的土地上,或者用冷水把小褂打湿,这样疼痛就会慢慢地、好像很不情愿似的离开他的身体。
这些日子天朗气清,风和日丽。在晴朗的天空里,只是偶尔飘过被高空的风撕得蓬蓬松松的白云,白云的影子像一群群天鹅似的在宽阔的水面上滑过,一挨到远处的河岸,就消失了。
如果能看看疯狂旋转的急流在岸边翻腾,听着流水各种腔调的喧闹声,而什么也不想,尽量不去想那些使人痛苦的事情,那倒是很好的。格里高力有时一连几个钟头看着流水旋出的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波纹。水面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形状:有的地方,刚才水平如镜,水面上漂着断芦苇、枯树叶和草根,过一会儿,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旋涡儿,拼命把旁边漂过的一切东西往里吸,可是再过一会儿,在打旋涡的地方,水又向上冒了起来,翻滚出一个个浑浊的水圈儿,忽而吐出一截黑黑的芦草根,忽而吐出一片伸展开的橡树叶,忽而吐出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束干草。
傍晚,西方天空燃烧着红得像樱桃一般的晚霞。月亮从高高的杨树后面升上来。月光像冷冷的白色火焰似的流泻在河面上,在微风吹起细细水波的地方,月光粼粼,在黑暗中闪闪跳动着。夜里,无数北飞的雁群也在岛的上空不停地叫着,雁叫声和水声交织成一片。没有人惊动的禽鸟常常落在岛的东边。在静水里,在淹了水的树林里,公水鸭在呼唤,母水鸭在应和,海雁和大雁也轻轻地咯咯叫着,互相召唤。有一天,格里高力一声不响地走到岸边,看见离岛不远处有很大的一群天鹅。太阳还没有升上来,远方的丛林后面已经露出红红的朝霞。河水经霞光一照,变成了粉红色,这些停在平静的水面上、把高傲的头转向日出的地方的庄严的大鸟也变成了粉红色。天鹅一听见岸上的沙沙声,就用嘹亮的嗓门儿大声叫着,飞了起来,等飞到树林上空,天鹅翅膀那一片雪白耀眼的亮光把格里高力的眼睛都刺花了。
佛明和他的同伴们消磨时间的方法各不相同:很会过日子的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把瘸腿盘得舒舒服服的,一天到晚在补衣服,修鞋子,细细地擦枪擦刀;卡帕林因为不习惯在潮湿地方睡觉,就天天躺在太阳地里,用小皮袄连头蒙住,不停地低声咳嗽着;佛明和丘玛柯夫不知疲倦地在玩用纸画成的自制纸牌;格里高力天天在岛上走来走去,在岸边一坐就是半天。他们彼此很少说话,因为要说的话早就说完了,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和晚上等候佛明的堂弟来的时候,他们才凑到一块儿。他们都十分苦闷,来到岛上的整个时间里,只有一次,格里高力看见,丘玛柯夫和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不知为什么忽然高兴起来,摔起跤来。他们在一个地方闹腾了半天,不住地哼哧着,互相说着简短的玩笑话,他们的脚都踩进白沙里齐踝子骨那么深。瘸子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的力气显然大一些,但是丘玛柯夫却比他灵活。他们用的是加尔梅克式的摔跤法,弯着腰,肩膀向前探着,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对方的腿。他们脸上的神情都很专注,紧张得脸都白了,呼吸又急促又猛烈。格里高力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摔跤。他看到,丘玛柯夫瞅了个机会,突然仰面倒下去,把对方拖倒,然后两腿一弓,就把对方从自己身上翻过去。转眼工夫,像黄鼠狼一样又灵活又敏捷的丘玛柯夫就压到了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的身上,并且把他的两个肩膀拼命往沙里按,而气喘吁吁和哈哈大笑着的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就高声喊叫:“哼,你真浑蛋!咱们可没有说过……可以从头上翻过去……”
“你们像小公鸡一样斗起来了,算了吧,可别打起架来。”佛明说。
他们根本不想打架。他们和和气气地互相搂着,坐到沙地上,丘玛柯夫用低沉然而很好听的粗嗓门儿唱起一支快拍子的跳舞歌来:
啊,严寒呀,严寒!
严寒的三九天呀,
冻死了芦苇里的大灰狼,
冻坏了小屋里的好姑娘……
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用尖细的高嗓门儿跟着唱起来,他们唱得非常和谐,分外好听:
好姑娘走到台阶上,
手里拿着黑色皮大氅,
给马上的战士穿到身上……
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再也憋不住:他跳起来,一面弹着手指头,在沙地上拖着那条瘸腿,跳起舞来。丘玛柯夫一面唱着歌,一面拿起马刀,在沙地上挖了一个不深的坑,这才说:
“等一等,瘸鬼!你一条腿短,在平地上跳起来不方便……你要么在斜坡上跳跳,要么把一条长些的腿放在坑里,另一条腿就在外面。就把长腿放到这坑里吧,来吧,瞧,这样有多好……好,跳起来吧!”
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很听话地把那条好腿放进丘玛柯夫挖的坑里。
“真不错,这样舒服多了。”他说。
丘玛柯夫笑得喘着粗气,拍起手来,用快拍子唱起来:
等你回来,亲爱的,就上我家来,
你来了,我好好地和你亲亲……
于是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的脸上保持着所有跳舞的人都有的那种认真表情,很灵活地跳起舞来,甚至还试着蹲下跳了一阵子……
天天过着一模一样的日子。天一黑,他们就急不可待地盼望佛明的堂弟到来。五个人都聚集在岸边,小声说着话儿,用大衣襟遮着纸烟的火光抽烟。他们决定在岛上再住一个星期,然后乘夜间渡河到右岸去,弄几匹马,到南方去。听说,马斯拉克匪帮正在本州的南部活动呢。
佛明嘱托自己的亲戚去打听,附近哪一个村子里有可以骑的马匹,并且叫他们每天都把州里的情形报告给他。他们得到的消息是令人放心的:红军在左岸搜寻过佛明,也到鲁别仁村来过,但是在佛明家里搜查了一遍以后,马上就走了。
“应该快点儿离开这儿。干吗他妈的老蹲在这儿呀?咱们明天就走,好吗?”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丘玛柯夫提议说。
“首先要把马的事儿摸清楚。”佛明说。“咱们急什么呀?既然有东西给咱们吃,这种日子过到冬天也可以。你们看,这四周围景致多美呀!等咱们休息好了,再去干事情。叫他们去找咱们吧,咱们是不会落到他们手里的。我很后悔,因为我糊涂,把咱们打垮了,当然很难过,不过咱们还没有全完。咱们还能集合起人来!只要咱们一上马,在附近一些村子里一转悠,过一个星期,咱们就有五六十人,也许上百人了。真的,咱们的人会多起来的!”
“胡说八道!糊涂自信!”卡帕林气忿地说。“哥萨克们已经背叛了咱们,过去没有跟着咱们干,今后也不会跟着咱们干。应该有勇气正视现实,不能一味地抱着糊涂希望。”
“他们怎么会不跟着咱们干呢?”
“既然起初不跟着咱们干,现在更不会跟着咱们干了。”
“哼,那咱们还要瞧瞧看呢!”佛明不服气地说。“我决不放下武器!”
“这都是空话。”卡帕林无精打采地说。
“浑蛋!”佛明发起火来,高声叫道。“你干吗要惑乱人心?我讨厌透了你的眼泪!当初你为什么要干?干吗要起事?你既然这样没有种,干吗要充好汉?是你第一个鼓动我起事的,这会儿就想做孬种啦?你干吗不做声了?”
“我和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滚你妈的吧,浑蛋!”卡帕林气急败坏地叫了几句,就冷得把皮袄裹了裹,支起领子,走了开去。
“你们这些高贵的人,都是这样经不住折腾。只要有一点儿波折,就要缩进头去了……”
佛明叹着气说。
他们一声不响地坐了一阵子,倾听着河水均匀而强大的喧闹声。一只母鸭子被两只公鸭子追逐着,紧张地嘎嘎叫着,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去。一小群欧椋鸟很带劲儿地啾啾叫着,朝空地上飞来,但是一看见有人,就像一条黑带子似的在空中绕了个弯儿,向上飞去。
过了一会儿,卡帕林又走了过来。
“我想今天上村子里去一下。”他看着佛明,不住地眨巴着眼睛说。
“去干什么?”
“你问得好怪!你没有看见,我伤风很厉害,几乎站都站不住了吗?”
“哼,那又怎样?到村子里去,你的伤风就好了吗?”佛明不动声色地问道。
“我至少要在暖和地方睡上几夜才行。”
“你哪儿也别去。”佛明强硬地说。
“怎么,我非得死在这儿不可吗?”
“随你怎样。”
“为什么我不能上村子里去呢?在凉地上睡了这些天,快要了我的命啦!”
“要是在村子里把你抓住呢?这一点你想过没有?那就要了我们大家的命了。我还不了解你这个人吗?只要一审问,你就会把我们供出来!也许不等审问,在去维奥申的路上就把我们出卖了。”
丘玛柯夫笑了起来,并且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完全赞成佛明的话。但是卡帕林执拗地说:
“我一定要去。凭你那些神经过敏的推测,说服不了我。”
“我对你说过了:坐下吧,别莽撞。”
“可是你要明白,亚可夫·叶菲莫维奇,我再也不能过这种野兽的生活了!我得了胸膜炎,也许还是肺炎呢!”
“你会好起来的。晒晒太阳,就好了。”
卡帕林生硬地说:
“反正今天我要走,你没有权力拦我,不管怎样我都要走!”
佛明带着可疑的神气眯起眼睛,看了看卡帕林,又朝丘玛柯夫挤了挤眼睛,从地上站了起来。
“卡帕林,你好像是真的有病啊……你大概烧得很厉害呀……来,来,让我来试试:你的脑袋热不热?”他伸出一只手,朝卡帕林走了几步。
显然,卡帕林从佛明的脸上看出他不怀好意,便向后退了几步,厉声叫道:
“滚开!”
“别咋呼!你咋呼什么?我不过是要试试。你干吗发起急来?”佛明一个箭步,掐住卡帕林的喉咙。“想投降吗,坏蛋?”他低声嘟哝着,并且使出全身的力气,要把卡帕林推翻到地上。
格里高力费了很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
吃过午饭以后,格里高力正在把洗过的衣服往树棵子上搭,卡帕林走到他跟前,说:
“我想单独和您谈一谈……咱们坐下来吧。”
他们坐到被大风吹倒的一棵腐烂的杨树上。
卡帕林低声咳嗽着,问道:
“您对这个蠢猪的疯狂举动是怎样看的?我打心里感谢您的帮助。您见义勇为,不愧是一个军官。不过这事儿太可怕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咱们就跟野兽一样……咱们已经有多少天不吃热东西了,还要睡在潮湿地上……我伤风了,肋部疼得要命。我大概生肺炎了。我真想烤烤火,在暖和的屋子里睡睡,换换衣服……我做梦都想着干净的新衬衣、新床单呀……不行呀,我受不了呀!”
格里高力笑了笑。
“您是想舒舒服服地打仗吗?”
“您听我说,这算打的什么仗?”卡帕林很快地接话说。“这不是打仗,这是没完没了的流浪,杀几个苏维埃干部,然后就逃跑。只有等老百姓都拥护咱们,闹起暴动来的时候,那才叫打仗,现在这不是打仗,不是,决不是打仗!”
“咱们没有别的出路呀。咱们总不能投降吧?”
“是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格里高力耸了耸肩膀。他说出了他躺在这小岛上不止一次想过的话:
“不舒服的自由,还是比舒服的监牢好一些。您该知道,老百姓有句俗话:监牢虽然结实,可是只有魔鬼才喜欢它。”
卡帕林用小树枝在沙上画了一些图形,沉默了很久以后,又说:
“不一定投降,不过应该寻找新方式和布尔什维克斗争。应该和这些下贱的家伙分手。您是一个知识分子……”
“哼,我算什么知识分子呀,”格里高力冷笑道,“我连说话都很费劲儿呢。”
“您是军官嘛。”
“这是意外的事。”
“不是,别开玩笑,您是军官,在军官界厮混过,见过一些像样的人,您不是像佛明那样的暴发户,您应该明白,咱们留在这儿没有意思,这等于自杀。他已经叫咱们在橡树林里挨了一次好打,要是咱们还把自己的命运和他捆在一起的话,还要叫咱们挨上好多次打。他是个下流货,又是个大蠢猪!咱们跟着他,就要完蛋!”
“这么说,不是投降,而是要离开佛明了?上哪儿去?去投马斯拉克吗?”格里高力问道。
“不是。这同样也是冒险,不过规模大一点儿罢了。现在我有另外一个看法了。不是去投马斯拉克……”
“那又上哪儿去呢?”
“上维奥申。”
格里高力懊恼地耸了耸肩膀。
“这叫做:重投罗网。这主意我看不中。”
卡帕林用尖锐闪光的眼睛看了看他。
“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麦列霍夫。我可以对您信得过吗?”
“完全可以。”
“您这是一个军官的真心话吗?”
“是一个男子汉的真心话。”
卡帕林朝着在宿营地方晃动着的佛明和丘玛柯夫那边看了看,尽管离他们相当远,他们无论如何都听不见这里的谈话,他还是压低了声音。
“我明白您和佛明以及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您也和我一样,在他们当中是异物。您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原因,我不想知道。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您是因为历史问题,害怕逮捕,不是这样吗?”
“您已经说过,不想知道原因嘛。”
“是的,是的,我这是随口说说,现在我就来谈谈我自己。我以前是个军官,也是一个社会革命党党员,后来我又坚决改变了政治主张……认为只有帝制才能拯救俄罗斯。只能实行帝制!是上天给咱们的国家指明了这条道路。苏维埃政府的国徽是锤子和镰刀,对吧?”卡帕林用树枝在沙上写出“锤子、镰刀”两个词儿,然后用狂热地眨动着的眼睛盯住格里高力的脸:“您倒过来念念。念过了吗?您明白了吧?只有‘皇帝登基’ ,才能结束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政府!您可知道,当我看出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简直神秘得可怕!我浑身直哆嗦,因为,可以说,这是天意,指出咱们这样流窜是根本不行了……”
卡帕林激动得喘不上气来,就不做声了。他那两只尖尖的、隐隐带着发狂神情的眼睛一直盯着格里高力。但是格里高力听了这种启示以后,一点也没有哆嗦,也没有感到神秘得可怕。他看待一切事物一向很清醒,把一切看得很平淡,所以就回答说:
“这不是什么天意。您在俄德战争时期上过战场吗?”
卡帕林被问得窘住了,过了一阵子才回答说:
“说实在的,为什么您要问这个问题呀?没有,我没有直接上战场。”
“战争时期您是在哪儿过的?在后方吗?”
“是的。”
“全部时间都是在后方吗?”
“是的,就是说,虽然不是全部时间,但是也差不多。您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我可是从一九一四年直到今天,都在战场上,中间只有很短的间断时间。那我就来说说天意不天意……要是连上帝都没有的话,还会有什么天意呢?我早就不信这些胡扯的话了。从一九一五年起,我看清了战争的真相以后,也就看出来,上帝是没有的。什么神也没有!要是有的话,就不该让人搞得这样乱七八糟。我们上过战场的人早就不信上帝了,让那些老头子和老奶奶去信吧。让他们找点儿安慰吧。什么天意也没有,恢复帝制也是不可能的。老百姓再也不要帝制了。您刚才搞的这玩意儿,把几个字母倒过来念念,请原谅我直说,这不过是小孩子玩的玩意儿。我有点儿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您对我说干脆些、说简单些吧。我虽然当过军官,可是没有进过士官学校,没有什么文化。如果我有点儿文化的话,也许不会像被大水困住的狼一样,和您坐在这荒岛上了。”他说最后几句话,带着十分遗憾的口气。
“这不要紧,”卡帕林急忙说,“您信不信上帝,不要紧。这是您的信仰问题,您的良心问题。您是保皇党,还是立宪民主党,或者只是一个主张自治的哥萨克——这都没有关系。要紧的是,咱们对苏维埃政府的态度是一致的。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往下说吧。”
“咱们曾经指望发动哥萨克都起来暴动,是吧?这个指望落空了。现在应该摆脱这种处境。以后还可以和布尔什维克斗争,而且也不一定靠什么佛明来领导。要紧的是现在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所以我想和您结成同盟。”
“什么样的同盟?反对谁?”
“反对佛明。”
“我不明白。”
“一切都很简单。我想请您一块儿干……”卡帕林十分激动,说话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了。“咱们杀死这三个家伙,就上维奥申去。明白了吗?这样咱们就可以得救。咱们给苏维埃政府立下这样的功劳,就会得到宽大。咱们就能活下来!您要明白,咱们能活下来!……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当然啦,将来有机会咱们还是要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不过到那时候要认真地干,不能像这样跟着这个倒霉的佛明冒险了。您赞成吗?您要知道,这是咱们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而且是光明的出路。”
“可是怎样下手呢?”格里高力愤怒得浑身直打哆嗦,但是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感情,问道。
“我什么都想好了:咱们在夜里用刀把他们杀了,第二天夜里等那个给咱们送吃食儿的哥萨克来了,咱们就可以渡过顿河,就平安无事了。非常简单,一点儿也不麻烦!”
格里高力装出很亲热的样子,笑着说:
“这太妙了!卡帕林,您告诉我,早上您要上村子里去暖和暖和的时候……您就是想上维奥申去吧?佛明猜对了您的意思了吧!”
卡帕林仔细看了看很亲热地笑着的格里高力,他也笑了,微微带点儿不好意思和不快的神情。
“坦白地说,是的。您要知道,涉及自己的性命问题的时候,是不能好好地选择手段的。”
“您是想出卖我们吗?”
“是的,”卡帕林坦率地承认说,“不过要是在这个岛子上抓住你们的话,我会尽力保护您一个人的。”
“为什么您不一个人把我们干掉呢?夜里干这种事儿很容易嘛。”
“太冒险了。要是枪一响,其余的人就……”
“把家伙放下!”格里高力很沉着地说,一面拔手枪……“放下,要不然我当场把你打死!我现在站起来,用脊背把你遮住,不叫佛明看见,你把手枪扔到我脚底下。听见吗?你别想开枪!你只要一动,我就打死你。”
卡帕林坐在地上,脸色像死人一样白。
“别打死我呀!”他咕哝着煞白的嘴唇,小声说。
“不打死你。要把你的家伙下了。”
“您会把我的事儿说出去的……”
眼泪顺着卡帕林那胡子拉碴的两腮流了下来。格里高力又厌恶又可怜他,不禁皱起眉头,提高嗓门儿说:
“把手枪扔下!我不说出去,不过实在应该说出去!哼,你原来是条毒蛇!哼,真毒呀!”
卡帕林把手枪扔到格里高力脚下。
“还有勃朗宁呢?把勃朗宁也拿出来。就在你的上衣口袋里嘛。”
卡帕林把闪着镍光的勃朗宁手枪也掏出来,扔在地上,用双手捂住脸。他哭得直打哆嗦。
“别哭了,坏蛋!”格里高力使劲压制着要打他的心情,厉声说。
“您会把我的事儿说出去的……我完了。”
“我对你说过,我不说出去嘛。不过只要咱们从岛子上一过了河,你就随便上哪儿去吧。谁也不要你这样的人。你自个儿去找地方安身吧。”
卡帕林把手从脸上放下来。他的一张脸泪汪汪的、红红的,两眼肿了起来,下巴直打哆嗦,那副模样实在可怕。
“那您为什么……为什么缴我的枪呢?”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格里高力很不高兴地回答说:
“这是为了——免得你在背后朝我开枪。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还一个劲儿地说什么天意、皇帝、上帝呢……你这人有多么狡猾呀……”
格里高力也不看卡帕林,时不时地啐着直想吐的唾沫,慢慢朝宿营的地方走去。
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用麻线在缝马鞍的连接带,轻轻地吹着口哨。佛明和丘玛柯夫躺在马衣上,照常在打牌。
佛明匆匆看了格里高力一眼,问道:
“他对你说了什么?你们谈什么来?”
“他不满意这种日子呢……胡扯一通……”
格里高力守信用,没有把卡帕林的事说出来。不过到了晚上,人不知鬼不觉地把卡帕林的步枪大栓卸掉,藏了起来。“谁知道他妈的夜里他会想什么坏主意……”他在躺下睡觉的时候,心里想道。
第二天早晨,佛明把他叫醒了。佛明弯下腰,小声问道:
“卡帕林的家伙是你拿了吗?”
“什么?什么家伙?”格里高力抬起身来,很费劲儿地舒展了一下肩膀。
他在黎明之前才睡着,在黎明时候冻得够戗。他的大衣、帽子、靴子都湿漉漉的,因为太阳一出,雾气一齐凝成水落了下来。
“他的家伙不见了。你拿了吗?你醒醒吧,麦列霍夫!”
“嗯,是我。怎么回事儿?”
佛明一声不响地走开了。格里高力爬起来,抖了抖军大衣。丘玛柯夫在不远的地方做早饭:他涮了涮他们那唯一的一只钵子,把面包按在胸膛上,切成很均匀的四块,把罐子里的牛奶倒到钵子里,又把一大团小米干饭掰碎了,然后朝格里高力看了看。
“麦列霍夫,你今天睡得好香啊。瞧,太阳都升到什么地方啦?”
“良心干净的人,睡觉总是很香的,”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一面在大衣襟上擦着洗干净的木勺子,一面说,“可是卡帕林一夜都没有睡,一个劲儿地翻来翻去……”
佛明一声不响地笑着,看着格里高力。
“请坐下吃饭吧,众位好汉!”丘玛柯夫说。
他头一个舀了一勺子牛奶,啃了一大口面包,格里高力拿起自己的勺子,一面仔细打量着大家,问道:
“卡帕林在哪儿?”
佛明和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一声不响地吃着,丘玛柯夫仔细看了看格里高力,也没有说话。
“你们把卡帕林弄到哪儿去了?”格里高力模模糊糊地猜测着夜里的事情,问道。
“卡帕林这会儿已经离得很远了。”丘玛柯夫不动声色地笑着回答说。“他洑水朝罗斯托夫方面去了。这会儿恐怕已经在霍派尔河口漂着了……你瞧,他的皮袄还搭在那儿呢。”
“你们真的把他杀了吗?”格里高力朝卡帕林的皮袄瞥了一眼,问道。
这事儿本来用不着问了,不问也完全清楚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还是问了。大家没有立即回答他,于是他又问了一遍。
“噢,明摆着的事儿嘛,把他杀啦。”丘玛柯夫用睫毛遮住像女人一样清秀的灰眼睛说。“是我杀的。我就干这种杀人的差事……”
格里高力仔细看了看他。丘玛柯夫那黑中透红、干干净净的脸上的神情很平静,甚至很愉快。他那泛着金光的黄白色胡子,在晒得黑黑的脸上显得异常分明,使黑黑的眉毛和向后梳的头发显得格外黑。这个佛明匪帮中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外表确实很漂亮、很文雅……他把勺子放在帆布上,用手背擦了擦胡子,说:
“麦列霍夫,你谢谢亚可夫·叶菲莫维奇吧,是他救了你的命,不然的话,你这会儿也和卡帕林一块儿在顿河里漂着了……”
“这是为什么?”
丘玛柯夫慢慢地、从容不迫地说起来:
“看样子,卡帕林是想投降,昨天和你谈了半天,不知谈的是什么……所以我和亚可夫·叶菲莫维奇就想把他收拾掉,省得他造孽。可以全部告诉他吗?”丘玛柯夫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佛明。
佛明点头表示同意,于是丘玛柯夫一面咯吱咯吱地嚼着夹生的小米饭,一面说下去:
“天一黑,我就准备好一根橡树棒子,对亚可夫·叶菲莫维奇说:‘今天夜里我把卡帕林和麦列霍夫他们两个都干掉。’可是他说:‘你把卡帕林结果了吧,别动麦列霍夫。’我们就这样商量定了。我注视着卡帕林,等他睡着了,我听了听,你也睡着了,还打呼噜呢。我就爬过去,照他的脑袋就是一棒子。咱们的上尉连腿都没有动弹一下!舒舒服服地把身子一伸,小命就完了……我们悄没声地在他身上搜了搜,然后就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拖到岸边,脱掉靴子、上衣和皮袄,把他扔到水里。可是你还一个劲儿在睡呢,睡得什么也不知道……麦列霍夫,昨天夜里死神可是离你很近哩!死神已经站在你头顶上了。虽然亚可夫·叶菲莫维奇说不要动你,可是我想:‘他们白天谈了些什么呢?五个人里面有两个人躲得远远的去说秘密话儿,就不会有好事情……’我悄悄走到你身边,已经想一棒子砸下去了,可是我一想:砸一棒子,可是你是个很结实的家伙,要是一棒子砸不死,你就要跳起来,开枪……这时候又是佛明把我拦住了。他走过来,小声说:‘别动他,他是咱们的人,可以信得过他。’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我们就是不明白:卡帕林的家伙哪儿去了呢?我就这样离开了你。嘿,你睡得可是真死呀,根本不知道可能会倒霉!”
格里高力很平静地说:
“你这浑蛋,打死我可真冤枉!我可是没有和卡帕林串通。”
“那为什么他的家伙在你手里呢?”
格里高力笑着说:
“白天我就把他的两支手枪缴来了,步枪大栓是在晚上卸下来,藏在鞍垫底下的。”
他把昨天和卡帕林谈的话以及卡帕林的主意说了一遍。
佛明很不满意地问道:
“这事儿你为什么昨天不说呢?”
“我有点儿可怜这个没出息的家伙。”格里高力坦白地承认说。
“噢呀,麦列霍夫呀,麦列霍夫!”着实吃惊的丘玛柯夫叫了起来。“你该把你的怜悯心收起来,跟卡帕林的枪栓一起藏到鞍垫底下,要不然你会因为怜悯心倒霉的!”
“你别教训我吧,我的事儿我知道。”格里高力冷冷地说。
“我为什么要教训你吗?你想想,如果因为你这种怜悯心,昨天夜里糊里糊涂把你送上西天,那可怎么办呢?”
“那也算活该。”格里高力想了想,小声回答说。后来又说了两句,与其说是说给别人听的,不如说是自言自语:“在清醒的时候死,是很可怕的;在睡着了的时候死,一定很舒服……”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