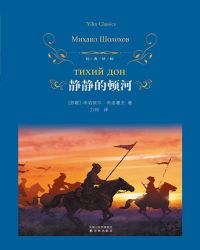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十五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五章
四月底的一天夜里,他们坐小船渡过了顿河。下柯里夫村的一个年轻哥萨克亚历山大·柯舍辽夫,正在鲁别仁村的岸边等候着他们。
“我要跟你们干,亚可夫·叶菲莫维奇,我在家里呆不下去。”他一面和佛明打招呼,一面说。
佛明用胳膊肘捣了捣格里高力,小声说:
“看见吗?我说的嘛……不等咱们从岛子上过来,这不是,就有人等着了!这是我的朋友,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哥萨克。好兆头啊!这么看,事情大有希望呢!”
从口气上来判断,佛明够开心的。他因为来了新同伙,显然十分高兴。因为顺利地过了河,而且马上就有人来参加,他一下子就提起了精神,增添了新的希望。
“嘿,你不光有步枪和手枪,还有马刀和望远镜啊?”他在黑暗中打量着、摸索着柯舍辽夫的家伙,很满意地说。“真是一个好哥萨克!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是真正的哥萨克,一点儿也没有掺假!”
佛明的堂弟把一辆套着一匹小马的大车赶到岸边。
“把马鞍都放到车上吧,”他小声说,“快点儿,为了基督,时候已经不早了,咱们的路还不近呢……”
他很着急,一个劲儿地在催促佛明,可是佛明从岛上来到岸上,一踏上自己村子的土地,就觉得心里踏实起来,觉得不妨回家去看一下,也看看村里的一些熟人……
天亮以前,他们在红莓村旁边的马群里挑选了几匹好些的马,上了鞍。丘玛柯夫对看马的老汉说:
“老大爷,你不要因为马的事儿太难过。这几匹马也算不上多么好,我们不过凑合着骑骑罢了,等我们弄到好些的,就把这马归还原主。如果原主问:是谁把马赶走的?你就说:克拉司诺库特镇的民警弄走啦。就让马的主人上那儿去要吧……你就说,我们骑上赶土匪去了!”
他们和佛明的堂弟道过别,就上了将军大道,后来向左拐弯,五个人就放开马朝西南奔去。听说,马斯拉克匪帮最近在麦石柯夫镇附近出现过。佛明决定去加入这个匪帮,所以就径奔西南方。
他们为了寻找马斯拉克匪帮,在右岸的草原道路上游荡了三天,避开大的村庄和市镇。在和卡耳根乡搭界的塔甫里亚人的村子里,弄到几匹又肥又壮、脚步很快的马,把原来那几匹不大好的马换了下来。
第四天早晨,在离维沙村不远的地方,格里高力头一个发现远处的山口上有一队正在行进的骑兵。在大道上行进的至少有两个骑兵连,前面的两侧还有几小队侦察兵。
“也许是马斯拉克,也许是……”佛明拿起望远镜。
“也许是雨,也许是雪,也许是,也许不是。”丘玛柯夫用嘲笑的口气说。“你还是好好地看看吧,亚可夫·叶菲莫维奇,如果那是红军,咱们还要赶快向后转呢!”
“这么远,谁他妈的能看得清他们!”佛明很懊丧地说。
“你们瞧!他们看见咱们了!有一队侦察兵正朝这儿跑呢!”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叫道。
的确已经看见他们了。在右侧行进的一队侦察兵转了一个陡弯,飞马朝他们奔来。佛明急忙把望远镜放进套子里,但是格里高力笑着在马上探过身子,抓住佛明的马笼头。
“先别急!让他们走近一点儿。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咱们先看清楚再说,如果不对头,要跑也来得及。咱们骑的是新换的马,你怕什么?拿望远镜仔细看看!”
十二名骑兵越走越近,他们的身形越来越大。在生满嫩草的山坡绿色的背景上,他们的身形已经显得非常清楚了。
格里高力和其余几个人都焦急地看着佛明。佛明那拿着望远镜的两手轻轻哆嗦着。他非常紧张地眺望着,紧张得有一滴眼泪顺着那朝太阳的一边腮帮子流了下来。
“是红军!帽子上有星!……”终于佛明低声喊道,并且立即拨转了马头。
他们飞跑起来。零零落落的枪声在他们背后响起来。格里高力和佛明一块儿跑着,偶尔回头望望,跑出有四俄里。
“咱们会合得真不坏!……”格里高力用嘲笑的口气说。
佛明沮丧得一声不响。丘玛柯夫轻轻地勒了勒马,叫道:
“应该避开村子!咱们到维奥申乡牧场上去,那儿僻静些。”
他们又疯跑了几俄里,马渐渐没有力气了。伸得长长的马脖子上冒出一团团的汗沫,显出一道道很深的皱纹。
“要跑慢点儿!把马勒一勒!”格里高力说。
后面的十二个骑兵只剩下九个了,其余几个落在老后面了。格里高力用眼睛打量了一下他们之间的距离,就喊道:
“站住!咱们来把他们打退!……”
五个人都让马换成了小跑,一面跑一面下了马,摘下步枪来。
“拉紧缰绳!瞄准尽左边一个……开火!”
他们各打了一梭子,打死了一名红军骑的马,他们又上马跑起来。红军已经不怎么想追赶他们了,时不时地远远地打上几枪,后来就不再追了。
“要饮饮马了,那儿有一个水塘。”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用鞭子指着远处泛着一片碧色的一个草原水塘,说。
现在他们已经是让马一步一步地走了。他们细心地注视着迎面的洼地和山沟,尽量拣地势不平、可以隐蔽的地方走。
他们在水塘里饮过了马,又上路了,起初是一步一步地走,过了一会儿就小跑起来。晌午时候,他们在一片斜穿草原的很深的谷地的斜坡上停下来喂马。佛明吩咐柯舍辽夫步行到附近一个土冈上去,趴在那里担任警戒。如果草原上有什么地方出现骑兵,柯舍辽夫就发信号,并且立即跑到喂马的地方来。
格里高力把自己的马腿绊起来,放马去吃草,自己就在不远处的斜坡上挑选了一块干地方,躺了下来。
在这谷地的向阳坡上,嫩草长得又高又稠密。晒热的黑土那种淡淡的气息,压不倒快要凋谢的野紫罗兰那种幽雅的香气。紫罗兰生长在荒废的耕地上,从干木樨草丛中钻出来,或者像花边一样生长在早已无人走的田埂的两边,甚至在硬得像石头一样的荒地上,枯草丛中也露出一朵朵的紫罗兰花儿,就像一只只蓝蓝的、明净的小孩子眼睛。紫罗兰在这僻静而辽阔的草原上逞艳的时候快要过去了,不过在谷地斜坡上、在碱地上,鲜艳夺目的郁金香已经对着太阳伸展开自己的红的、黄的和白的花瓣,起来接替紫罗兰了,而微风就把各种花香掺和到一起,把香味在草原上散得远远的。
在向北的陡坡上,因为悬崖遮住了太阳,还有一片片湿漉漉的积雪。积雪散发着一阵阵的冷气,不过经冷气一吹,快要凋谢的紫罗兰的香气更醉人了,那香气隐隐约约,令人留恋难舍,就好像珍贵的、早已过去的往事……
格里高力把两腿叉得宽宽的,用胳膊肘支着上身,趴在地上,用迷恋的眼睛望着笼罩在一片阳光中的草原,望着远方天边一座座蓝幽幽的古守望台,望着斜坡边上那腾腾的蜃气。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听见远处和近处百灵鸟的歌唱声,听见正在吃草的马轻微的走动声和打响鼻的声音、马嚼子的哗啦声、微风拂动嫩草的沙沙声……他全身贴在硬邦邦的土地上,就感到有一种奇怪的脱离尘世和高枕无忧的心情。这是他早已熟悉的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往往是在经过一度惊恐以后出现,这时候格里高力好像是重新看到了周围的一切。他的视觉和听觉好像格外敏锐了,原来引不起注意的东西,在一度激动之后,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现在看着一只老鹰呼的一声斜斜地飞过,在追赶一只小鸟,看着一只黑黑的甲虫慢慢地、很吃力地在他格里高力撑开的两肘之间爬着,看着那像少女一样艳丽的紫红色的郁金香被风吹得轻轻摇晃着,都觉得很有意思。郁金香离得很近,就在一个塌陷了的田鼠洞的边上。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摘到,可是格里高力一动不动地趴着,如醉如痴地默默欣赏着小小的花儿和茎上那肥茁茁的、还在皱褶里仔细保留着闪闪有光的清晨的露水珠儿的叶子。后来他掉转目光,无思无虑地对着在天空、在一大片荒废的田鼠洞上方盘旋的老鹰看了半天……
过了两个钟头,他们又上了马,打算在天黑以前赶到叶兰乡的几个熟识的村庄。
大概红军的侦察兵已经把他们的行踪用电话通知了各地。他们一来到卡敏村的村口,一阵步枪子弹就从小河那边朝他们迎面打来。佛明一听到子弹那像唱歌一样的啸声,急忙转头就跑。他们冒着步枪火力顺着村边跑去,很快就来到维奥申乡的牧马地带。在烂泥沟村外,有一小队民警想拦截他们。
“咱们从左面绕过去。”佛明提议说。
“咱们往前冲,”格里高力果断地说,“他们九个人,咱们五个人。可以冲过去!”
丘玛柯夫和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都赞成他的意见。他们都抽出马刀,放开疲倦的马,快跑起来。民警们没有下马,不住地打着枪,后来跑到了一边,没有迎战。
“这是一支不经打的队伍。他们抄抄册子很在行,可是认真打起仗来就不行了!”柯舍辽夫用嘲笑的口气高声说。
等到紧跟不放的民警开始逼上来,佛明和其余的人就一面还枪,一面向东跑去,就像被猎狗追着的狼那样:只是偶尔龇一龇牙,几乎连头也不回。在一次对射当中,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受了伤。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腿肚子,打伤了骨头。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脸色煞白,腿上疼得他直哼哼,说:
“打在腿上啦……偏偏就打在这条瘸腿上……这不是故意捣蛋吗?”
丘玛柯夫身子往后一仰,可着嗓门儿哈哈大笑起来。他都笑出了眼泪。他一面扶着靠在他的胳膊上的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在马上坐稳,一面笑得打着哆嗦,说:
“嘿,他们这是怎么挑的呀?这是他们故意往这儿打的……他们看见:一个瘸子在跑呢,所以就想,把瘸腿干脆给他打断吧……唉,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呀!唉,我的好乖乖呀!……你的腿又要短一截了……这一下子你可怎么跳舞呀?现在我非得给你那条好腿挖一尺深的坑不可了……”
“住嘴吧,废话大王!我没心思听你的废话了!行行好,住嘴吧!”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疼得皱着眉头,央告说。
过了半个钟头,等他们从无数山沟中的一条山沟里钻出来,上了一道长长的山坡,他央求说:
“咱们停一停,休息一会儿吧……我要把伤口扎一扎,不然的话,血要流满靴筒子了……”
大家停了下来。格里高力牵着几匹马,佛明和柯舍辽夫时不时地对远处的民警开上两枪。丘玛柯夫帮着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脱下靴子。
“血真的流得太多了……”丘玛柯夫皱着眉头说着,把靴子里的红红的鲜血倒到地上。
他想用马刀把被血浸得湿漉漉并且冒着热气的裤腿截掉,但是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不同意。
“我的裤子是条好裤子,不能弄坏了。”他说着,两手撑在地上,抬起受伤的腿来。“把这条裤腿扯下来,不过要轻点儿。”
“你有绷带吗?”丘玛柯夫摸索着口袋,问道。
“要他妈的绷带干什么?不要绷带也行。”
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仔细看了看伤口,然后用牙齿把一颗子弹的头拔下来,把火药倒在手掌上,先用唾沫和了一点儿泥,把火药和泥掺在一起,拌和了半天。他用这种泥巴把打通的枪伤的两个伤口糊得严严的,很满意地说:
“这法子很管用!等伤口一干,过两天就长好了。”
他们一直不停地跑到旗尔河边。民警们一直在后面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只是偶尔对他们打上几枪。佛明不住地回头看着,说:
“他们是钉咱们的梢……是不是等待援军?他们远远地跟着咱们不是没有用意的……”
他们在维斯罗古佐夫村蹚水过了旗尔河,一步一步地上了一面平缓的山坡。马已经十分疲倦了。他们下坡的时候还能勉勉强强骑着马小跑,可是再上坡的时候就牵着马走了,而且还一面用手擦着汗漉漉的马的两肋和屁股上那一团团哆哆嗦嗦的汗沫子。
佛明果然猜中了:在离维斯罗古佐夫村五俄里的地方,有七个人骑着新换的、跑得飞快的马朝他们追来。
“他们要是这样换着班追咱们,咱们可就糟了!”柯舍辽夫愁眉苦脸地说。
他们不走正路,在草原上跑着,轮流开枪抵抗:两个人卧倒在草丛里打枪,其余的人就跑出二百丈远,下马来,向敌人开枪,好让先前的两个人向前跑出四百丈远,再卧倒下来,准备开火。他们把一个民警打死了,也许是打成了重伤,把另外一个民警的马打死了。不久,丘玛柯夫的马也被打死了。他抓住柯舍辽夫的马镫,跟着马跑起来。
影子渐渐长了。太阳快要落山了。格里高力建议大家不要分散,所以他们都在一块儿一步一步地走着。丘玛柯夫跟着他们在步行。后来他们看见冈头上有一辆双马拉的大车,他们就上了大道。赶车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大胡子哥萨克,赶着车飞跑起来,但是他们开了两枪,大车就停了下来。
“砍死这个下流货!叫他尝尝逃跑的滋味……”柯舍辽夫咬牙切齿地说着,就使劲抽了马一鞭子,朝前冲去。
“别动他,萨什卡 ,不许动他!”佛明制止他说,并且老远就喊道:“老大爷,把马卸下来,听见吗?要想活命,就快卸下来!”
他们也不听老头子那眼泪汪汪的央告,亲自动手卸下皮套,解下颈套和肚带,很快地把鞍上好了。
“把你们的马换一匹给我也好啊!”老头子哭着央求说。
“你是不是想挨耳刮子了,老家伙?”柯舍辽夫问道。“我们的马还有用处呢!留你一条活命,就该谢天谢地了……”
佛明和丘玛柯夫上了新换的马。不久又有三个人加入了跟踪他们的那六个人当中。
“要跑快点儿!快点儿吧,伙计们!”佛明说。“天黑前咱们要是能赶到柯里夫草甸子上,那就有活路了……”
他把自己的马抽了几鞭,跑到前头。他把第二匹马的缰绳挽得短短的,让它在左边跑着。被马蹄踩断的红红的郁金香,像一大滴一大滴鲜血似的,往四面乱飞。格里高力在佛明后面跑着,看到这种红花飞溅的情景,不禁闭上了眼睛。不知为什么他头晕起来,一阵熟悉的刺疼钻进心里……
马使出最后的力气跑着,由于不停的奔跑和饥饿,人也疲乏了。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已经在马上摇晃起来,脸色像纸一样白了。他流血流得太多了。他又干渴,又恶心,吃了一点儿干硬的面包,但是马上就吐出来了。
黄昏时候,在离柯里夫村不远处,他们跑进了从草原上回来的一大群马当中,又最后一次朝着追赶的人开了几枪,他们很高兴地看到,追赶的人不赶了。那九个骑马的人在远处凑到一块儿,看样子是商量了一下,后来就拨转马头回去了。
他们来到柯里夫村,在佛明熟识的一个哥萨克家里住了两天。主人日子过得很富裕,对他们招待得很好。安置在黑暗的棚子里的马匹,吃足了燕麦,过了两天,因为疯跑累坏了的马匹就完全休息过来了。大家轮流着看守马匹,挤在一座到处是蜘蛛网的、很凉爽的糠棚子里睡觉,放开肚子大吃大喝,为在岛上过的那些半饥饿的日子好好地捞捞本儿。
本来第二天就可以离开这个村子的,但是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使他们耽搁下来:他的伤口发炎了,早晨,伤口四周红肿起来,傍晚时候,一条腿都肿了,他并且昏迷过去。他觉得非常干渴。整个夜里,只要一清醒过来,就要喝水,他拼命地喝,每次都喝很多。一夜的工夫喝了差不多有一桶水,但是即使别人搀扶着,他也站不起来,动一动就觉得疼得不得了。他就躺在地上撒尿,不住声地直哼哼。为了让他的哼哼声不那么吵人,把他抬到棚子里远些的角落里,但还是没有用。有时候他哼哼的声音非常大,在他昏迷过去的时候,就大声说胡话和乱叫。
只好轮流守着他。给他端水,用水浸他那发烫的额头,在他呻吟或说胡话声音太高的时候,还要用手或帽子捂他的嘴。
第二天傍晚,他苏醒过来,说他觉得好些了。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呀?”他招了招手,把丘玛柯夫叫到跟前,问道。
“今天夜里。”
“我也走。行行好,你们别把我扔在这儿呀!”
“你怎么行呀?”佛明小声说。“你连动都不能动了。”
“我怎么不行?你瞧瞧看!”他使足劲儿欠了欠身子,可是马上又躺了下去。
他的脸通红通红的,额头上冒出一颗颗小小的汗珠儿。
“我们带你走,”丘玛柯夫果断地说,“我们带你走,请你别害怕!把眼泪擦擦吧,你又不是老娘们儿。”
“这是汗。”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小声说,并且把帽子往眼睛上拉了拉……
“我们倒很想把你留在这儿,可是掌柜的不同意。你别害怕,瓦西里!你的腿会好起来的,咱们还要在一块儿打仗和跳哥萨克舞呢。你泄什么气呀,嗯?伤虽然很重,可是不要紧,没事儿!”
一向对人很冷漠很蛮横的丘玛柯夫,这番话却说得十分亲热,口气中带着异常温柔体贴的意味,格里高力不禁十分惊讶地看了看他。
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离天亮不久了。好不容易把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扶上了马,可是他已经不能独自骑马了,一会儿倒到这边,一会儿又倒到那边。丘玛柯夫用右胳膊搂着他,和他并马走着。
“真是个累赘……应该把他扔掉。”佛明走到格里高力身旁,伤心地摇着头,小声说。
“把他打死吗?”
“嗯,有什么办法,守着他受罪吗?咱们带着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他们一步一步地走了很久,都不说话。格里高力换了丘玛柯夫的班,后来又换上柯舍辽夫。
太阳出来了。下面的顿河上,还有一团一团的雾气,可是在高地上,草原的远方已经很清澈,很明净了,而且天空也越来越蓝,天空中那蓬松的白云一动也不动。草地上落了厚厚一层露水,就像用银线绣的,马走过的地方,留下一条黑黑的、像水流过似的印子。草原上肃穆而宁静,只能听到百灵鸟的叫声。
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随着马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晃悠着脑袋,小声说:
“哎呀,好难受呀!”
“别说了!”佛明很粗暴地打断他的话。“我们服侍你也不舒服呀!”
在离将军大道不远的地方,有一只小鸨从马蹄边飞了起来。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一听到小鸨翅膀那细细的、颤抖的啸声,从昏沉状态中清醒过来。
“弟兄们,请你们扶我下马……”他央求说。
柯舍辽夫和丘玛柯夫小心翼翼地架着他下了马,让他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
“让我们来看看你的腿怎样了。来,把裤子解开!”丘玛柯夫蹲下来,说。
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的腿肿得非常厉害,把一只肥大的裤腿撑得紧绷绷的,一点皱褶都没有了。皮肤一直到大腿都泛着深紫色,油亮油亮的,而且有许多摸起来很柔滑的黑点子。在黑黑的、瘪下去的肚皮上也出现了这样的黑点子,只不过颜色淡一些。伤口和干在裤子上的褐色的血已经发出恶臭的腐烂气味,丘玛柯夫用手指头捏住鼻子,皱着眉头,好不容易压住涌上来的一股恶心感,仔细把伙伴的腿看了看。然后他又仔细看了看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那垂下的、发了青的眼皮,和佛明交换了一下眼色,说:
“好像成了坏疽了……嗯,嗯……瓦西里·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你的情况很糟啊……简直是要命的事儿呀!……唉,瓦夏呀,瓦夏,你怎么这样倒霉呀……”
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急促地、频频地喘着气,一句话也没有说。佛明和格里高力就像听到口令似的,一齐下了马,从上风头走到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跟前。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躺了一会儿,便用手撑着坐了起来,用模糊的、决意离开人世的眼神打量了大家一遍。
“弟兄们,把我打死吧……我已经不能活了……浑身都难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他又仰面躺下去,闭上了眼睛。佛明和其余的人都知道,他会有这种要求的,而且都在等着他这种要求。佛明迅速地向柯舍辽夫挤了一下眼睛,便转过身去,柯舍辽夫二话不说,就从肩上摘下步枪来。他看了看走到一旁去的丘玛柯夫的嘴唇,与其说是听到,不如说是猜到丘玛柯夫在说:“开枪吧!”但是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又睁开眼睛,很刚强地说:
“请朝这儿打,”他抬起手来,指了指自己的鼻梁。“这样一下子就能死了……你们要是上我们的村子里去,就把我的事告诉我老婆……叫她别再盼我了。”
柯舍辽夫令人不解地摆弄了半天枪栓,迟迟不开枪,于是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垂下眼皮,又说了最后几句话:
“我只有老婆……没有孩子……她生过一个孩子,可是孩子死了……以后再没有生过……”
柯舍辽夫两次举起枪来,又两次放下去,脸色越来越灰白……丘玛柯夫气呼呼地用肩膀把他往旁边一抗,把他手里的步枪夺了过来。
“你不行,就别干,狗崽子……”他沙哑地叫了两句,就摘下帽子,拢了拢头发。
“快点儿!”佛明一只脚踏上马镫,吩咐说。
丘玛柯夫一面考虑着要说的话,一面慢慢地、轻轻地说:
“瓦西里,永别了,为了基督,请你宽恕我和我们大家吧!咱们到了阴间里还会见面的,我们也要到阴间里受审判……我们一定会把你的话告诉你老婆。”他等候回答,但是司捷尔里亚德尼柯夫却等着死,一句话也不说,脸色越来越白。只有晒成焦黄色的睫毛哆嗦着,好像是被风吹的,再就是左手的指头轻轻动着,不知为什么还想扣上胸前军便服上的一个破扣子。
格里高力这一生中见过很多人死,可是这一次他不能看了。他使劲拉着缰绳,牵着自己的马,走到前面去。他等待枪声的那种心情,就好像有人要朝他的肩胛骨当中开枪……他等着开枪,他的心紧张地跳动着,但是等到后面的枪声猛烈而急促地一响,他的两腿都软了,好不容易才勒住直立起来的马……
他们走了有两个钟头,一声不响。到休息的时候,丘玛柯夫才第一个开口说话。他用手捂住眼睛,低沉地说:
“我他妈的干吗要朝他开枪呀?要是把他扔在草原上,心里也许不会这样难受。就好像他还站在我眼前……”
“你一直就没有干惯吗?”佛明问道。“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是不能习惯吗?你根本没有心了,你的心成了一块锈铁啦……”
丘玛柯夫的脸刷地白了,他怒冲冲地盯住佛明。
“现在你别惹我,亚可夫·叶菲莫维奇!”他小声说。“你别刺我的心,要不然我也可以把你敲了……这很简单!”
“我惹你干啥呀?没有你,我的操心事儿就够多了。”佛明用和解的口气说过这话,就在阳光下眯起眼睛,舒舒服服地伸着懒腰,仰面躺下去了。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