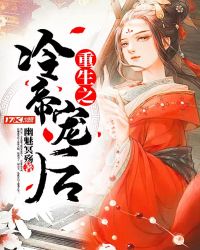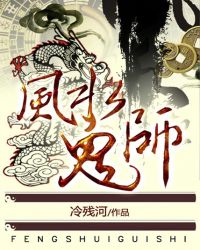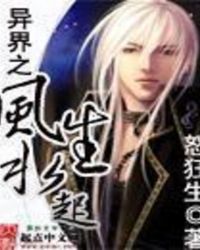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套装共6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老调子已经唱完
公元前2070年,大禹不幸逝世。 注释标题 禹是传说中的人物,原本不应该有准确的生卒时间。这样写是基于两个前提:一,承认启是禹的儿子,而且是他在禹去世后废除禅让制,确立世袭制;二,承认“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公元前2070年为夏始年的结论。但此说仅供参考,不能作为定论。
当然,是因公殉职。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我们民族这位远古英雄是死在南巡途中的,地点在今天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于是,一个难题就摆在了众人面前:他留下的权力真空由谁填补? 注释标题 见《史记·夏本纪》。以下无另注者皆同。
兹事体大,不可等闲视之。
说来这原本不是问题,因为有制度也有先例。制度就是所谓禅让,先例则是传贤不传子。比如接替尧的是舜,而不是尧之子丹朱;接替舜的是禹,也不是舜之子商均。这就是之前三位老大尧舜禹的权力交接方式。由于这种方式是五帝时代的,所以在儒家那里被看作是“帝道”。
但,这里面有前提条件和时代背景。
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祖先》一卷中所说,部落联盟晚期实行的是双执政或双首长制。尧当一把手的时候,舜是二把手;舜当一把手的时候,禹是二把手。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平稳过渡。因此,如果禅让和传贤当真存在,那么第一道程序就该是选贤,而且这道程序据说禹也走了。他起先选了皋陶,皋陶去世后又选择了治水时的得力助手益。
因此禹死之后,接班的就该是益,有问题吗?
有。
问题出在第二道程序,这道程序叫避让。
避让是必须的,否则显得有野心,不谦和。所以,尧死之后,舜就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要把原本属于他的职位让给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注释标题 见《史记·五帝本纪》。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让对象是舜的儿子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请问,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多半还是后来那些篡改历史的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
我们要问,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多事之秋。那么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究竟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也只能说,这是一种恶俗。
不过剧本既然已经写好,便只能硬着头皮上舞台。因此禹去世后,益也照葫芦画瓢,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禹的儿子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夏商周三代政权的合法性岂不统统都成了问题?事实上至少在战国,人们便开始对历史真相产生怀疑。孟子的学生万章就问:大家都说大禹的时代道德滑坡,天下不传给贤人而传给儿子,有这事吗?
孟子倒不怕这一问,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天下可以让来让去。在此之前,万章也曾问他:尧把天下让给舜,是不是事实?孟子的回答斩钉截铁:没有的事!他还说:天下本来就不是天子的,怎么可以拿去给人!
万章问:那么舜有天下,谁给他的?
孟子说:天给他的。
所以,万章又来问禹的事,孟子就不难回答。他的说法是:传子还是传贤,全看天意。天要给贤人,就传贤;天要给儿子,就传子。何况启原本就能继承禹的遗志,益则资历尚浅威望不够。言外之意很清楚:此时传子就是传贤。 注释标题 以上均见《孟子·万章上》。
这个说法后来被司马迁全盘接受,从此成为正统史学界的主流意见。然而不同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战国时期就有人说,禹传给益的职位是启依靠武力抢去的,甚至还有人说这其实是禹的安排:他表面上传天下于益,实际上却暗示启自己夺权。这就已经是在怀疑禹的人品了,却也被司马迁录入《史记》,还使用了“天下谓”三个字。可见这种传言在当时已是沸沸扬扬,治学严谨的司马迁也不能充耳不闻。 注释标题 这些说法见《竹书纪年》《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战国策·燕策一》《史记·燕召公世家》。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启废禅让
不妨先看孟子的说法。
孟子说,禹在生前确实向上天举荐了益,益也确实按照规矩避让于启。但是遗憾得很,朝觐、诉讼和唱赞歌的人都不去见益,而是去见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儿子,领袖的儿子呀(吾君之子也)!
司马迁说得更具体:吾君帝禹之子也。
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没错,启可能是优秀的,但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实力大大超过了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早就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咸与维新。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禹的儿子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众所周知,益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奶酪,启成功地得到了他的蛋糕。至于手段是和平演变,还是武装夺权,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启的新称谓:夏后帝启。 注释标题 见《史记·夏本纪》。
这很有意思。
先说后。后,可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写成“后”,意思是诞育者,引申为领导者,相当于王。不过王的甲骨文字形是大写的人站在土地上,后的意义却很可能是临盆生孩子。所以到后来,女性称后,男性称王。 注释标题 王字“象王者肃容而立之形”,见孙海波《甲骨金文研究》;后字有“产子之义”,见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上篇》。两字的解释分别请参看《古文字诂林》1-206、8-87。
皇天后土,也是这个来历。
帝的本义则是缔造者,也引申为领导者。问题是,启既然已经是后,为什么还要称帝?因为这时的“帝”是部落联盟大酋长的称号,比如帝尧、帝舜和帝禹。因此,帝启二字便标明了权力的来源以及政权的合法性。
但,帝禹和帝启,却有本质区别。
禹是不能叫夏禹的,只能叫大禹或帝禹。启却可以也必须叫夏启,或夏后启。因为原本是族名的夏,现在已经变成了国号。准确地说,闯红灯的启在废除禅让制,开创世袭制的同时,也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 注释标题 战国之前的典籍从不称禹为夏禹,只称禹、大禹、帝禹,启则称夏启、夏后启。此说见范文澜《中国通史》。但,夏作为国号,却未必是启的自称。启应该是没有国号意识的,夏为国号多半是后世的认定。这说明司马迁他们也已经意识到启废禅让的历史意义。所以《史记》写《夏本纪》时有“国号曰夏后”一句,写《殷本纪》却没有汤定国号为商,或者盘庚定国号为殷。
国家诞生了,我们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那时毕竟还是过渡时期,因此“后”也多。于是夏启便叫“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Rajan),城邦君主也叫罗惹。只不过此罗惹非彼罗惹,此刻的群后也非当年的群后。 注释标题 元后和群后的称谓,《尚书》中仍在使用。如《尧典》称“群后四朝”,《泰誓》称“元后作民父母”。又《梵语杂名》称“王梵名罗惹”,《守护国界经》称“言王者即罗惹义”。
后,是国家诞生时的脐带。
元首叫“后”的,是“部落国家”。
想当年这样的政治实体一定数量可观,它们被称为“诸夏”。诸的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都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对夏文明的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看来,夏人早就有了祖宗崇拜。
早到什么时候?
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
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
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夏启,不过顺势而为。
然而从史前史到文明史的轨迹,却十分清楚:
女娲登坛,生殖崇拜,创立氏族社会;
伏羲设局,生殖崇拜,变母系为父系;
炎帝东征,图腾崇拜,变氏族为部落;
黄帝出场,图腾崇拜,变部落为部落联盟;
启废禅让,祖宗崇拜,变部落联盟为部落国家。
尧舜禹,则都是在为夏启做准备。
难怪启废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问题是,历史上当真有夏吗?
这可是有争议的。
谁代表中国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 注释标题 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认为,由于没有确定的夏遗址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因此不能确定商以前是否有一个发育成熟的夏朝。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历史上在这个时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个说法是科学的。
当然讲不通。事实上,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恐怕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时代”,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主权国家联盟”。它们可以叫“三代”,不能叫“三朝”。
真正的王朝,开始于秦。
之前,则是漫长的成长期: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以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为中华文明奠定基础和初步定型是西周,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西周初年,也基本上只有城市国家。领土国家大量形成要到春秋,独立国家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夏商周,岂能是王朝?
不是王朝,又是什么?
三个民族,三个阶段,三种文明,三个代表。
代表谁?
中国。
说起来这也是一件奇特的事情。比如夏商周,明明是三个不同部族主导的时代,却居然都是中国;元明清,更清清楚楚是三个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居然都是中国。谁都是中国,谁都不能说唯独自己是中国,更非谁想说自己是中国就可以是。然而只要是,便成为中华文明和历史不可分割之整体的一部分。所以,诸夏固然是,入华的五胡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屡经混血而文明如一,就因为全都有此认同。
中国的概念,是超越种族更超越政治的。
那么,这样一种“中国”又该是什么呢?
最原始的意义当然是城市,或中心城市,而且是天下或世界的中心。它在西周,甚至具体地就是洛阳,因为周公营建成周洛阳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此天下之中。 注释标题 见《史记·周本纪》。
于是,他们“宅兹中国”。
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铸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内底,铭文全篇记录了成王时修建洛阳的史实。显然,他们是把洛阳作为“世界中心城市”来建设的,因此建成以后便举行隆重的仪式,在那里安放了九鼎。
九鼎也是“中国”的象征,据说是大禹治水成功后用九州之铜铸造的。启废禅让,九鼎归了夏;商汤灭夏,九鼎归了商;武王伐纣,九鼎又归了周;秦并天下之后,这宝贝却下落不明,害得后来武则天只好山寨了一套。 注释标题 九鼎故事见《左传》之桓公二年、宣公三年及杨伯峻注,《史记·封禅书》。武则天的九鼎在万岁通天二年(697)四月铸成。
这很奇怪。
似乎不能说九鼎并不存在,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便曾在洛阳城外,向周定王派来的使节表示了对九鼎的浓厚兴趣,由此留下了“问鼎中原”的成语。可惜他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不但没能一睹真容,就连九鼎是一只还是九只都没弄清楚。那使节说:关键在德而不在鼎。无德,有了鼎也没用。我们周虽然衰落,却还没到亡国亡天下的地步。九鼎的大小轻重,恐怕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问的。 注释标题 见《左传·宣公三年》。
如此重要的东西,怎么会不见了呢?
然而直到春秋战国,人们都相信有九鼎,也相信九鼎是从夏传到商,再从商传到周的。这就等于用它为线索把夏商周串联起来了,他们也当然都是中国,是同一文明的创造和传承者。只不过那时的天下还不是统一国家,因此他们不是中国的三个王朝,只能说是“中国”的三个代表。
夏商周成为三个代表,是因为他们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文明程度都是最高的。诸夏高于诸狄和诸羌,也高于当时还很弱小甚至处于初级阶段的商族和周族。等到商的文明程度超过了夏,代表权便理所当然也归了商。
周的后发制人,也一样。
何况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而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他们对周边民族,也会既武力征服,又和平演变。但,只征服,不消灭。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总之,所谓“中国”其实就是T型台,先后取得了文化主导权的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甲骨文与青铜器
无论如何,夏文明都是质朴的。
质朴不难理解。那时生产水平毕竟低下,夏人根本就不知奢华为何物,也没有摆谱的理由。孔子说禹的饮食起居艰苦朴素,唯独祭祀不敢马虎,应该属实,但与道德无关。 注释标题 见《论语·泰伯》。
其实,传说中的夏即便真实地存在,也不是秦汉那样的王朝。当他们出现在文明的第一级台阶上时,不过是率先实现了从部落到国家转变的带头大哥。初期,恐怕就连部落国家的联盟都没有,只有一个最大的部落国家叫夏,若干中小部落国家叫诸夏,此外就是尚待转变的诸狄和诸羌。
所以,他们有没有文字,也很难说。
萌芽或许有了。考古学家在夏代的陶器陶片上发现了刻画的符号,其中很有一些与后来甲骨文不乏相似之处,因此有可能已经具备文字功能。不过就算是吧,那也是刻在陶器上的,与后来铸在青铜器上的不可同日而语。
夏,朴实无华。
殷商文明却诡异而绚烂。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从形状到精神都一脉相承。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的确,人类是“创造符号的动物”。符号,区别了自然与文化;文字,则区别了史前和文明。这也正是夏文明遭到质疑的重要原因。以甲骨文为母体的汉字,却是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以及种族界限远距离传播的符号。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因此,即便不知道它们的准确读音,也不妨碍明白它表达的意思。唯其如此,说着不同方言和语言的族群才有可能接受汉字传达的信息,认同以汉字为载体的文明。当年的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现代的中国人,都如此。
没错,如果不是用汉字书写,以古今语音之差异,我们将读不懂先秦诸子,也无法欣赏唐诗宋词。中华文明能够具有世界性,能够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汉字功不可没。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文明圈也可以说就是汉字文化圈。日本学者甚至发现,在周代,较早较多地接触到铸有铭文之青铜器的邦国,都比较认同周天子的权威,情况相反的则态度冷淡。由此有了一种说法:汉字的魔力。 注释标题 见(日本)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
确实有魔力。难怪古人说,汉字发明出来时,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个没完。 注释标题 见《淮南子·本经训》。
对不起了,鬼们!
商人却完全不顾牛鬼蛇神的感受,自说自话地利用文字与神祇和祖宗沟通。沟通的方式有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和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
然而无论哪种文字,都天然地具有卓异的风格、艺术的品位和审美的意味。甲骨文朴拙劲挺,钟鼎文雄健诡谲,石鼓文厚重恣肆,尽显筚路蓝缕的草莽之气,开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犊的没心没肺。从商到周,都如此。
这是一种“童年气质”。
同样的气质也体现于青铜器,这是商人的拿手好戏。夏代虽然有黄铜也有青铜,但商人掌握的冶炼技术显然水平更高,这才把夏人请下了T型台。因此他们的猫步,肯定走得铜光闪闪,铿锵有力,极尽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么?
英武、富有、权威。
承担了这个任务的是兵器和礼器。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 注释标题 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但是这没有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我们的殷商文明也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 注释标题 这个观点见李泽厚《美的历程》,诗见《诗经·商颂·长发》。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也不奇怪。
天命玄鸟
开创了商时代的是汤。
这个说法没有错。前面说过,夏商周都不是王朝,而是时代,也是进程。夏代文明草创,只有部落国家;周代日臻成熟,已有国家联盟,还有天下共主。因此,前者恐怕只能叫“夏阶段”,后者则无妨称为“周天下”。二者之间的商应该建立了部落国家的联盟,可以叫作“商时代”。这个称谓也意味着一个事实:此时此刻,由商人代表中国。
商汤,是“划时代的人”。
划时代的商汤据说大名叫履,又叫天乙,汤则是他的荣誉称号,意思是“除虐去残”。由于有此功绩,他被列为小康社会的三个代表(三王)之一,在历史上备受推崇。
这就照例要有励志的故事。
故事很现成。有一天,商汤用网捕猎。他祷告说:天下四方的都进来吧!结果飞禽走兽尽入其网。商汤又打开网的三面,然后对鸟兽们说:想从左边出去的往左,想从右边出去的往右,不听命令的就留下来!
结果众人都说:仁德之至啊,泽被禽兽! 注释标题 以上见《史记·殷本纪》及(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
可惜,跟不少对道德楷模的刻意打造一样,这件事也露了马脚。请问,当商汤说“不用命,乃入吾网”时,他究竟是要表现不忍一网打尽的恻隐之心,还是要显示自己权威的不容置疑呢?恐怕是后者吧!要知道,禽兽们原本就是因为服从命令才进来的,哪有不听命令的?恩威并施罢了。
再说我们也不知道,落入网中的有没有玄鸟。
玄鸟就是燕子,也是商族的图腾和保护神。根据一个古老的神话,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读如谢)就是由于母亲简狄在河边洗澡时吃了玄鸟蛋,才怀孕生下的。因此商族的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注释标题 故事见《史记·殷本纪》,诗见《诗经·商颂·玄鸟》。
于是,对玄鸟的祭祀便成为盛大的节日。每年,当黑色的燕子归来时,他们都要举行性爱的狂欢。这时除男性奴隶外,贵族、平民和女奴,都可以自由地来到玄鸟神庙,在神的面前尽情享受一夜情。当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注释标题 见翦伯赞《先秦史》及其考证。
如此习俗,中外皆同,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则是弥补婚姻对人性的压抑,重温远古的性爱自由。它甚至是古罗马一个固定节日,叫沙特恩节(Shateen Festival),只不过时间是在冬至那几天,也没有燕子或玄鸟。 注释标题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注43。
这是性爱的复活节,与儒家主张的道德风马牛不相及。
事实上,商人建立政权并非靠道德,维持统治当然也不靠玄鸟。前者靠的是对青铜冶炼技术的垄断、商业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以及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后者则还要加上神权的力量。所以商代祭祀活动和神职人员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许只有古埃及可以相提并论。
不同的是,商王并不在王宫之外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没错,王宫里会有大量的巫师。他们的任务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但如果商王愿意,他也会自己来解释。更重要的是,祭祀用的青铜礼器只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而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他自己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注释标题 请参看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
但,这与性爱的狂欢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商的“沙特恩节”不但复活了性的自由,而且揭示了文化的密码。这个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节日告诉我们,商族最早是以燕子为生殖崇拜象征的,只不过后来它变成了图腾。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又像在埃及一样变成了神。
变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鲁斯那样继续保持鸟的形象,因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只太阳神鸟。可惜太阳崇拜是属于夏的,商文化必须更高级。高级就不能再是鸟或兽,玄鸟也就变成了更具神格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为人间有“下帝”。下帝商王,是天命玄鸟的后代,皇天上帝的宠儿,青铜礼器的主人。难怪饕餮、肥遗、夔龙和虬龙,都为他保驾护航。 注释标题 有下帝故有上帝,见翦伯赞《先秦史》。
如此江山虽非铁打也是铜铸,怎么也说亡就亡了呢?
或许还得走进商都去看一看。
不能再胡闹了
迁徙到殷的商都,就像有城墙的上海。
殷就是现在的安阳,商则是现在的商丘,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在商丘建立根据地的是商汤,以安阳(殷)为大本营的是盘庚。盘庚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不再移动,所以后人便把这个族群和国家称为殷,或商,或殷商。 注释标题 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尚书》《史记》等称殷,《古本竹书纪年》等称商,《今本竹书纪年》等称殷商。
他们如何自称,却不清楚。
不清楚是肯定的。那时还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国号。称帝之后定国号是王朝时代的事,把殷或商称为首都也同样欠妥。殷商只是部落国家,并非后来的领土国家,怎么会有首都?也只能叫根据地或大本营,却肯定是城市,因为他们自称“大邑商”或“天邑商”。 注释标题 商在汤的时代,应该只是规模比夏更大的部落国家。到殷纣王时期已有多个城市,则可能已是领土国家。樊树志《国史概要》将其势力范围分为直接管辖区和间接管辖区,后者称为四方或四土,前者谓之大邑、大邑商、天邑商,如《殷契佚存》987曰“王其入大邑商”,《殷虚书契续编》3-24-1曰“王今入大邑商”,《殷虚书契后编》上18-2曰“王才在大邑商”,《小屯殷虚文字甲编》2416曰“告于兹大邑商”,《甲骨缀合编》182曰“天邑商公宫衣”。
将商都或殷都理解为都市,可以成立。
但,那是怎样的都市啊!
城墙是高大的,宫殿是威严的,街道纵横交错,房屋鳞次栉比,作坊星罗棋布,饭店灯红酒绿。乘坐豪车的贵族招摇过市,无所事事的平民徘徊街头,额上打了火印的奴隶被驱赶着去服劳役,不同种族的巨商小贩穿梭往来。就连后来成为周武王得力助手的羌人姜太公吕望,据说也曾在殷的城市朝歌(朝读如召,今河南省淇县)卖过牛肉。
这是商业的城市。
商品来自四面八方。渤海沿岸的海产品和绿松石,西北草原的畜群和皮毛,长江上游的铜和锡、下游的稻米,以及商人自己生产的农作物和工艺品,都在殷都进行买卖,使用的货币则曾经一度是来自斯里兰卡的海贝。如此之高的商业化和繁华开放程度,堪比后来的唐代长安和宋代开封。
殷都,俨然古代东方世界的国际贸易中心。 注释标题 请参看翦伯赞《先秦史》的描述及其考证。
手工业同样相当发达,工艺水平也极高,连马缨和篱笆的制作都有专门的工匠,完全达到专业化的程度。这些产品除了满足商王和贵族的骄奢淫逸,也拿到市场上买卖。生意最好的时候,甚至庙宇都会变成市场。
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此代,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跑来跑去做生意的称为“商人”。 注释标题 请参看翦伯赞《先秦史》、樊树志《国史概要》。
行商坐贾,即源于此。 注释标题 徐中舒先生即谓: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见《国学丛书》第一卷第一号。
这似乎“不像中国”。
的确,从夏开始,我们民族便基本上以农业立国,重农抑商几乎成为世代共识,工商业和城市经济发达到超过农业的就只有殷商和两宋。有趣的是,宋其实就是殷,是殷这个字的音变,所以殷商残余势力在周代的国号就是宋。这就太有意思了,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什么前缘命定? 注释标题 关于宋与殷的关系,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无疑,南北两宋的宋,不是东西两周的宋,前者与殷商也多有不同。他们虽然都注重城市工商业经济,但两宋气质是文雅甚至淡雅的,殷商却如熊熊烈火,浓郁瑰丽。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宋的情况只能在《大宋革新》一卷交代,殷商的气质则可能源于他们喜欢折腾的民族个性。这个民族大规模集体性的迁徙,从契到汤四五百年中八次,从汤到盘庚三百三十年间五回,正所谓“前八后五”,简直就像游牧民族。 注释标题 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见张衡《西京赋》。
实际上也很可能就是。商人好巫术,重鬼神,酷爱肉食和饮酒,有大量牛的肩胛骨可供占卜并记录卜辞,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多次迁徙,亦非像后来的东晋和南宋那样是为了避难,而是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牧场或商品集散地。也就是说,他们是边游牧边做生意的,就像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Sogdia)、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Bedouins)。
商,恐怕原本就是游牧商贸民族。
因此,他们来到中原,跟当年的炎帝族一样,也经过了万里长征。只不过,炎帝是西戎,他们是东夷;炎帝的图腾是兽(牛),他们的是禽(玄鸟)。但敢想敢干,一样。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几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一遍,结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国,一半像外国:神权政治像埃及,等级观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伦,商品经济像腓尼基,奴隶制度像罗马。据卜辞记载,他们甚至可能有罗马那样的角斗表演,让沦为奴隶的战俘自相残杀,供商王和贵族观赏。 注释标题 殷商卜辞中有“卜贞,臣在斗”(前二·九)的记录,吕振羽、翦伯赞两先生均猜测有用奴隶的角斗表演之事。
殷商六百年,浓缩了世界古代史。
如果不是周人异军突起,殷商会不会发展为罗马帝国?
难讲。
黄河九曲十八弯,中国道路也一样。
商人却处处出格。他们“析财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便分家过日子,包产到户,甚至析财到人,就连妇女也有自己独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他们又“以业为氏”,也就是从事什么行业,就采用什么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绳的是索氏,做旗帜的是施氏,编篱笆的是樊氏。更为严重的是居然还“以国为姓”。诸侯封在某国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家人。谁的实力强,谁就是大爷。 注释标题 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第三章及所引文献。
对不起,这就是“闯红灯”了。
结果却与夏启刚好相反。请大家想想,以国为姓,还有君吗?以业为氏,还有父吗?析财而居,还有家吗?家都没了,还有国吗?家国、君臣、父子都没有,还有天下吗?照他们这样下去,变图腾为祖宗,岂不是白干了?
这就比酗酒、泡妞、开裸体舞会、以渔猎为游戏、迫害忠良不听劝告、让女人干预朝政等等严重多了,甚至比严刑峻法滥杀无辜还要严重,当然不能再让他们胡闹下去!游牧商贸也好,城市工商也罢,这两种文明都不是我们的菜。曾经一度代表中国的殷商,也最终被周人赶下了历史舞台。
后起之秀周,要为中华文明立法、立范、立规矩。
奠基者来了。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奠基者》 易中天中华史·第一部:先秦(套装共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