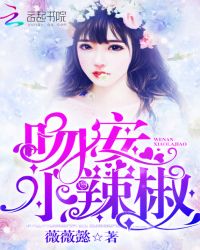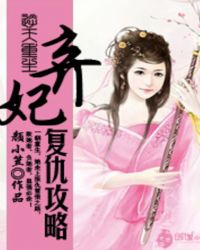母与女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李维榕家庭心理治疗系列·解剖原生家庭真实案例(套装8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母与女
母与女的关系,是十分奇妙的。
很多时候,母亲都会把女儿当作自己的一部分,二为一体。
母亲喜爱的事物,希望女儿也能喜欢;母亲没有完成的梦想,希望女儿会去完成;母亲虽然会崇拜儿子,但女儿,才是亲信。
女儿天生是母亲的忠实观众,留心着母亲的一举一动。小脚板爱穿母亲的高跟鞋,走得一拖一跌,却一心跟随母亲脚步。
女儿也是母亲的守护神,一察觉到母亲处境不利,就会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己;很多女孩子的心理病,都与保护母亲有关。
十五岁的亚敏,就是一个好例子。
亚敏有偷窃习惯,又数次企图自杀。她的家人,以及她就读学校的老师,都十分担心,不明白亚敏为什么会有这样反常的行为。
这是我学生的一宗个案,首先是学校要求我学生见亚敏,但我学生很快就发觉,这十五岁的女孩子,只有母亲一人做伴,事无大小,都以母亲主意为主。
见过母亲后,却发觉母亲比女儿更奇妙。这位快四十岁的母亲,比女儿更像个小女孩,四处找人陪她玩耍。十三岁的儿子放学回家发现母亲静坐一角,问她为什么不去买菜做饭,母亲说:“你先陪我玩一盘波子棋,不然我就不做饭。”
碰上这样的母亲,亚敏当然要负起很多打理家庭的责任。
这样还不止,母亲又会不时想出新花样,她让女儿穿上自己的睡袍,扮作自己走到丈夫床上,说是要测验丈夫的反应。
母亲说,她本来并不打算嫁给现在的丈夫,只是婚前一次约会时,他嫌她不够漂亮,她就立意嫁给他,理由是男朋友变成丈夫后,她才有机会报复。婚姻当作“复仇之旅”,如此古怪的母亲与妻子,当然被我学生服务的精神科诊所当精神病人看待。
我的学生对着一母一女,真搞不清哪一个才是病人。因此她要求我作一次示范诊断,以便决定应该向哪一方面入手。
以家庭治疗的角度而言,“病人”并不一定是症状携带者(Symptom Bearer)。亚敏虽然有偷窃及自杀等行为,但是她的病源,却可能是母亲。而母亲这种怪诞的表现,又该归咎于谁?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要念出难处,最好是全家一起见面。
亚敏一家十分合作,一叫就来。一家五口,父母及三个儿女,以亚敏为长,另外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十三岁、一个九岁。
亚敏静静坐在母亲身旁,虽然有问有答,但是大部分时候都是望着母亲的指示。母亲却分明看重儿子,并坦白地指出:“我是重男轻女的,儿子说什么都可以,女儿却说什么都不成。”
亚敏好像很习惯在人前被母亲奚落,只有一脸无可奈何的笑容。
我问亚敏的父亲:“你对妻子这种重男轻女的看法,是否认同?”
父亲说:“我不认同,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她什么事都是我行我素。她不准许亚敏见我的母亲,谁也左右不了她的决定。”
每一个家庭除了主要成员外,还有很多幕后的重要角色。原来亚敏的祖母与亚敏的母亲冷战多年,亚敏出世时,祖母一定要亚敏归她教养,母亲争持不过,只好让亚敏被祖母抱走。因为憎恨婆婆,慢慢也开始讨厌亚敏。到亚敏六七岁回家与父母同住时,母亲始终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女儿。
被拒绝的女儿却是那样忠心耿耿,任得母亲打骂,却仍然想尽办法讨母亲欢心。也在同时,她开始有偷窃的行为。偷的都是她并不需要的东西,却就是不能罢手。
父亲说:“我们把她打得手掌开花,但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她什么都有,为什么要去偷?”
我说:“有一种偷窃行为,是与内心的不平衡有关,你们有没有留心是否有不快乐的事情发生在亚敏身上?”
父亲倒答得爽快:“当然不快乐啦,天天被母亲当出气袋,不过她也用不着去偷东西呀!”
母亲不大说话,但说起话时有种斩钉截铁的感觉,不像丈夫那副艾艾怨怨的无能。
我想:这个家庭的权力分配,是非常一面倒的,加上母亲这几年来苦心经营,偷偷把丈夫的银行户头都转到她名下,大财在手,她的气焰更盛。
奇怪的是,三个儿女都不同情他们的父亲,却紧随母亲身旁,尤其两个年长的,十分留心母亲的动态,反而对自己的事情毫不关心。
从理论及临床经验,我们知道儿女是很能为父母牺牲自我的,但是,却怎样也想不出,他们的母亲为何对这三个孩子有这样大的影响力?
直到第二次见这家人时,才发现真相:原来要自杀的,并不是亚敏,却是亚敏的母亲。
她说:“我常常觉得做人没有意思,常常想死掉。”
我问:“你试过自杀吗?”
她答:“试过的,几天前我就想死。我问儿子,你陪我去死好吗?儿子说:‘妈,我不想死,你也不要死吧。’我见他不肯陪我,就去问女儿,亚敏说:‘好,你要死,我就陪你。’我们一起走上医院背后的山坡,想跳下去,想想又觉得太矮,怕跳下去死不了,因此就回家了。”
这位母亲陈述找儿女陪她寻死的过程,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毫无怨悔。父亲听着,却一点反应也没有,完全没有要保护儿女的冲动。在这种家庭的气氛下,可以想象儿女会觉得多么不安全。
我问大儿子:“你担心母亲会死掉吗?”
大儿子第一次认真地回答我说:“担心极了。我那天上课,一直担心妈妈是否真的去死,直到她回来才放心。”
我问亚敏:“你真是个孝顺女儿,母亲要死,你也陪伴?”
亚敏微笑点头。
怪不得三个孩子成了母亲的守望人,一个把死当玩耍的母亲,怎令儿女放心得下?
这母亲的行为当然极端,但是把她当作精神病人看待也于事无补,倒不如把她的问题“正常化”,先解除她儿女的忧虑。
因此,我对她说:“你真是个老顽童,玩波子棋不够,连自杀也要玩。你大概是没有玩伴,才会与孩子混在一起,你丈夫不陪你玩吗?”
听了我的话,她十分开心,有点遇到知己的狂喜,说:“他不陪我玩的,他陪我玩就好了。”
怎样替老顽童找伴?我认为是这宗个案的方向。
因为这个家庭不知道:爸爸才是妈妈的伴。父母关系不调和,总是苦了自己的子女。
尤其是苦了那个与母亲二为一体的女儿!
有问题的分明是亚敏,要处理的却是她父母间的婚姻关系。
家庭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 李维榕家庭心理治疗系列·解剖原生家庭真实案例(套装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