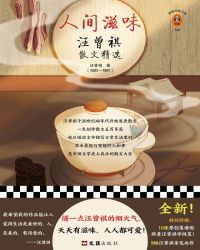背东西的兽物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间滋味:汪曾祺散文精选(读客经典文库)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背东西的兽物
毛姆描写过中国山地背运货物的伏子,从前读过,印象极为深刻,不过他称那种人为“负之兽”,觉得不免夸饰,近于舞文弄墨,而且取义殊为卑浅,令人稍稍有点反感。及至后来到了内地,在云南看到那边的脚夫,虽不能确定毛姆所见即是这一种人,但这种人若加之以毛姆那个称呼是极贴当而直朴的,我那点反感没有了,而且隐然对他有了一种谢意。
人在活动行进之中如果骤然煞住,问一问我在这里到底是在干点儿甚么呢,大概不会有肯定答案的,都如毛姆所引庄子的那一段话中说的那样,疲疲役役,过了一生,但这一种人是问也用不着问,(别人不大会代他们问,他们自己当然不可能发问,)看一看就知道真是甚么“意义”都没有,除了背东西就没有生活了。用得着一个套语:从今天背到明天,从今年背到明年。但毛姆说他们是兽物还不是象征说法,是极其写实的,他们不但没有“人”的意义,而且也没有人形。
在我们学校旁边那条西风古道上时常可以看到他们,大都是一队一队的,少者三个五个,多的十个八个,沉默着,埋着头,一步一步走来。照例凡是使用气力作活的人多半要发出声音,或唱歌,或是“打号子”,用以排遣单调,鼓舞精力,而这种人是一声也不出的,他们的嘴闭得很紧。说是“埋头”,每令人想到“苦干”,他们的埋头可不是表示发愤为雄,是他们的工作教他们不得不埋头。他们背东西都使用一个底锐、口广、深身、略呈斗斛状的竹篮。这东西或称为背篓,但有一种细竹所编,有两耳可跨套于肩臂,而且有个盖子,作得相当精致的竹篮,像昆明收旧货女人所用的那一种,也称为背篓,而他们用的是极其粗率的简厢的。背篓上高高装了货物。货物的范围很窄,虽然有时也背盐巴、松板、石块、米粮等物,大多是两样东西,柴和炭。柴,有的粗块,有的是寸径树条,也有连枝带叶的小棒子;有专背松毛的,马尾松针晒干,用以引火助燃,此地人谓之松毛,但那多是女人,且多不用背篓,捆扎成一大包而背着。炭都是横着一根一根的叠起来。柴炭都叠得很高,防它倒散,多用绳素络住。背篓上有一根棕丝所织扁带子,背即背的这一根带子。严格说不应当说是背,应当说是“顶”,他们用脑门子顶着那一根带子。这样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不得不埋着头了。头稍平置,篓子即会滑脱的。柴炭从山中来,山路不便挑扛,所以才用这种特殊方法负运。他们上山下山,全身都用气力,而颈部用力尤多,所以都有极其粗壮,粗壮到变形的脖子。这样粗壮的脖子前面又多半挂了个瘿袋,累累然有如一个肉桂色的柚子。在颈子上都套着一个木板,形式如半个刑枷,毛姆似乎称之为“轭”的,这也并非故意存有暗示,真的跟耕田引车的牛头上那一个东西全无二致,而且一定是可以通互应用的。在手里,他们都提着一根杖。这根杖不知道叫甚么名堂,齐腰那么高,顶头有个月牙形的板,平着连着那根杖。这根杖用处很大,爬坂上坡,路稍陡直,用以撑杖,下雨泥滑,可防蹶倒,打站歇力时尤其用得着它,如同常说,是第三条腿。他们在路上休息时并不把背篓取下,取下时容易,再上肩费事,为养歇气力而花更大的气力,犯不着,只用那一根杖舒到后面,根着地,背绥放在月牙形手板上,自己稍为把腰伸起,两腿分开,微借着一点力而靠那么一会儿就成了。休息时要小便,也就是这么直着腰。他们一路走走歇歇,到了这儿,并没有一点载欣载奔的喜意,虽然前面马上就要到了。进了前面那个小小牌楼,就是西门,西门里就是省城了,省城是烧去他们背上的柴炭的地方,可是看不出他们对于这个日渐新兴起来的古城有甚么感情。小牌楼外有一片长长的空地,长了一点草,倒了一点垃圾,有人和狗拉的屎,他们在那里要休息相当时候。午前午后往来,都可以看得见许多这种人长长的一溜坐着,这时,他们大都把背上载着的重物卸放在墙根了,要吃饭,总不能吃饭时也顶着。
柴不知怎么卖,有没有人在路上喊住他们论价买去呢?炭则大都是交到行庄,由炭商接下来,剔选一道,整理整理,用装了石粉的布包在上面拍得一层白,漂漂亮亮的,再成斤作担卖与人家。老板卖出去的价钱跟向他们买的价钱相差多少,他们永远也无法晓得,至于这些炭怎么烧去,则更不在他们想象之内了。
他们有的科头,有的戴了一顶粗毡碗形帽子,这顶帽子吃了许多油汗,而且一定时常在吃进油汗时教他们头皮作痒。身上衣服有的是布的。但不管是甚么布衣绝对没有在他们身上新过,都是买现成的旧衣,重重补缀上身。城里有许多“收旧衣烂衫”男人女人,收了去在市集上卖,主顾里包括有这种人,虽然他们不是重要的,理想的,尤其是顶不是爽气的,只不过是最可欺骗的主顾。他们是一定买最破最烂的,而且衣服形形色色都有,他们把衣服的分类都简化了,在你是绝对不相同的,在他们是一样的。更多的是穿麻布衣服。这种麻不知是不是他们自己织的,保留最古粗的样子,印在陶器上的布纹比这还要细密些。每一经纬有铺子扎东西的索子那么粗,只是单薄一点。自然是原色,麻白色。昆明气候好,冬天也少霜雪,但天方发白的山路上总是恻恻的有风的,而有些背柴炭人还是穿一层单麻布衣服。这身衣服像一个壳子似的套在身上,仿佛跟他们的身体分不开,而又显然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跟身体离得很远,没有一处贴合,那种淡淡的白色使他们格外具有特性了。身体上不是顶要紧的地方袒露了一块,在他们不算是大事情。衣服,根本在他们就不算大事。他们的大事是吃一点东西到肚里。
他们每人都把吃的带着,结挂在腰裤间,到了,一起就取出来吃。一个一个的布口袋,口袋作成筒状,里头是一口袋红米干饭。不用碗,不用筷子,也不用手抓,以口就饭而喋接。随吃,随把口袋向外翻卷一点,饭吃完,口袋也整整翻了个个儿,抖一抖,接住几个米粒,仍旧还系于腰裤间。有的没有,有的有点菜,那是辣子面,盐,辣子面和盐,辣子面和盐和一点豆豉末,咽两口饭,以舌尖黏掠一点。看一个庄家,一个工人,一个小贩,一个劳力人,吃饭是很痛快过瘾的事,他们吃得那么香甜,那么活泼,那么酣舞,那么恣放淋漓,那么快乐,你感觉吃无论如何是人生的一点不可磨灭的真谛,而看这种人吃饭,你不会动一点食欲。他们并不厌恨食物的粗砺,可是冷淡到十分,毫不动情的,慢慢慢慢的咀嚼,就像一头牛在反刍似的!也像牛似的,他们吃得很专心,伴以一种深厚的,然而简单的思索,不断的思索着:这是饭,这是饭,这是饭……仿佛不这么想着,他们的牙齿就要不会磨动似的——很奇怪,我想不出他们是用甚么姿态喝水的,他们喝水的次数一定很少,否则不可能我没有印象。走这么长的路而能干干的吃那么些饭,真是不可了解的事。他们生在山里,或者山里人少有喝水的习惯?……我想起一个题目:水与文化。
老觉得这种人如何饮之以酒,不加限节,必至泥胡醉死。醉了,他们是甚么样子呢?他们是无内外表里,无层次,无后先,无中偏,无小大,是整个的:一个整个的醉是甚么样子呢?他们会拥抱,会砍杀,会哭会笑?还是一声不响的各自颓倒,失去知觉存在?
他们当然是有思索的,而且很深很厚,不过思索得很少,简单,没有多少题目,所以总是那么很专心似的,很难在他们的眼睛里找出甚么东西,因为我们能够追迹的,不是情意本体,而是情意的流变,在由此状况发展引度成为另一状况,在起迄之间,人才泄漏他的心,而他们几乎是永恒的,不动的,既非明,也非暗,不是明暗之间酝酿绸缪的昧暧,是一种超乎明暗的浑沌,一种没有限界的封闭。他们一个一个的坐在那里,绝对的沉默,不是有话不说,是根本没有话,各自拢有了自己,像石块拢有了石头。你无法走进他们里面去,因为他们不看你一眼,他们没有把你收到他们的视野中去。
纪德发现刚果有一种土人,他们的语言里没有相当于“为甚么”的字。……
在一个小茶馆外头,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人说话,而且是在算账!从他们那个还是极少表情的眼睛里,可以知道一个数字要在他的心里写完了,就像用一根钝钉子在一片又光又硬的石板上刻字一样的难。我永远记得那个数目:二百二十二,一则这个数字太巧,而且富民话(我听出他们的话带有富民口音)二字念起来很特别,再也是他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好像一个孩子努力的想把一个跌碎了的碗拼合起来似的,“二百——二十——二,二百,——二十,——二……”
有一次警报,解除警报发了,接着又发了紧急警报,我们才近城门又立刻退回去,而小牌楼外面那些负运柴炭的人还不动。日本飞机来过炸过了,那片地上落了一个炸弹,有人告诉我炸死了两个人。我忽然心里一动,很严肃的想:炸死了两个人,我端端正正一撇一捺在心里写了那一个“人”字。我高兴我当时没有嘲弄我自己,没有蔑笑我的那点似乎是有心鼓励出来的戏剧的激情。
(本篇原载1948年2月1日《大公报》;初收《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人间滋味:汪曾祺散文精选(读客经典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