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天早晨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间滋味:汪曾祺散文精选(读客经典文库)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礼拜天早晨
洗澡实在是很舒服的事。是最舒服的事。有甚么享受比它更完满,更丰盛,更精致的?——没有。酒,水果,运动,谈话,打猎,——打猎不知道怎么样,我没有打过猎……没有。没有比“浴”这个更美的字了。多好啊,这么懒洋洋的躺着,把身体交给了水,又厚又温柔,一朵星云浮在火气里。——我甚么时候来的?我已经躺了多少时候?——今天是礼拜天!我们整天匆匆忙忙的干甚么呢?有甚么了不得的事情非做不可呢?——记住送衣服去洗!再不洗不行了,这是最后一件衬衫。今天邮局关得早,我得去寄信。现在——表在口袋里,一定还不到八点吧。邮局四点才关。可是时间不知道怎么就过去了。“吃饭的时候”……“洗脸的时候”……从哪里过去了?——不,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天,杨柳,鸽子,教堂的钟声,教堂的钟声一点也不感动我,我很麻木,没有办法!——今天早晨我看见一颗凤仙花。我还是甚么时候看见凤仙花的?凤仙花感动我。早安,凤仙花!澡盆里抽烟总不大方便。烟顶容易沾水,碰一碰就潮了。最严重的失望!把一个人的烟卷浇上水是最残忍的事。很好,我的烟都很好。齐臻臻的排在盒子里,挺直,饱满,有样子,嗒,嗒,嗒,抽出来一枝,——舒服!……水是可怕的,不可抵抗,妖浊,我沉下去,散开来,融化了。阿——现在只有我的头还没有湿透,里头有许多空隙,可是与我的身体不相属,有点畸零,于是很重。我的身体呢?我的身体已经离得我很遥远了,渺茫了,一个渺茫的记忆,害过脑膜炎抽空了脊髓的痴人的,又固执又空洞。一个空壳子,枯索而生硬,没有汁水,只是一个概念了。我睡了,睡着了,垂着头,像马拉,来不及说一句话。
(……马拉的脸像青蛙。)
我的耳朵底子有点痒,阿呀痒,痒得我不由自主的一摇头。水摇在我的身体里顶秘奥的地方。是水,是——一只知了叫起来,在那棵大树上,(槐树,太阳映得叶子一半透明了,)在凤仙花上,在我的耳朵里叫起来。无限的一分钟过去了。今天是礼拜天。可怜虫亦可以休矣。都秋天了。邮局四点关门。我好像很高兴,很有精神,很新鲜。是的,虽然我似乎还不大真实。可是我得从水里走出来了。我走出来,走出来了。我的音乐呢?我的音乐还没有凝结。我不等了。
可是我站在我睡着的身上拧毛巾的时候我完全在另一个世界里了。我不知道今天怎么带上两条毛巾,我把两条毛巾裹在一起拧,毛巾很大。
你有过?……一定有过!我们都是那么大起来的,都曾经拧不动毛巾过,那该是几岁上?你的母亲呢?你母亲留给你一些甚么记忆?祝福你有好母亲。我没有,我很小就没有母亲。可是我觉得别人给我们洗脸举动都很粗暴。也许母亲不同,母亲的温柔不尽且无边。除了为了虚荣心,很少小孩子不怕洗脸的。不是怕洗脸,怕唤起遗忘的惨切经验,推翻了推翻过的对于人生的最初认识。无法推翻的呀,多么可悲的认识。每一个小孩子都是真正的厌世家。只有接受不断的现实之后他们才活得下来。我们打一开头就没有被当作一回事,于是我们只有坚强,而我们知道我们的武器是沉默。一边我们本着我们的人生观,我们恨着,一边尽让粗蠢的,野蛮的,没有教养的手在我们脸上蹂躏,把我们的鼻子搓来搓去,挖我们的鼻孔,掏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皮肤上发泄他们一生的积怨,我们的颚骨在磁盆边上不停的敲击,我们的脖子拼命伸出去,伸得酸得像一把咸菜,可是我们不说话。喔,祝福你们有好母亲,我没有,我从来不给给我洗脸的人一毫感激。我高兴我没有装假。是的,我是属于那种又柔弱又倔强的性情的。在胰子水辣着我的眼睛,剧烈的摩擦之后,皮肤紧张而兴奋的时候我有一种英雄式的复仇意识,准备甚么都咽在肚里,于是,末了,总有一天,手巾往脸盆里一掼:“你自己洗!”
我不用说那种难堪的羞辱,那种完全被击得粉碎的情形你们一定能够懂得。我当时想甚么?——死。然而我不能死。人家不让我们死,我不哭。也许我做了几个没有意义的举动,动物性的举动,我猜我当时像一个临枪毙前的人。可是从破碎的动作中,从感觉到那种破碎,我渐渐知道我正在恢复;从颤抖中我知道我要稳定,从难堪中我站起来,我重新有我的人格,经过一度熬炼的。
可是我的毛巾在手里,我刚才想的甚么呢;我跑到夹层里头去了,我只是有一点孤独,一点孤独的苦味甜蜜的泛上来,像土里沁出水分。也许因为是秋天。一点乡愁,就像那棵凤仙花。——可是洗一个脸是多么累人的事呀,你只要把洗脸盆搁得跟下巴一样高,就会记起那一个好像已经逝去的阶段了。手巾真大,手指头总是把不牢,使不上劲,挤来挤去,总不对,不是那么回事。这都不要紧。这是一个事实。事实没有要紧的。要紧的是你的不能胜任之感,你的自卑。你觉得你可怜极了。你不喜欢怜悯。——到末了,还是洗了一个半干不湿的脸,永远不痛快,不满足,窝窝囊囊。冷风来一拂,你脸上透进去一层忧愁。现在是九月,草上笼了一层红光了。手巾搭在架子上,一付悲哀的形相。水沿着毛巾边上的须须滴下来,嗒——嗒——嗒——地板上湿了一大块,渐渐的往里头沁,人生多么灰暗。
我看到那个老式的硬木洗脸桌子。形制安排得不大调和。经过这么些时候的折冲,究竟错误在那一方面已经看不出来了,只是看上去未免僵窘。后面伸起来一个屏架,似乎本是配更大一号的桌子的。几根小圆柱子支住繁重的雕饰。松鼠葡萄。我永远忘不了松鼠的太尖的嘴,身上粗略的几笔象征的毛,一个厚重的尾巴。左边的一只。一个代表。每天早晨我都看他一次。葡萄总是十粒一串,排列是四,三,二,一。每粒一样大。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张桌子的木质,那些纹理,只要远远的让我看到不拘那里一角我就知道。有时太阳从镂空的地方透过来,斜落在地板上,被来往的人体截断,在那个白地印蓝花的窗帘拉起来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厚磁的肥皂缸,不上釉的牙口磨擦的声音;那些小抽屉上的铜页瓣,时常的的的自己敲出声音,地板有点松了;那个嵌在屏架上头的椭圆形大镜子,除了一块走了水银的灰红色云瘢之外甚么都看不见。太高了,只照见天花板。——有时爬在凳子上,我们从里头看见这间屋子里的某部分的一个特写。我仿佛又在那个坚实,平板,充满了不必要的家具的大房间里了。我在里头住了好些年,一直到我搬到学校的宿舍里去寄宿。……有一张老式的“玻璃灯”挂在天花板上。周围垂下一圈坠子,非常之高贵的颜色。琥珀色的,玫瑰红的,天蓝的。透明的。——透明也是一种颜色。蓝色很深,总是最先看到。所以我有时说及那张灯只说“垂着蓝色的玻璃坠子”,而我不觉得少说了甚么。明澈,——虽然落上不少灰尘了,含蓄,不动。是的,从来没有一个时候现出一点不同的样学。有一天会被移走么——喔,完全不可想象的事。就是这么永远的寂然的结挂在那个老地方,深藏,固定,在我童年生活过来的朦胧的房屋之中。——从来没有点过。……我想到那些木格窗子了,想到窗子外的青灰墙,墙上的漏痕,青苔气味,那些未经一点剧烈的伤残,完全天然的销蚀的青灰,露着非常的古厚和不可挽救的衰素之气。我想起下雨之前。想起游丝无力的飘转。想起……可是我一定得穿衣服了。我有点腻。——我喜欢我的这件衬衫。太阳照在我的手上,好干净。今天似乎一切都会不错的样子。礼拜天?我从心里欢呼出来。我不是很快乐么?是的,在我拧手巾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很快乐。我想到邮局门前的又安静又热闹的空气,非常舒服的空气,生活——而抽一根烟的欲望立刻淹没了我,像潮水淹没了沙滩。我笑了。
疯子
我走着走着。……树,树把我盖覆了四步。——地,地面上的天空在我的头上无穷的高。——又是树。秋天了。紫色的野茉莉,印花布。累累的枣子。三轮车鱼似的一摆尾,沉着得劲的一脚蹬下去,平滑得展出去一条路。……阿,从今以后我经常在这条路上走,算是这条路的一个经常的过客了。是的,这条路跟我有关系,我一定要把它弄得很熟的,秋天了,树叶子就快往下掉了。接着是冬天。我还没有经验北方的雪。我有点累——甚么事?
在这些伫立的脚下路停止住了。路不把我往前带。车水马龙之间,眼前突然划出了没有时间的一段。我的惰性消失了。人都没有动作,本来不同的都朝着一个方向,我看到一个一个背,服从他们前面的眼睛摆成一种姿势。几个散学的孩子。他们向后的身躯中留了一笔往前的趋势。他们的书包还没有完全跟过去,为他们的左脚反射上来的一个力量摆在他们的胯骨上。一把小刀系在练子上从中指垂下来,刚刚停止荡动。一条狗耸着耳朵,站得笔直。
“疯子。”
这一声解出了这一群雕像,各人寻回自己从底板上分离。有了中心反而失去中心了。不过仍旧凝滞,举步的意念在胫踝之间徘徊。秋天了,树叶子不那么富有弹性了。——疯子为甚么可怕呢?这种恐惧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只是一种教育?惧怕疯狂与惧怕黑暗,孤独,时间,蛇或者软体动物其原始的程度,强烈的程度有甚么不同?在某一点上是否是相通的?它们是直接又深刻的撼荡人的最初的生命意识么?——他来了!他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中等身材,衣履还干净,脸上线条圆软,左眼下有一块颇大的疤。可是不仅是这块疤,他一身有说不出来的一种东西向外头放射,像一块炭,外头看起来没有甚么,里头全着了,炙手可热,势不可当。他来了,他直着眼睛走过来,不理会任何人,手指节骨奇怪的紧张。给他让路!不要触到他的带电的锋芒呀。可是——大家移动了,松散了,而把他们的顾盼投抛过去,——指出另一个方向。有疤的人从我身边挨肩而过,我的低沉的脉跳浮升上来,腹皮上的压力一阵云似的舒散了,这个人一点也不疯,跟你,跟我一样。
疯子在那里呢?人乱了,路恢复了常态,抹去一切,继续前进。一个一个姿势在切断的那一点接上了头。
三十七年九月,午门。
(本篇原载《文学杂志》1948年三卷六期;又载《中国新诗》1948年第五期;初收《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人间滋味:汪曾祺散文精选(读客经典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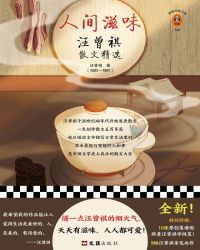


![迷人病[快穿]](/uploads/novel/20210402/2ac514d738c09977a302f3f318650fc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