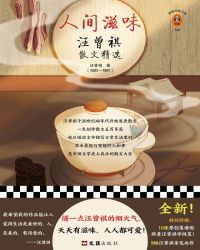古代民歌杂说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间滋味:汪曾祺散文精选(读客经典文库)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古代民歌杂说
说《弹歌》
断竹,续竹;
飞土,逐肉。
这是一首现存最古的中国歌谣。《文心雕龙·章句篇》云:“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黄世”是黄帝之世,黄帝之世,代表一个很古远的时代。这大概是可信的。
这是一首关于弓弹的歌谣。玩其词义,盖创作于弓矢、弹丸发明不久之后。
中国的弓弹在何时发明,现无确考,照常理推测,是先有了弓矢,然后再有弹丸的。弹丸是矢箭的代用品,取其携用均较轻便,在对付细小的目的物时用它较为合适。越国有一个陈音,他是认为先有弹,后有弓的。《吴越春秋》:“陈音对越王云:‘弩生于弓,弓生于弹……’”。他所谓弓,按文义,是包括箭的。这不见得有什么根据。说“弓生于弹”,可能是因为弹之制作,比弓简单,搓土为丸,唾手可得,不像弓矢又是镞,又是苛,还要加上羽那么麻烦。其实不然。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发射物,而在发射体。弓矢的发明是人类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及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这是很对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人们知道了利用弹力,利用弓弦以发生弹力,知道了利用最初的机械。弦的发明是决定性的条件。其次才是矢、弹。而且最初的矢大概也不是像后世所用的那么精工,很可能即是利用原来打猎和打仗用的棍棍棒棒而带有锐尖的扣在弦上,嘣的一声发射出去,这样就能在一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远距离之外打击敌人与猎物。于是掌握了箭的人便有了莫大的威力。《易》:“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说得很近情理,很可信。弓矢的发明很可能在金属的发明之前。关于矢的不用金属,其他的例证还有《左传》:“楚灵王曰:‘……昔日先王熊绎,澥在荆山,唯是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太平御览》引《魏志》:“挹娄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总之,说“弓生于弹”,没有什么根据。我们宁可相信后汉李尤的话:“昔之造弹,起意弦木,以丸为矢,合竹为朴,漆饰胶治,不用筋角”(《太平御览》引《弹铭》)。弹的发明,当在弓矢之后,但也不会很久,因为已经有了弓弦,用它代矢便不用费很多脑筋,很多时日。
说了这些话的目的,旨在说明:这首歌谣的创作盖在弓矢的发明之后不久的。
弓矢的发明,照恩格斯说,是在“蒙昧时代”的最高阶段。《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蒙昧时代……最高阶段……是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的……:写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器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这是根据大量材料而得出的不可辩驳的结论,应用于中国的历史也不能例外。如果肯定弹之发明后于弓矢之发明不久这个前提,那么,我们便可进一步推绎,这首歌谣的创作,至多距离“蒙昧时代”也不会很久。宽泛一点地说这是“黄帝之世”时代的歌谣,是有相当充分的理由的。
肯定了这首歌谣的创作的时间,我们便有条件来谈论这首歌谣的性质和内容了,就越发觉得那位陈音的话可以说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吴越春秋》:“陈音对越王云:‘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质,饥食鸟兽,渴饮雾露,死则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故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之谓也。’”
如果我们相信恩格斯的话,对陈音的话是很容易驳斥的:蒙昧时代,家庭尚未确定形成,那个时候,还无所谓孝子,也没有“孝”这个观念,生养死葬这一套伦理还要经过一整个历史时代才能产生,把这首歌谣解释为孝子之歌,是后世儒者的造谣,是托古说教。
那么这是一首什么歌谣?弓弹是猎具,猎具为猎者发明与使用,这是一首猎者之歌(当时的社会尚无精密分工,从猎者盖是一部族之全体,也可以说是从猎的全民之歌),所歌的是行猎。是猎具,是弹。《弹歌》者,弹之歌也,如是而已。
弹是猎具,而且大概是专门用来打鸟的(很有可能古人用箭以猎兽,用弹以猎鸟。兽体大,宜用锐镞以深中要害,鸟体小,弹丸足以致死且得完肉。如乐府《乌生》所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鲁迅《奔月》中写后羿用大箭射麻雀,结果把一匹麻雀射得粉碎,这是很有趣,也很近情理的想象,他如果知道用弹,那结果就会好一些)。《庄子》“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可为一证。李尤《弹铭》也分明说“丸弹之利,以弋凫鹜”。
这是一个关于打猎的歌谣,更进一步,试为作一悬解,曰:这是一段猎人的咒语。
芬兰史诗《卡列瓦拉》写约卡赫伊宁在等待着华奈摩伊宁走近一些的时候,念着咒语:“我的弓弦哪,你要有弹力,呵,橡木箭哪,你要快得像光速一样;毒箭头哪,你要对准华奈摩伊宁的心……”这可以作为射箭之前念咒语的一个遥远的旁证。在中国,则《水浒传》里“放冷箭燕青救主”一回中,燕青在发箭之前念叨的一句“如意子休要负我”!在性质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咒语,不过是缩短成一句语气急迫的散文了。
这一首歌谣,四个短句,通体用的是隐语。前两句说的是弹弓的制作。断竹,续竹,在字面上造成一种矛盾。既已断之,又复续之,似乎不可理解。所谓“续竹”,即合竹为朴,再加以漆饰胶结,使竹之两端联结,并非使已断之竹按原茬再接起来。下面两句是说的弹的作用,但不直说,而用代语,以土代丸,以肉代鸟兽猎物。这样的回互其词,假如不标出题目是《弹歌》,乍一看,是不大容易看明白意思的。代语,字面矛盾,是谜语的常用的手法。这是一首谜语,一首中国的最早的谜语——也是作得很巧的,耐人寻味的谜语之一。
而,谜语,最初的谜语,按民俗学家的研究,是有咒语的作用的。它运用这种曲折费解的语言,不是为了游戏,而是企图由此产生一种神秘的力量,去支配自然,达到所期望的效果。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它怎么会“想出”这样有意思的隐语:直接用“肉”以代鸟兽。原来贯串全文的“最高任务”(借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术语)正是为了——得肉。正如庄子所说的一样:“余因以求鸮炙”。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庄子简直想得更为急切,一提到弹弓,马上就想到一只烧熟了的野鸡;于此倒可见古之人是更为“质朴”一点的,只想到肉,没有更往远处幻想一步。
我们弄清了(或者说:假定了)这首歌谣的性质,这不但不有损于这首歌谣的艺术价值,反之,我们正因为知道我们的祖先创作这首歌谣的目的,而更能亲切地感觉到它的情绪。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的祖先,一手挽定强弓,一手捏着泥弹,用足了力气,睁圆了眼睛,嘴里念道: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然后嗖——的一弹打出去。古代的语言难于复现,但是如果采用广东话或者吴语来念,念出了歌谣中的四个入声,还是能够很具体地感到那种紧张殷切、迫不及待的热烈情绪的。我们在这里一样也能感觉到人对于自己能够制造工具,对于工具的赞美(所飞者土,所费者微;所逐者肉,所得者大,这多么好啊!)和对于自己的聪明和威力的自豪,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先民在草莽时期的生活的气氛。这些,我想是我们在隔了一个很邈远的时间之后,读起这样短促的歌谣还能获得感动的根本原因。我们读到这首歌谣,总是得到一种感动,尽管我们弄不分明我们为什么会受感动。
我们很容易想到摩尔根记载的澳洲人打袋鼠的歌谣和舞蹈——那全部的仪式。是的,我们可以这样地联想,这是对我们有启发的。这同样是用了语言、音乐和形体来影响、支配自然,获得胜利。很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这首歌谣的音乐和伴随它的舞蹈,也不能确定它是否与音乐、舞蹈相联系着,它是否附丽于一定的形式;但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动摇我们对于这首歌谣之具有形式的、符咒的作用的信念。
如果种种假说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起源说找到一条新的、中国的佐证。艺术是为了生活,为了和自然作斗争,为了某种物质的目的,为了——“逐肉”;艺术不是弄着玩玩的。
1960年11月21日 沙岭子
说《雉子班》
“雉子,
班如此!
之于雉梁,
无以吾翁孺
——雉子!”
知得雉子高蜚止,
(黄鹄蜚,之以千里王可思)
雄来蜚从雌:
“视子趋一雉。”
“雉子!”
车大驾马滕,
被王送行所中,
尧羊蜚从王孙行。
这是一个悲剧,一首雉家族的生离死别的,惨切的哀歌。
雉的家庭——雄野鸡、雌野鸡带着他们的孩子,小野鸡,正和一群野鸡在一起,雌雄群游于山路,自得其乐。忽然天外飞来横祸,一面密网盖下来,母亲——雌野鸡被扣住了。这是一个游遨行猎的王孙撒下来的网。小野鸡年纪小,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事,吓得忒愣愣一翅子就飞跑了(同时飞跑的还有别的野鸡),他一个劲儿往深山里飞。雄野鸡在仓惶之中还没有完全失去方寸。他这时两头牵累:一头是娇子,一头是爱妻,两头都放不下。首先招呼孩子!他追在他后面高声地叫:“孩子,就这样飞!一直飞到咱们老家,别回头,别跟着我们公姆俩!”看着小野鸡飞远了,他放了心,小野鸡得了活命了;但是他也知道他们从此就见不到他们的孩子了,他看着他越飞越远的后影,叫了一声:“孩子!”知道孩子已经高飞远走了,雄野鸡折回来,又追上被捕的雌野鸡。第一件事,是告诉雌野鸡:“我亲眼看见咱们的孩子跟在一个大野鸡后头了。”孩子已经有了依靠,好叫做母亲的放下心(这可能是他看到的,可能是编造出来安慰母亲的)。母亲也是一样,一方面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一方面知道跟孩子是永远见不着了,惨叫了一声:“孩子!”雌野鸡的命运是注定了:这位王孙是个很显赫的贵人,乘的车又大,驾车的马又快得像飞,雌野鸡被一直送到王宫里去,一点生还的希望都没有。雄野鸡这时心意已决,他的心倒塌下来了:只有这样:我跟她一起去,永不离开!他一翅一翅地飞,跟定了王孙的车子飞……
这是一首一向被认为很难读通的乐府诗。闻一多先生以为鼓吹铙歌十八曲中,这一首和《圣人出》、《石留》等三篇最为难读,很谨慎地说:“此歌皆不可强解,今唯略读一二,阙所不知。”(《乐府诗笺》)余冠英先生花了许多工夫,把这首乐府凿开了一条蹊径。但我觉得余说尚不够圆满,有些地方忽略,有些地方看拧了,按余说读,仍不够通畅。今强为索解,解如上。亦有说,说如下:
“班”我以为即“翻”,按古无轻唇音例,这两个字的读音原来一样(我很疑心“乘马班如”的“班”也当作飞跃讲)。“雉梁”余注以为是“野鸡可以吃粱粟的地方”,未免迂曲,而且这样长的句子缩成了“雉梁”两个字,这种文法也值得商榷。我觉得梁就是山头,现在也还有这么说的:“山梁子”。“雉梁”即野鸡群居的山梁子。或者简直就叫做“野鸡梁子”,也很合乎口语。“无以吾翁孺”,我以为各字都当如字直解。以,依也。吾,我或我们也。翁是老头儿。孺是女人。按孺本训小,一般指小孩子为孺或孺子。但是古时也有把小妻称为孺子的。清俞正燮《癸巳类稿·释小补楚语笄内则总角义》条:“小妻,曰妾、曰孺、曰姬……曰孺子……或但曰小”;下面还引说:“《汉书·艺文志·中山王孺子妾歌》注云:孺子,王妾之有名号者。《齐策》云‘王有七孺子’,韩非书作‘十孺子’,又《韩非·八奸篇》云:一曰在同床贵夫人爱孺子是也。《左传·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南孺子生子,谓贵妾。注云:桓子妻者,非是。《秦策》亦云‘某夕某孺子纳某士’;《汉书·王子侯表》‘东城侯遗为孺子所杀’;则王公至士民妾,通名孺子……”足证古代是把妾称为“孺子”的。这里的雌野鸡也可能是雄野鸡的小老婆,但是我们对野鸡的妻室还是不必严格区别正庶吧。那大概就是笼统地指的是老婆。呼之为小,不过如俞理初说怀嬴称婢子,是“闺房暂言,不拘礼称”,两口子说话,不讲究这些。《左传·哀公三年》的误注,以为“孺子”为桓子妻,倒给了我们一个反证,原来古代妻也是可以称“小”的,这一点可以马虎。称之为“孺”,视之为小,这可能是为习惯上轻视妇女的意识支配,也很可能是一种爱称。侯宝林说相声,说对于妇女的称呼大都加一个小字,如小丫头,小媳妇,而男人则多称大,大老爷们,大小伙子,吁,是则妇女称小,自古而然,于“今”未变也矣。总之,我以为解孺为妻,是可以说得通的。“翁孺”对称,亦犹北朝乐府《捉搦歌》中的“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的“翁妪”,即“公姆俩”“两口子”“两夫妻”也。“翁孺”“翁妪”声音原极相近,即说是可以通假,也不为勉强。按此,则“无以吾翁孺”就是“别跟着我们公姆俩”,意思是叫雉子去自寻生路。“知得”即得知。“高蜚止”的“止”是语尾助词,犹“高山仰止”的“止”。“黄鹄蜚,之以千里王可思”,如果作本文读,依余注,亦可通。或者干脆一点,把它看作是衍文,或者是夹杂进来的非本文性的词句亦可。乐府中常有与文义无关的字句杂入,使本文变得奇拗难读。旧来以有两种情况,一是“声词相杂”,一是“胡汉相混”,我设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帮腔或衬字也不分字体大小和本文杂写在一起了。这种与文义无关或无直接关系的词句,最初大概是由群众帮腔或歌伴和唱,也有即由演唱者自己唱出的。“小放牛”村女叫牧童“牧童哥,帮腔来”,帮的是“七个弄冬一呀嗨,八个弄冬一呀嗨,一朵一朵莲花开”;单弦牌子曲“金钱莲花落”“太平年”都有和唱;四川的抒情山歌中竟会夹进字面上与本文情调似极不相及的插语“猪油韭菜包包子,好吃不好吃?”这要是跟本文连写,非此时此地人,将觉大惑不解。我疑心,“黄鹄蜚,之以千里王可思”和《蜨蝶行》里的“雀来燕”可能都是帮腔衬字,为唱禽鸟故事时所常用。如果是这样,如果作为文字材料来读,可以撇开不管,“知得雉子高蜚止,雄来蜚从雌”,意思更为紧凑,如果演唱,则这一类帮腔和唱照例是不影响情节的展开和情绪的连贯的,唱自由他唱,解吾亦如此解。“趋”,追随也。以下词句并可从余注。
把这首诗看成是野鸡家庭的惨剧,这一点余先生是和我相近的,但是我们对情节的理解不同。这里关键问题在这个悲剧中谁是被难者,谁是悲剧的主角。照余注,被猎获的是小野鸡,而剧中的主角就很模糊,似乎忽此忽彼,无一专主。我以为被捕的是雌野鸡,而剧中主角是雄野鸡,全部故事都是集中在他的身上,紧贴着他而写出的,贯串全诗的是他的情绪,这样才紧张,才生动。余注的立脚点恐怕是“知得雉子”的一个“得”字,以为是说雉子被人“得”着了。但是“得”是就人来说的,就雉来说,是罹,而不是得。看全诗,全是代雉立言,立场在雉的一面,不应用此主宾颠倒的词。如依余注,则全部情节似乎是这样:雄野鸡送小野鸡飞出去寻食,告诉他路上要小心,提防着人这种东西。后来知道小野鸡被人得着了(怎样知道的呢?),雄野鸡赶紧飞来,又跑到雌野鸡那儿去;然后,他或他们再跟着王孙的车子一起飞。雄野鸡这样跑来跑去,于情理上既无可解释,情节上又颇破碎。这雄野鸡简直是个老糊涂,既知要小野鸡对老头小孩都要避着点,怎么还放心得下让他一个人去冒险瞎闯呢?而且照余说,则“雄来蜚从雌”“视子趋一雉”都没有着落。“从”字意思很显明,只能作眼随讲,这个“从”字就是下面的“尧羊蜚从王孙行”的“从”,所从者是一雉,并非二雉(从王孙即从王孙车中之雉)。如果照余说被捉的是雉子,怎么又还能“视子趋一雉”呢?是看见他在笼子里跟随了另一只野鸡了么?但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已经被捉,有雉可趋与无雉可趋是一样的,临死即拉上一个垫背的,也不见得有什么可安慰处。
从艺术结构上看,笼贯全诗大部分的是一种绝望的,张皇急骤的调子。“雉子,班如此!之于雉梁。无以吾翁孺,雉子!”分明是一连串迫切的呼喊,一开头即带来了十分紧张的气氛,说明着一场不测的剧变。余注:“班”即“斑”,“班如此”是老野鸡夸赞小野鸡羽毛斑斓好看(野鸡羽毛富于文采,容易叫人往斑斓好看上想,倒是很自然的),与这种短促、断续的语调实不相合。即依余注,被捉的是小野鸡,而小野鸡很快就要罹祸,老野鸡却在事先平白无故地夸赞其羽毛,这在构思上实嫌蔓远,不够集中。而且“班如此”与“之于雉梁”也不相衔接。试翻成白话看:“孩子,你长得真花哨,你去到野鸡可以吃粱粟的地方去!不管遇着老人和孩子都要提防着一点,孩子!”这么东一句,西一句的,有这样说话的么?若依我的解释,在“雄来蜚从雌,‘视子趋一雉’”之后第三个“雉子”(可能是雌野鸡单独呼叫,也可能是两只大野鸡同时哀呼)处,达到全剧的高潮,以下雄野鸡既已下了决心,情绪上趋于悲剧性的镇定,最后三句的调子,也相应地缓慢舒徐下来,渐行渐远,有余不尽。若依余注,则两只大野鸡同来随定囚载小野鸡的车子而飞,在第三个“雉子!”处情节应仍未展尽,下面仍应有较紧张的戏剧动作,可是最后三句的音韵与这个需要是不相合拍的——请注意这首诗用了两个韵,第二个“雉子”下换了一个韵。前面“子”“此”“孺”“止”“雌”“雉”,连用齐齿呼,声音比较滞涩,令人有窒息之感,真好像是在吱吱的叫似的(诗人用韵时下意识受到了鸟叫的暗示?),而后三句的“滕”“中”“行”却是平和而安静的。这样的转换用韵(三句中其他字的音色也比较浏亮),是服从情景的需要,不是偶然的。
也许会有人说,你把这首诗解释得似乎“太”好了,简直是“神”了,这么一解释,这首民歌岂不是完全可以读通了么?这首乐府的艺术表现岂不是太完整,这样的非凡的洗练,紧凑,生动,集中,这样的如闻其声的对话,这样强烈的戏剧性,这不是太现代化了么?这样的来解释一个两千年前的作品,合适么?这不是有点太冒险了么?是的,我也正在犹豫着哩。不过,我想,如果我们有一定的根据,那就应该把话说得足足的,一点也不保留,一毫折扣也不打。抱残守阙,不是我们今天应有的态度。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大胆些,更大胆些。即使是错了,怕什么?
如果我的解释按常理既可说通,诉诸训诂,尚不悖谬,大体上可以成立,我是很快乐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对于这首诗的思想和艺术就可以作充分的估量;对乐府中犹存的几首动物故事诗,甚至对整个汉乐府所反映的那一时代的生活,它作为集体创作所表现的鲜明、深刻的人民性,就可以增添一分肯定,我们对民族的、人民的文化遗产就可以多一分自豪。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原载《北京文学》2007年第五期) 人间滋味:汪曾祺散文精选(读客经典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