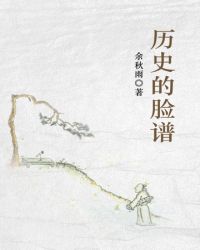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历史的脸谱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几年前当电视剧《三国演义》播出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呼吁要把年轻人从电视机前拉开,拉回到《三国演义》的文字原著上。因为那些孩子都在看那个电视剧,我发现当时即使是不同意这种呼吁的人也不敢理直气壮,只是轻声轻气地辩解说电视剧有可能引导年轻人去读文字原著。
对此我要理直气壮地在这儿说点儿反话了。我认为年轻人看《三国演义》的电视剧比读文字原著更重要,什么理由呢?因为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表达,而是一种综合工程。同样一段文字,古人是用什么节奏抑扬顿挫地说出来的?他们怎么穿衣服,怎么礼让,怎么宴饮,怎么参与一个个社交仪式,举起什么样的武器去打仗?这一切,文字原著无法感性的直观的提供,只有到了有多方学者和艺术家集体参与的影视作品当中才能完整呈现,或者说才能“全息呈现”。而且,历史上那些文本啊,其实优秀的也不多,不要以为那种原著文本一定就好,比如《三国演义》在文学上比《红楼梦》就差得太远太远。
……
那个伪精英架势的文人强迫大家去读原著,其实他们自己根本也做不到。按照这个说法,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果要演出就不能看的了,只能读原著,而且不能读中文原著,要读英文原本,而且还不能读一般的英文原本,必须读古英文的原本,最好是没有整理过的古英文原本,请问能做到这一点的,全世界有几个人?
中华文明
有的学者一直在下这样的结论,比如:中华文明喜欢协调,其他文明喜欢冲突;中华文明喜欢人文,其他文明喜欢科技;中华文明喜欢写意,其他文明喜欢写实等等是这样吗?大家粗粗一想就知道,连最起码的常识都通不过。
这就值得我们深深一叹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惊人速度已经让全世界震惊,而我们进行文明比较的水平还停留在林则徐时代,这同样让人震惊。
我也参与过这样的文化讨论,后来感觉到自己的可笑,终于在苦苦思索之后找到了一条最简单的道路,那就是:中华文明与别的文明千不同万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只有它活下来了;中华文明的优势,也只能从这么一个唯一的事实当中去寻找。
汉字
大家猜,我找到的第一项中华文明的长寿秘密是什么?居然是汉字。对,就是我们一笔一画从小写到大的汉字。
这是一个对自己习以为常的文化手段的震撼性的发现。那天我在埃及卢克索的太阳神庙考察,那些巨大的石柱上的象形文字吸引着各国参观者的目光。因为是象形,似乎不难破解,但问来问去,连那儿的专家都不认识。他们告诉我,古代战争一结束,胜利者总是严令废除被占领地的文字。因为文字包含着历史,隐藏着尊严,意味着沟通,甚至于预示着复辟。废除文字就等于废除一国的文化传承,这比杀害它的百姓、抢夺它的财物都来得严重。但是,这么严重的事情要做起来却很方便,因为古代识字的人本来就不多,把他们消灭是举手之劳,如果占领者特别仁慈的话,只要把识字者和那些文字分开就可以了,特别像埃及的那些神庙里边的祭司,把他们相继赶走,那么等他们去世的时候,废除文字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有的时候文字还在,刻在石柱石碑上,但谁也不认识,那也等于废除了。埃及卢克索太阳神庙石柱上的那些象形文字,像鸟,像雨,像虫,但是它们曾经是有意义的,表达了人类的崇高祝愿。现在这些鸟、鱼、虫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含义,回到了自然意义,在人们茫然的目光当中僵硬千年。
……
这么一想,那天我在尼罗河边突然对《论语》、《孟子》、《道德经》这些古代经典产生了一种几乎想流泪的亲切感。你看,同样是两千多年,我们读着它们,仍然像读乡下外公的来信。什么叫死亡?什么叫活着?这就叫活着,一种惊人的活了两千多年而从未死亡过的文化。证明它活着的,是历代几千万读书人,包括我们。
奇迹
……又一个中国古代战场,战旗猎猎,喊声震天。天上战争之神睁大了眼,而文化之神却闭起了眼。因为战旗上写的都是汉字,喊叫的都是汉语,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对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大一统始终保持着理性的审视态度,因为由此产生的消极面太大了,但是,对于文字统一却是例外,完全给予正面评价,因为它是一种伟大文明始终没有失去“人文共同体”的基座。为了这个原因,我写过,我们在尼罗河边的芦苇丛中曾经对秦始皇产生感念。
不要再把汉字仅仅看作书法工具。它是活着的图腾,永恒的星辰。在文字领域,它是全人类唯一的奇迹。
汉字简化
我是支持汉字简化的,理由有下面几点:第一,自汉代以来,汉字每一代都在简化;第二,二十世纪的汉字简化,是因为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在教育、科技上落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汉字太复杂,难教难学,因此提出过废除汉字、改用世界语的主张,罗马化的主张,拉丁化的主张。汉字简化既改变了它难教难学,又防止了它过于拉丁化的、过激的拉丁化这种设想;第三,在一九三五年国民**就公布过第一批的简体字表有三百多字吧,大陆的做法只是延续;第四,大陆的汉字简化,不是出于凭空乱想,而是集中了历代书法家在写行书和草书的时候的简笔方式,和民间生活当中长期使用的简笔方式;第五,事实证明,大陆的那次简化对于扫除文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因此,在我看来,大陆在五十年代实行的这次汉字简化,是中国文化“变而守本”的一个成功范例。而不是一个失败的典型,只有这样的变,才能保全汉字不必走向拉丁化和获得普及。我也请大家不要小看五十年代大陆“扫除文盲”的运动,如果没有那个运动,也就没有今天大陆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中华文明,由于文字又一次放松身段而扩展了它的生命。
凶兆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是世界最早发明文字的地方之一,有人还认为那里是各文字系统的共同源头,但是那个地方一直处于战乱之中,直到今天。文明破碎了,这是人人看到的,但是最让我动心的,是文字的破碎。
那里有一种早期的楔形文字值得全人类膜拜,而且这种文字现在也能够部分地解读。但遗憾的是,我到那儿,在新修复的巴比伦城墙前惊喜地看到楔形文字居然是一句现代的政治口号。当我们的朋友顾正龙先生翻译给我听的时候我大惊失色,因为这里已经失去了对古代文字应用的尊重。当古文字成了现代政治的奴仆,那么,整个古代巴比伦文明也就成了现代政治的筹码。这种不懂轻重、不顾辈分的现代政治,还会有希望吗?没有希望了,说实话,就在那句以楔形文字写出的现代政治口号前,我预感到了这个地方的凶兆,我已经看到了某一种炮火连天的情景。
空间
那天,在耶路撒冷的著名的哭墙前,很多犹太人把自己的头抵在墙前,流着眼泪,念念有词。在他们的上方,是那座非常著名的清真寺,一些阿拉伯女孩正用陌生的眼光看着眼下的一切。我们刚刚接触的是另一个大文明,就是不远处的耶稣受难的“苦路”,看了那个苦路回来,正遇到有一群参观哭墙的中国农民企业家在那儿。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认出了我,就走上前来问:“余老师,我们中国人好像比不上犹太人的民族感情,我们没看到过哪一个中国人头抵着万里长城流泪不止。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吧?”
我当时就回答:“不必。犹太人流浪千年,在故乡只剩下了这么一堵墙,谁见了都会流泪。我们中国虽然也历尽艰辛,却从来没有到过这种空间尽失的地步。中华文明一直拥有辽阔的流转空间,我们不哭,我们也不必学人家哭。在这里,我才知道什么叫泱泱大国。”
大
在中国的文化话语里边,从来离不开空间视野,你看啊,总是一开口就是三山五岳、****、四极八荒、六合九州。就像“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这样的诗句,最容易让中国人动心;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文句,很容易让中国人动情。比较起来就是说小鼻子小眼、小家子气、小肚鸡肠、鼠目寸光、井底之蛙,永远是中国文化的贬斥之词,“好男儿志在四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永远是中华文化的励志之语。大空间,永远是大空间,这就是成了中华文化的一种精神规模。
在中国大地你常见这样的景象:不管时世如何,你走到大山深处,突然发现一所简陋的小学,里边有孩童的书声传出来;你到一个偏僻的小镇的茶馆去闲坐,悠然听到旁座有人在轻声谈论一个古代的经典。这种文化渗透到了千里万里之间,每一个大地的皱褶当中都接受了,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文化确实和大地同寿。
极端
任何宗教到了中国,往往就不极端了。这证明,中国广大民众当中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化背景,它可以磨掉极端主义的锋棱。这里我可以讲几句我自己非常崇敬的佛教。我曾在尼泊尔和印度各地,虔诚地考察过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创立佛教、传播佛教的大部分行迹,还到过他创立佛教前修行多年的那个洞窟。那种修行的方式带有明显的极端倾向,所谓日进粒米,骨瘦如柴,这个行为令人震惊,令人感动,但毕竟是一个不太可能被广泛接受的大宗教的样子。后来释迦牟尼终于下山,在尼连河边吃了东西,洗了澡,向那棵菩提树走去。我按照他的路线走了一遍,知道这是对一种极端方式的摆脱,回到了正常方式走向伟大。但是,在释迦牟尼之后,佛教的传播又出现了繁琐论辩的极端化倾向,大量智慧的头脑加重了佛教的学究性、门派性,结果只能渐渐地衰落。但是一到中国就不一样了,大家看,佛教吸纳进了敦煌式的色彩和舞蹈,吸纳进了名山大川的美景,融入了儒者的潇洒而成为禅宗,又融入了中国式的伦理观念而走到了千家万户,甚至,像我祖母这一辈连一句佛经也读不懂的妇女,全都成了虔诚的佛教徒。这在基本教义派看起来,那简直是太不“认真”了,我以前对此也产生过疑惑,但是当我到了事事都极端认真,认真得每天打架的耶路撒冷我才明白,我们中国确实不需要耶路撒冷式的“认真”。
魔或者佛
极端主义的思维模式,初一看确实是非常纯净,一尘不染。他们主张“离佛一尺即是魔”,这里边包含三层意思:第一,这个世界上要么是佛,要么是魔,不存在中间地带;第二,佛的要求很高,因此地盘很小,一尺之外都是禁区;第三,既然稍稍离开就是魔,是魔就要用极端方式消灭。这就是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尽管他们不一定讲那句话了。
那么,中国式的寻常物理正好相反,中国就主张“离魔一尺即是佛”。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敢于离开邪恶一步,就立即成了光明世界的一员,佛的门槛不高,佛的天地很大,人人都可以进入。这种思维不在乎极端意义上的佛和极端意义上的魔,只取中道,而且由中道来协调整个世界,使之和谐。
立地即成
这种思维显得很宽厚,也很仁慈,因为它对魔都产生了一种召唤,让他们跨出一步改恶从善,我们平常经常听到的所谓“回头是岸”、“立地成佛”就是这个意思;相反,极端主义这个思维对于真正的佛都产生了威胁,要他们不能越雷池半步。因此,孔子就把中庸说成是道德的最高标准,这就很有道理了。因为它非常仁慈,非常宽厚,倒过来,我们也必须指出,那些极端主义虽然纯净,却是最不道德的。
……电视台记者采访一对百岁夫妻,问:“你们一生经常吵架、怄气吗?”
老太太说;“那怎么活得下来?”老大爷说:“浑浑沌沌才有百年。”但他的口气斩钉截铁,一点儿也不浑沌。
宁肯如此
请大家想一想,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有大量的年轻人,包括一些妇女,无怨无悔地浑身绑着**成为自杀**,自杀袭击的工具,伤害了大量无辜的民众,这不仅仅是对无辜的民众是不道德,而且对于这些人本身也是不道德的。是什么力量使他们无怨无悔的成了人类公义的敌人?是极端主义。极端主义的诱惑力,实在不能小看了,尤其是对年轻人。
大家可能记得,我在考察人类古文明的那本日记叫《千年一叹》当中留下了一些我和阿拉伯的小孩和以色列的小孩的一些一起拍的照片,我在照片下面写道:“难道这些孩子,几年以后注定要匍匐于战场?”这正是我一路最大的不忍。因为我看到,比他们年纪稍稍大一点儿的年轻人,已经要拿着枪上街吃饭了。
是的,他们的目光是那么的单纯,因此他们最容易接受极端主义。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可能复杂一点儿,或者说油滑一点儿,不能甘心情愿地去做自杀**。那么,我要说:宁肯如此。
家
最长久的思维总是有最简单的起点。人类历史一直被三种逻辑控制着:马蹄的逻辑、船帆的逻辑和锄头的逻辑。
当然还会有别的逻辑,但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
中华文明的非侵略本性,不仅仅表现在农耕心理不愿意离开土地和家庭,而且也表现在对远方的土地不感兴趣,即使是再雄才大略的中国皇帝像秦始皇、汉武帝他们,也从未对中亚、西亚的土地产生过任何好奇。汉武帝为了获得他最喜爱的汗血马曾经发起过一些距离较远的征讨,但也只是为了马,拿到了马也就回来了。
中国古代有一些被广为传颂的英雄人物,可以暂时的把家庭搁置在一边,比如叫做“三过家门而不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但细细品味一下,在这些话里边,“家”这个字,仍然是一个最高坐标,这些人只是把这个最高坐标暂时放松,就成了震天撼地的历史人物。甚至直到现代,人们为了某次战争,也会把“保家”放在“卫国”前面。
压根儿没想过
我想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明代的中国航海家郑和了,他的远航与哥伦布他们的“发现新大陆”是发生在同一个世纪,而且郑和还比他们早了几十年。对于朝廷派郑和远航的动机,历史学家有不少争论,但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就是谁也不会说朝廷对“西洋各国”产生了领土要求。事实证明,从皇帝到郑和,甚至于直到航海队里的一切成员,从来没有人想把人家的任何一块土地并入到明朝的版图。沿途也发生过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但那只是因为当地有人骚扰或者抢掠了船队。大家想,这种以强大的船队登上了别国土地而又毫无领土幻想的集体心理,这个可不是出于自我克制,而是出自于一种本能。用我们今天的口语来说,也就是压根儿没想过。这种压根儿没想过的本能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沉淀成了本能。你看,在同一个世纪里边的同样的航海,哥伦布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我们再也不要拿着哥伦布他们的例子来责备我们自己的前辈了。他们很本分地回家了,没有在外面打家劫舍,更没有带回来血迹斑斑的地图。
逻辑
前几个月在电视上看到美国国防部长在抨击中国:“现在谁也没有威胁你们,你们为什么还在增加国防经费?”这话即使从最善良的角度来讲,也像是四百多年前利玛窦身边的传教士发出的询问。利玛窦说,他们按照自己西方世界的逻辑在猜测中国。但是,这位国防部长显然并不是传教士,他恰恰掌握着足以威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武器和架势,包括那次电视讲话的架势。这神情就让我想到了旧时代的那个乡间豪绅,财大气粗地质问刚刚在村边修建住宅的农户:“这里有谁会来抢你?为什么要砌砖墙?”
这又让我想起了一件我写到过的往事。前几年吧,在巴黎,两位去开会的上海工程师向一位当地的老太太问路。老太太把他们当作了去抢他们工作的中国人了,指了路之后又把他们带到身后的一张世界地图前,不礼貌地质问:“这是我们巴黎,那是你们中国,我们自己人找工作也不容易,你们那么远的路干什么来了!”
其中一位上海工程师立即接过话头,说:“我们是贵国邀请来开会的,明天就要回去,回到上海以前的法租界。一百多年前,巴黎离上海也那么远,交通更没有现在方便,你们跑到上海干什么去了!”
这个回答很幽默,但是说实话,我刚刚听到的时候立即流出了眼泪。一种太对得起别人的千年文明,我说,一种太对得起别人的千年文明,反而一直被别人质问,质问者居然是忘记了自己曾干过了些什么。
永恒的情景
我记得上世纪前期有一位法国的学者说过,到十九世纪末,艺术作品有可能写的情节模式,已经被小说和戏剧都写完了,后来大家自以为是创作了新的故事,其实一定是重复了很久之前一位作家的某一部作品,只不过把事件和角色的外部形态换了一下,而且那个作者不知道而已。而另一位法国作家还把古往今来人们永远在用的故事套路归纳为“二十六种永恒的情景”。我当时在教学生创作的时候很重视这种归纳,但仔细一分析,这“二十六种永恒情景”后面还有大量重复和交叉,不重复的只有十几种。所以,我设想今后电脑也能参与创作,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把基本情节模式进行快速的排列组合,然后输入你所需要的现代信息,然后把自己的情感、灵魂、血肉都能够灌注进去的话,那么有可能出现我们所说的不错的作品。
其实,艺术创作是这样,管理秩序也是这样,有些基本的模式。就从我在前面介绍的中国两千几百年前的那些思想家所提供的社会秩序的模式而言,我们后代到底多少人能够超越?很多现代企业家以为自己在管理上有大量的发明创造,其实这个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读书读得太少。
……
我们一定误会了中华文明的早期精神大师,把他们看成是坐在云端上替天立言的圣人。其实他们是颠簸在泥途牛车上的社会观察家,天天苦恼着应该如何打理纷乱的世间。
治水
以前我读到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论述,他认为中国的大一统思维与治水有关。中国以农业立国,离不开大河的灌溉,而横穿中国腹地的两条大河长江、黄河决定了中国的生态命运,需要不断地治理。但是,长江、黄河贯穿很大的地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单独治理,如果任何一个地方不负责任的话,就会影响其他地方。因此,在马克斯·韦伯看起来,中国的大一统思维来自于治理大河的需要,他甚至于说,连统治的“治”字,也来自于治水。不懂中文的他不知道从哪位传教士那里知道了这个秘密的。他的这个说法,使我非常佩服,觉得他很有道理。但是,我又觉得作为一个没有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确实不明白中国的某一个重大的精神未必来自于实用,而更多地来自于人文传统。治水是一种实际需要,再加上强大的人文传统,两相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中国统一的话语。
故乡
……“大一统”是着眼于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底线。但是毫无疑问,这也会遇到国土的统一。秦王朝既然废除了分封制和世袭制,那就为国土的统一建立了一种制度保证。后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分裂的局面,比如汉以后的三国鼎立,西晋以后的南北朝,唐以后的藩镇割据,但总的说来,各方强人都在为统一全国做准备。各方强人都不会公然地否定大一统的共同价值底线,只会指责对方违背了这种底线,因此整个趋势还是走向统一。比如,三国鼎立时候的魏、蜀、吴,各自都整合了地方的割据势力,后来本身又被整合,这就是一再重复的文化模式。
至于周边一些已经发展成小邦国的民族,中华文明从来不以种族的区别,而以文化的归属来决定分合。因此,也是文化使中国解决了其他文明古国都解决不好的民族小邦国的问题。史书上所谓的“夷狄”后来也慢慢地变成了“诸夏”,还实现了“胡汉一家”。总之,在中华文明的整合史上,终于使“天下归心”的是文化……
与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国,很多强大的精神价值不存在实际的载体。前不久,我和我的朋友余光中先生到一个地方去玩儿的时候,当地朋友就像其他地方一样,都希望写过《乡愁》的余光中先生把故乡的概念落实在当地。但余光中先生回答是这样的:我的故乡是文化。
什么都是
诸葛亮留给历史的主要印象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地“治国平天下”的儒生君子,一篇《出师表》道尽了他的这种人格特征。但是,他从《隆中对》开始的征战生涯,更明确地验证了他是一位深通权术、兵法的顶级谋士。不仅儒、法、兵三家,而且似乎先秦诸子的各家在他身上都有体现。走出隆中之前,他却按照老庄的道家思维在隐居。但是,他的老庄也不是纯粹的,否则刘备来请教他,他怎么可能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套天下的军事现状?当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他要搜集到这些情报不知要花费多少心力。由此可知,他隐居的时候并不是纯粹的道家,他谋划的时候并不是纯粹的法家,他打仗的时候不并是纯粹的兵家,他尽忠的时候也不是纯粹的儒家,但他又什么都是。正是这种充满弹性的全方位人格,使中华文化在各个领域保持着既不同又统一的逻辑和秩序。
罗素的话
大概是一九二一年初夏吧,一天,罗素在一批中国友人的陪同下坐轿子登山。那天天气突然很热,山道呢,又非常崎岖,因此轿夫们都非常辛苦。终于爬到了最高峰,大家休息一会儿,这些轿夫坐成一排,取出烟管乐滋滋地抽着,开始互相取笑,好像世间万事在他们的笑声当中了无牵挂了。罗素看到这个景象就想,这个事情如果换了别的国家,那些轿夫一定会抱怨酷暑难当,要求增加小费,而像自己这样比较高层次的欧洲人呢,到了山上也不会了无牵挂,而一定会担心我们下山以后的交通工具等等。但中国人一有空闲就取笑逗乐,那实在是另一种文明。由此联想开去,罗素发现,同样介绍一个居住的地方,欧洲人会首先告诉你这个地方的交通设施,那非常实用了,而中国人如果讲交通设施的话,多半会讲不明白,他们更会告诉你的是最不实用的内容,比如说古代某个诗人隐居在这里……
罗素当然不会简单地裁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但却十分公平地让人家感觉到:西方文明并不是唯一的坐标。
对于我前面反复论述的中华文明的非侵略的本性,大家还记得吗?罗素说得比我有趣得多了。他说,白种人有强烈的支配别人的欲望,中国人却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正是这一美德,使中国在国际上显得虚弱。其实,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自豪得不屑于打仗,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如果中国愿意,它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这是罗素的话,请注意,这些话不是在说现在,也不是在说抗战胜利之后,而是在说中国被列强宰割、处处民不聊生的一九二二年!
钥匙
任何文明的洞窟,不管藏有多少宝物,冠有多少美名,总有一个开启它的小小钥匙孔。中华文明的钥匙孔,叫“君子”。 历史的脸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