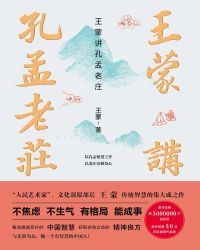一、“齐物”与“思辨”
庄子的逍遥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庄子·内篇·逍遥游》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庄子·内篇·逍遥游》
庄子是公元前369年诞生的,是个非常独特的人,写的文章想象力丰富,人们都说它是汪洋恣肆,就像大水冲过来一样。我喜欢用庄子自己的两个词儿来形容——“心如涌泉,意如飘风”,本来这话是形容一个强盗的,说强盗办起事来思维活跃得像喷泉一样,思想迅猛得像大风一样,刮来刮去,太独特了。
庄子开篇提出来的命题叫作“逍遥游”。把人生说成梦的是有的,把人生说成戏的也是有的。但是庄子希望的人生是什么?是逍遥之游。逍遥又是什么?中国古代似乎还没有自由这个观念,庄子给了我们一个逍遥的观念,逍遥就是中国古代的圣贤心目中的自由,不受外物的限制,不受束缚,自得其乐,想到哪儿做到哪儿,全凭自己的爱好,使自己愉快,使自己自由,使自己发展,使自己满足。
开篇就挺奇特的,庄子说在北冥,北方的一个大池子里,有一条大鱼,这条大鱼的身躯以千里来计算。这条大鱼变成鸟,叫作大鹏。这只大鹏的翅膀也有几千里。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解测量,地球的直径也不过是一万多公里,这条大鱼、这只大鸟,了不得。
毛主席的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就是从庄子的鲲鹏这个故事说起,“鲲鹏展翅”,鲲是鱼的名字,鹏是鸟的名字,变成鸟以后,翅膀一展,“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扶摇是高天上的风,高天就是高空、太空,把整个太空都掀动了,羊角是指上空空气的流动。毛主席是把鲲鹏作为一个正面的形象,作为一个有志者的大的精神、大的气魄。
庄子讲完大鱼、大鸟以后,紧接着写斑鸠和蝉对大鱼、大鸟的讽刺与嘲笑。斑鸠和蝉觉得很奇怪,鱼和鸟长那么大干吗?飞那么高干吗?飞那么远干吗?像它们想上哪个树枝就上哪个树枝,如果飞不上去了,就在地上跳跳,蹦跶蹦跶也挺好。
庄子说到这里略微有点损,意思就是小鸟理解不了大鸟,蝉也理解不了大鱼,这叫小大之辩。小和大之间,心情不一样,看法不一样,要做到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很困难。
《逍遥游》这一篇的最后,有点想不到,这个惠子老是充当庄子的对立面,喜欢跟庄子抬杠。他听了庄子这些伟大的、宏伟的、超乎正常人想象力的话以后,就跟庄子说,他见过一棵大树,大家都管这棵树叫樗,就是大臭椿,“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那个树干,不中绳墨,就是没有办法用木匠工具量度,看不出这棵树能有什么用途。“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小一点的树枝,曲折拐弯,乱七八糟,总而言之就是俩字:没用。这么大的一棵大树,一点用都没有。这棵大树就在大路边上长着,可是“匠者不顾”。木匠从那儿过连看都不看,因为看也没用,什么用处都没有,劈了当柴火也不好用,既不是栋梁之材,也不能打家具。惠子的意思就是说庄子能说是能说,能想是能想,但是没用。
庄子回答,“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有这么一棵大树,可是没有用,为什么非得打家具呢?为什么非得要拿它造房屋?“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把它放在一个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广莫之野”,就是又广阔又荒凉的野地。“彷徨乎无为其侧”,围着这棵树可以走来走去,自己也犹犹豫豫,不知道要干什么。“逍遥乎寝卧其下”,可以逍遥自在地在树底下铺上东西,躺在那儿睡一觉不就完了吗?人为什么非得要干什么事?人为什么要自己管住自己?人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定这样的或者那样的任务?“不夭斤斧”,这样的树不会被哪个人拿着什么工具砍掉,过早地结束它的存在。这么一棵没用的树,没有人照顾的树,没有人有兴趣的树,没有人注意的树,这才真正叫作逍遥。
“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因为它没有用,就没有人害它,没有人用它,没有人锯它,这棵树想怎么长就怎么长,在这睡一觉,是多么逍遥自在。
庄子把这个无用说得非常美好,就要做这棵无用之树,就喜爱这棵无用之树,就要在这棵无用之树下睡一觉,来享受逍遥,享受自在,享受没有压力、不受管束的生活。这个层面上看庄子很厉害,很会说,而且想得也很高尚,和别人不一样,他要的是逍遥,在这棵树底下睡一觉,就能感觉到的逍遥。
让我们想一想,庄子的逍遥是从鲲鹏开始的,是要飞九万里,翅膀就好像是一大块云彩,遮住了半个天空。这么伟大的志向,这么巨大的形体,这么高的期许,最后落了一个什么结果?找了一棵大臭椿树往那儿一靠,呼呼睡一觉,这究竟是鲲鹏的大智还是无奈?
看到鲲鹏的时候,非常佩服,非常惊讶,觉得庄子真牛!可是看到最后弄了一棵“无何有之乡”的大椿树,“广莫之野”的大椿树,而且在树边有一个人,彷徨地走来走去,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怎么逍遥?就是逍遥地睡一觉。
是不是又感觉到所谓的逍遥,既是伟大又是窝囊?怎么这么伟大的鲲鹏过了几分钟,就变成只能够找个树底下睡个觉的窝囊废了?这是牛还是怂?不同的人从庄子的故事中,必然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也许是喜悦,也许是叹息和遗憾。
齐物论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庄子·内篇·齐物论》
纪渻子为王养斗鸡。
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憍而恃气。”
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
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
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庄子·外篇·达生》
现在谈庄子的齐物论,槁木死灰与呆若木鸡。齐物论是庄子思想的核心,他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思考,进行了许多既有相当深度,又非常片面的、钻牛角尖的一些论述,所以这些论述非常奇特。作为文章来说几乎是天下第一;作为认识来说,又让人很难全部接受。
庄子讲一个民人叫南郭子綦,颜成子游去看望南郭子綦,看到南郭子綦简直像个死人,对什么事都没有反应。然后跟他说,你怎么看着就像一块干枯了的木头,又像一堆烧完了以后剩下的死灰,一点朝气都没有了,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人?
南郭子綦笑了,说:你不知道吗?“吾丧我”,我已经把那个小我忘掉了,那个小我在我身上已经不存在了。我脑子里只有大道了,只有世界了,只有天地了,我脑子里再没有那些对个人的小打小闹、小恩小惠、小利小害的斤斤计较了,所以就成了这个样。
这个描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令人吃惊。因为槁木死灰作为一个成语,表达的是一个活死人的精神状态,是一个活死人的面貌。就是一个人对什么事都没兴趣,没有追求,也没有厌恶。几千年来都用这话形容绝望、毁灭,形容差不多是死的一种状态。比如《红楼梦》里描写李纨,因为丈夫早亡,青春守寡,所以描写她感情的事情、和男女有关的事情,都是槁木死灰。这是最高级的道德。守寡的人见了异性,她本人的反应必须是零,必须是“槁木死灰”,所以这里用了这么一个词儿。
庄子在这儿所写的不是一个快要灭亡了的精神状态,不是一个消极得不得了的精神状态,而恰恰是得了大道的、修养到了巅峰的一种状态。这里为什么把“槁木死灰”形容成得道?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庄子认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太坏了,到处是阴谋诡计、争权夺利、血腥屠杀,到处是危险的陷阱。从外边得到的,都是算计、敌意、欺骗、阴谋,所以只有用槁木死灰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对待外部环境,才能够让自己平安、自己干净。
提倡槁木死灰,实际上是对当时环境的否定,一种绝望的表现。成了槁木死灰,起码还能踏踏实实地活两天。
庄子还讲了一个故事,后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成语,就是呆若木鸡。呆若木鸡现在也常用,形容一个人又傻又迟钝,呆得像木头鸡。木头鸡的特点是什么?有鸡的形状,有鸡的身体,但是没有鸡的生命,没有鸡的灵魂,没有鸡的任何功能。
“呆若木鸡”的故事是:纪渻子给周宣王养斗鸡,这里的“养”是指调教训练,看来那个时候就有斗鸡这种娱乐活动。过了十天,周宣王问鸡调教好了吗?纪渻子说没有,这只鸡现在“虚憍而恃气”,很浮躁,很自大,还好生气,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本领,全是虚的,这样的鸡不能让它去参加斗鸡的竞争。
又过了十天,第二十天了,周宣王又问。纪渻子回答说还是不行,现在有什么响动,有什么声音,有什么光影,这只鸡还动不动都有反应,一有声音它警惕,一有光影它就摆出一副好斗的样子,这样的鸡是幼稚的鸡,看着很敏捷,实际上并不灵,打不赢仗的。
又过了十天,第三十天了。纪渻子回答说还没有成,现在这只鸡看什么东西瞪着眼,急得不行,而且气很盛,趾高气扬,自以为很了不起,这样的鸡也是不中用的。
又过了十天,已经过了四十天了,周宣王再问。纪渻子说行了,“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这鸡已经对外界没有反应了,没有变化了。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已经非常淡定了,看着它就跟只木头鸡一样,但是是一只会打鸣的木头鸡。
“其德全矣”,这个时候它像木头鸡一样,功能、品智、品德已经全面完成了,已经是一只完整的鸡了,不会因为一时一地的声、影、晃动,或者是因为周围有别的鸡走过而分心分神,其他的外物与挑战对于它来说就跟没有一样。这样的鸡把别的鸡都吓坏了,因为没见过一只鸡居然能够跟木头鸡一样,这神鸡,什么都深藏不露。
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叫静水流深,水安静,证明它是深水,且深不可测。水往下流,越来越深,把握不住底下有多深。相反的,如果水又冒泡,又起浪头,那没有多深,因为浅才起大浪。深的地方的水流,在底下,在暗处,是看不见的,此所谓静水流深。
呆若木鸡也是这样的,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越是表面上看着非常了不起的那种人,越是不堪一击,吹牛行、吓唬人行、表演行,实战是不行的。呆若木鸡,这是庄子所向往的一种境界,但是后人只从字面上看,认为说的是傻、是迟钝,我们的理解和庄子恰恰相反了。
让我们自问一下,浮躁、虚骄,动不动就抖机灵,动不动就上火,就冒气、冒泡,这种精神状态,这种肤浅,我们身上有没有?
极致的精神定力
故曰,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焉,休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惔矣。平易恬惔,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
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去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罢。虚无恬淡,乃合天德。
故曰,悲乐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一而不变,静之至也;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不与物交,惔之至也;无所于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
——《庄子·外篇·刻意》
前面我已经讲到,庄子以槁木死灰、呆若木鸡来形容一个人的精神定力,形容一只斗鸡的精神定力。
庄子还有一套理论,他说“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就是说安适、淡漠、寂寥、虚无、无为,即第一不闹腾,第二不打盹儿,第三不咋呼,第四不急躁,这个才是天地最正常的一种平衡状态。这才是道德的本质,道德的本质不是让人苦苦修炼,而是让人安安静静、踏踏实实回到人的最原生的状态。所以说人如果能够休止于此,如果不妄作言行,不乱说乱动,就能够很平易、很日常、很自然地生活。
而如果一个人能做到平易自然,也就能够做到恬淡虚静,就能够达到一种富有精神定力的状态,而且不用费劲,压根就是安定的,外界对他的影响很小很小,差不多就是零。又平易自然,又恬淡虚静,根本不受外界的影响,那么忧愁祸患也就无法侵入了,邪气不会上身,没有亏损,所有的精神状态、精神品质、精神功能都很齐全。
圣人的出生是与天同行,是和天一块儿生下来的;圣人的死是与物聚化,外界变化了,他也就变化了,外界的一切都是变化的。静止的时候是阴,动起来的时候是阳。总而言之,他本身体现的是天地万物,不为自己操心,也不为自己发愁。
“悲乐者,德之邪也”,有的事感到悲哀,有的事感到快乐,这是人的精神走了歪门邪道的表现。“喜怒者,道之过也”,有欢喜的时候,还有发怒的时候,说明人掌握不住大道。“好恶者,德之失也”,对一些东西有好感,对一些东西有厌恶之感,这个也是失去了自己品德的表现。
“心不忧乐,德之至也”,做到既不忧愁也不快乐,就达到了道德的极致了。“一而不变,静之至也”,从早到晚,从今天到明天,从这个月到下个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该什么样什么样,是静之至也,达到了安静的极致。
另外庄子还讲,一个人在净水里才能看清楚自己的影像,因此水静也是智慧和观察的前提。“无所于忤,虚之至也”,什么事都不戗着来,不背叛,不顶撞任何事情,就做到真正的谦虚了。“不与物交,惔之至也”,不与外界的事情发生太多的互动,又做到淡了,淡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品质。“无所于逆,粹之至也”,跟谁都不发生矛盾,就做到纯粹了。这些说法比“槁木死灰”“呆若木鸡”好听,甚至还有点高大上。
庄子的这一套思想、这一套鼓吹,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不能不想到,庄子在全书的一开始所讲的那个鲲和鹏的故事,代表他的精神状态,代表他的心胸,他的世界不斤斤计较,不是眼皮子底下的鼠目寸光,而是有几千里之宽、几千里之高、几千里之大,他的精神已经和道接轨了,已经和无穷大接轨了,已经和永恒接轨了。他内心已经雄伟、宏伟到这种程度了,社会上的那些小打小闹、祸福得失、成败顺逆,对他来说近于零。
微积分告诉我们,当用无穷大做分母的时候,上边的这个N,无穷大分之N,差不多就是零了。庄子的这种定力,这种槁木死灰状,这种呆若木鸡态,不是由于灰心丧气,不是自戕,不是自己要把自己灭掉。要灭掉的话,就不用写这么漂亮的书了,也不用发表这些理论了,上吊也行,跳井也行。
正是他内心雄伟、智慧达到了极致,反过来对自己的日常,对自己碰到的各项事物、各个人、各种条件、各种状态,他看得冷了,热极了就冷了,冷极了就热了。在庄子的理论、庄子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特异的精神形态,他是想干什么?他把行为否定了,把感情否定了,把欲望否定了,把期待否定了,把什么都否定了。
他肯定的是休息,是安静,是空虚,是虚无,是孤独,他否定的是人气,是奔走、追求。就是说在庄子心目当中,当一个人的精神追求到了极端的高度、极致的广度、极大的格局、极清醒的认知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这些实际的事,名誉、地位,乃至于去当说客,去辅佐哪位君王去治国,都看不上了。
不但看不上了,也看透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很多的奔走,很多的智谋,是自取灭亡。有时候,庄子把自己说成了槁木死灰、无用,而且只能够躺在大臭椿树底下睡觉,把自个儿糟践没了。但是他背后又有一种骄傲,又有一种了不起、看透一切的感觉。
庄子太特殊了,庄子太厉害了,同时庄子的这些说法又给我们一个启发,即什么东西都不能过分,什么东西都不能到头,什么东西都不能到顶。如果到了顶、到了头、到了无穷大,反倒把自己整个的生活全否定了。让我们自问,在对待外界的各种干扰时,我们怎么样才能恰当地把握?既不斤斤计较,又不能成为木头鸡。
相对的真理
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庄子·内篇·齐物论》
庄子有一句名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我们往往把这句话理解成没有是非的感觉,没有是非的分辨。反正这么说也是一种谁是谁非,那么说也是谁是谁非,或者干脆把它解释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公婆俩人吵起来了,各说各的理。
但是庄子的思想要深刻得多,要彻底得多,彻底就是追根究底,追得人一口气憋在那儿上不来,这才叫哲学。庄子的哲学不仅仅是讨论谁是谁非,是否靠得住,而且讨论你和我、彼和此、这个和那个之间的甄别,一些妄议、一个争论到底有多少根据。
春秋战国时,学术观点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争得非常热闹。虽然我们现在看那是一个学术争鸣的黄金时代,但是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当时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夸张、各种各样的兜售、各种各样的狗皮膏药,江湖术士都争得一塌糊涂。当时的政治权力、军事斗争,以及天下的不统一,处在一种极端混乱的状态,国无宁日,民不聊生。所以庄子认为一般的俗人所做的是非之争、道理之争、意见之争、政见之争,根本不值得一提。
庄子有一些有趣的见解。第一,言语并不是清晰的和肯定的。因为说出来的话,自己都不觉得准确、有把握、有根据。他甚至说言语就像鸟叫一样,自己出点怪声,到底什么含义,有几个人对自己所说的话能够清楚地加以把握、加以解释,而且经过认真地推敲?真那么推敲起来,人还怎么说话?这一条就够绝的了。
第二,所有的人不都是有一个成见的吗?在没有讨论的时候已经有见解了,在没有调查研究的时候已经有见解了。那个时候不叫成见,叫诚心。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诚心,都以自己的诚心作为自己的老师,作为自己的依据。而把这个没有根据的见解当成了见解,这样的话不就更乱了吗?这样争来争去,也说不清自己到底要坚持的是什么,也说不清别人坚持的是什么,尤其说不清别人到底是要干什么。可是已经势不两立了,已经争上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个道理更深奥了。他说“道隐于小成”,真正的道理、真正的大道,最根本的道,都隐藏在那些小小的成功、小小的世界里了。找不着真正的大道,一般的人,包括君王及其臣子,这些掌权的人,他们知道多少天道,知道多少大道,知道多少老子所说的大且流动、恒久且来回的否定的道呢?一个君王所知道的那些,也许是跟其他邦国打交道的时候得到了一点便宜,也可能是请来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做他的大臣,那里能有多少大道?
“言隐于荣华”,这个“言”,就是语言。天知道隐藏在修辞里的、隐藏在那些华丽的词句里的、隐藏在引人注意的抑扬顿挫的语调里的话是什么。说半天,首先感动、吸引人的是言语中那些表面的东西,而一个人真正要说的是什么,听一遍就能明白了吗?看了一个人的文章就明白了吗?不明白,所以“道”不明白,“言”也不明白。而且庄子不避讳地指出儒墨之争,一边是孔孟,一边是墨家,争得还挺厉害,但是他们争来争去,他们互相了解对方的主张吗?
庄子认为真正的事实、真正的本质、真正的道理、真正应该说明的,或者应该牢记的那些语言都是隐藏着的。而说出来的往往是表面的,是意气用事的事,是印象式的、被成见所左右的靠不住的东西。
第四点,庄子喜欢分析,说“彼出于是”,“是”在这里当“此”讲,彼就是另一面,英语里也有这种说法,一个是以自己为主体,剩下的就是他者,就是others,就是别人。
别人的、他人的、那边的,和自己这边的相互对照是离不开的。对对方来说,“彼”就成了“此”,成了自我,成了这边,而“此”就变成了对方的那边了,成了“彼”,就已经不是这边了。可是人又都是有立场的,都站在自己这边,往往是拿自己当标尺来衡量别人,符合自己的愿望、符合自己的标尺,就认为是正确的;不符合自己的、符合人家的标尺就认为是错误的。
但实际上彼离不开此,此离不开彼,没有此(是)就没有彼;没有了那边,没有了他者,也就没有了这边,没有了自我。不仅彼和是(彼和此)是这么一个关系,生和死、是与非也是这么一个关系。“方生方死”,生下来了,也就开始死了。没有生,哪来的死;生的最后都是死,可能是五十年后死去,也可能是七十年后或者更晚死去。但是一个人死的过程是从他生下来开始的,方生就是方死。
方是就是方非,由于某种原因自己认同了某种见解,这种认同的原因,有可能使自己在将来的某个时期、某个时候否定对方的见解,甚至是己方的某种见解。
这一点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上最为明显,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承认他国呢?为什么要认同他国呢?为什么要和一个国家结盟呢?为什么强调跟一个国家的友谊呢?肯定有原因,这个原因离不开一个国家的利益和已经有的成见。那么由于这种利益,由于成见,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可能否定了。
所以庄子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设想,就是不要分彼和此,不要分生和死,不要分是和非。这样就处在道枢,处在环中,就好比在一个圆形的中心里,就变成了圆心。往哪儿走都是道,也分得清是和非、此和彼,成了大道的枢纽。
让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形,还没有考虑成熟,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什么话,可是就跟人家争上了,甚至就跟人家对立上了,有没有这种情况?
道通为一
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因是已!
——《庄子·内篇·齐物论》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庄子·杂篇·寓言》
庄子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大千世界之中寻找事物的共性,寻找事物的同一性,从而认为人们对事物的分析、区别,各种不同的评价未必有什么道理。
庄子有一句名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就是说我的出生是跟天地在一块儿的,没有天和地,没有这个大千世界,怎么可能有我呢?反过来没有了我,我又何必再去讨论这个天地,正因为我来过,我曾经感受过天地,天地也离不开我的感知。天地和我互相谁也离不开谁,我们是不可分离的关系。
万物与我为一,世界上那么多东西,那么多属性,但是它们作为天地之间的、作为世界上的、作为大道的产物,它们没有什么区别,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它们对于各自来说都是合适的,都是大道的表现。因此我们也用不着费劲把这个挑出来,把那个导出去,把万物弄得非常麻烦,自讨苦吃。
庄子说任何的事物“然于然”,它是这个样,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样;“不然于不然”,它不是这个样,就应该不是这个样;“可于可”,我们可以认同它的这种状况,就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可于不可”,我们不认同它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这样的,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特质和存在的依据,用不着乱做评论,也用不着说三道四。
庄子还说正因为这样,如果失去对比的对象,孤立地看一个事物,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成大的或小的、长的或短的。所以相传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也可以认为他是夭折的。而一个夭折的孩子,也可以认为他是长寿的,因为这个孩子本来被判定活不了,但他活了十年才死,那十年对他来说也是长寿,十年可以做很多事,也可以有很多状况发生。彭祖也是一样,他活了八百多岁,最后死了,他也许能活一万岁,和一万岁相比,他的八百岁不就是夭折了吗?和一百岁相比,他的八百岁不就是长寿了吗?
长寿和夭折本是比较的产物,不比较哪来的长寿和夭折。长寿比平均寿命长,夭折比平均寿命短,但是夭折比更夭折又长,长寿比更长寿又短,所以各有各的长寿,各有各的夭折。
漂亮的人、丑陋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状况,作为道的体现,是一样的,本来就是一个同样的东西,所以说道通为一。庄子讲万物都是通的,就是人要能看得明白,表面上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属性,整个天地就是一,人跟天地合起来就是一,万物和天地合起来就是一。
但是人又要谈论天地,又要认识天地,所以天地本来是一,有了关于天地的概念,有了关于天地的语言及这个语言的表述,就出来二了。这个意思还包含着一个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分离。本来主观世界是离不开客观世界的,没有天地万物就没有任何一个主体的存在,主体是世界的一部分,主体不是世界之外的。
当主体来讨论世界、认识世界的时候,主体就变成二;主体说的那些话,那些对于世界的印象评价、对于万物的评价,就变成二。然后庄子说一加二就又变成三。这个一,有各式各样的一,我们说天地,这是一;我们说天地和万物结合起来,这也是一;我们说庄子,谈论天地,谈论万物,庄子、天地、万物三者结合起来,这也是一。
这一也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概念,对于一的评论、讨论就是在客观世界、客观的天地之外,又出来一个观察天地、掌握天地、讨论天地的主观的精神世界,这就是二。然而当讨论到天地这样一个客观世界的时候,又讨论到观察天地的精神世界。就是说在天地和精神世界之外,又出来了一个主观的世界。这个主观的世界不仅仅对于天地是精神世界,对于认识天地、讨论天地的精神世界,也是一个精神世界。这样又出来一个观察精神世界的精神世界。
反过来用这种方法,一二三四五六以至于无限,好比拿两个镜子互相照。甲镜子照成了乙镜子,这时候我们一看这是两面镜子。甲镜子照上了乙镜子以后,乙镜子又把甲镜子和甲镜子所反射的乙镜子的形象,照在自己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是两面镜子。乙镜子本身是一面镜子,甲镜子是一面镜子,甲镜子里的乙镜子的映像,又是一面镜子,三面镜子。这三面镜子又传到甲镜子里,四面镜子、五面镜子……无限多的镜子,就成了一种长廊效应,镜子里面又出来了无限的镜子,因为它们能够互相比照。
庄子是比较早研究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主体和客体互相一作用又没完了。有一种静坐的方法,就是设想自己的心里开了一朵荷花,自己坐在设想的这朵荷花里,然后荷花里的这个想象的自己,心里又开了一朵荷花,这么开下去,还有穷尽吗?静坐的人这么一想,舒舒服服就融化在这里了,这是一种静坐的方法,跟庄子分析的道理差不多。
庄子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分析来分析去,实际上它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了主体和客体的区别,越分析就越复杂多样,这只是一个角度。庄子还编了一个故事,讲这种复杂其实来回都是一个样,就是有名的朝三暮四的故事。
一个养猴的人告诉猴说,早晨吃三颗果子,下午吃四颗果子,猴不干。于是养猴的人说,早晨吃四颗果子,下午吃三颗,猴欢呼。庄子讲这个故事,是说世界就那么回事,不是早晨三个下午四个,就是早晨四个下午三个,最后还是七个。世界就是这么七颗果实,怎么分都是一样。
我们现在认为朝三暮四,是说一个人的坏,说一个人的缺点。早晨这样,下午那样,没有准,靠不住,用庄子的眼光看这恰恰反映我们的智商跟猴子是一样的,我们没有比猴子更高明。如果我们比猴子更高明,就会觉得朝三暮四也可,朝四暮三也可,中间并无大的区别。
庄子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分析和说法,认为万事万物是齐物。把它看成一个、看成一种、看成一个平面就可以了,不必在那儿枉费心机地说这个、说那个,帮这个、骂那个。当然这也只是人生的角度之一,因为真正按这个思想分析下去,我把它看成是一,这个是符合道德的;我把它看成二,还是符合道的;看成三四五六七八,我看成一百八十万样,仍然是符合道的,又何必争论一不一的问题?争论一不就是不齐物了吗?
思想的极致与诡辩
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庄子·内篇·齐物论》
在前面的《齐物论》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人的思考、人的逻辑、人的分析,会达到一种极致,而达到极致以后,往往就又反过来否定人的思考。
庄子所说的“齐物”,就是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生命状态,其实用不着把它们区分得那么清楚,也没有什么可区分的。但是请想一想,庄子的齐物论及认为世界上的事情需要分辨、需要争个水落石出的区别论观点是不是一种区分?区别论强调世界上有是与非的区别、有长寿和短命的区别、有好与坏的区别、有美与丑的区别、有大与小的区别。
齐物论和区别论不就有区别了吗?区别论是一种强调区别、强调不同、强调相异的思想方法、思想角度,齐物论就是和这种思想区分,就是和这种人间的、正常的、普通的、浅薄的看法辩论,但是齐物论又否定辩论。庄子的一些说法简直是一般人想不到的,而且精彩到了极点,甚至会让人怀疑这是不是诡辩。比如齐物的极致是“齐生死”,庄子认为该生了就是生,该死了就是死,这些都是大道的表现,用不着认为生就多么好,死就多么不好。
他甚至举出一个例子:有一位叫丽姬的美丽女子被晋国人抓走了,刚抓走时整天哭泣,但是到了晋国,嫁给了晋王,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后,这个丽姬后悔了,后悔当初哭得没道理。庄子不可思议地说,人死跟丽姬被抢走一样,只不过没回来,自己没再说话。也许死了以后会觉得很幸福,也许死了以后会觉得比活在这个世界上还好,也许原来认为死是不好,那只不过是做梦而已。
对这个做梦的问题,庄子又做了一个新的分析:一个人在梦里哭了半天,第二天起来可能玩去了,打猎去了;在梦里快乐了半天,第二天可能碰到倒霉的事了。因此梦不能相信,梦是臆想的,人不能因为做了不好的梦而感到痛苦或焦躁,这些都是不必要的。
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认为自己做梦,这本身是不是又是一个梦?在实际中有了真的痛苦、真的快乐,一段真的离奇的经历,然后醒过来以后,做了一个更大的梦,这个梦里梦见的是真实的痛苦,然后认为自己从梦中醒过来了,这才是梦。从梦中醒过来了,认为头天夜间的那些心情、那些见闻都是梦。
如果再醒一次,醒过来才发现,醒过来才是梦,是梦中之梦。当然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认为醒过来是梦,本身就又是梦,谁能说得清楚?庄子说这就叫吊诡。一个人判断自己做梦,本身就含有一种危险,把这个判断如果推向极致,会怀疑自己的醒,是不是一种更高级的梦?那么还要进一步地醒,然后才能知道醒梦就是大梦。这个听起来吊诡,简直能把人给急死了。但逻辑上庄子讲得是有道理的。
庄子提出来对很多事情的分辨,何者为梦、何者为真,这种分辨是靠不住的,是没有把握的,并不是最后的结论。分辨什么东西都是真的,那么梦也是真的;分辨什么东西都是梦,那么梦也是假的。那么真才是最可靠的看法和判断,因为你没法判断。
庄子这个分析也有一绝,比如说我跟你争论,我胜了,我说得你理屈词穷,那真能证明我胜了吗?你真败了吗?真能证明我就是正确的、你就是谬误的吗?反过来说,争论的结果是你胜了,我败了,那么真能证明你就正确吗?真能证明我输了、我错了吗?
庄子提出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找谁来做证?找谁来判断?找谁来做结论当裁判呢?如果找一个同意你的见解的、是你那头的人,他来做证有什么意义?如果找来一个同意我的见解的、是我这头的人,找来又有什么意义?他不用做证,他就一定表示拥护我的见解,反对你的见解。他是帮助其中一人的,找他来做证,不是越证越糊涂了吗?
找一个对咱们俩的意见都不同意的人,他能做什么证?他做证的结果不就是一场混战吗?他裁判的结果、他判断的结果不是更招人骂吗?再找一个,对咱们俩的意见都同意的人,他觉得都有理,找他来做证,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庄子通过这件事说明,这个裁判对于当事人来说并没有意义。就算辩论结果我胜利了,你失败了,也没有意义,并不证明你不正确。对于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他们也没有资格来判断我们俩谁说得对,谁更对。
庄子提出一个观点——世界上有是有不是,就是世界上有肯定也有否定,否定也是一种肯定,为什么呢?就肯定了这个否定。世界上有然有不然,然是真实的、这样的、如此运动的。不然不是这样的。但同时又是然不然,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
反正它有一种存在,不存在也是一种存在方式,否定也是一种肯定,否定了否定,就是肯定。这个就跟负乘负,变成正一样。什么事仔细想起来都绕一个圈,想着想着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挖到了极点,又把自己原来所想的那个东西也否定了。
这个说法在现代世界、在西方世界也很有意思,人们管它叫数学悖论。比如说有一个著名的理发师悖论,理发师有一个规矩,就是谁要是给自己理过发,就绝对不再给他理发;没给自己理过发,就要好好地给人家理发。那么现在就碰到了一个问题,这个理发师给不给自己理发?如果给自己理发,他就违背了那个不给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的原则;如果不给自己理发,他又违背了愿意提供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服务的许诺,不就是没有辙了吗?
您说这究竟是诡辩还是揭露了人的语言、思维方式、逻辑本身就含有内在的矛盾?
超越与提升的三级跳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庄子·外篇·秋水》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
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无弃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
——《庄子·内篇·齐物论》
从庄子的一些论述、一些见解,我们可以看出来他非常与众不同,他思辨的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平地上议论问题时,他一下子跳到三丈高处,从高处来俯瞰我们论述的各种问题,居高临下。
这个高不是地位高,而是指智商高、见解高、心态高,因此超过了常人。同时正因为高,所以他不争,不在乎别人的说法,也不在别人面前显摆,只享受自己的思想,超越种种庸俗、烦躁、焦虑和无聊的争执。
《庄子》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惠子在梁国当宰相,庄子来看惠子。一到那儿就有传言,说庄子要夺惠子的宰相之位,可见庄子的智慧、辩才在当时很有名。惠子很紧张,就带着人到处搜捕庄子。这个说法不见得完全可靠,因为后来我们看到惠子成了庄子的一个最好的谈话对手,两个人的讨论,两个人的辩论,也正好显示了庄子的智慧。等到见到惠子以后,庄子就笑了,说从前有一种非常高尚的鸟,叫鹓。从南海一直飞到北海,那是很长的一段距离。鹓很清高,晚上休息,除了梧桐树,别的树一概不去。因为梧桐树树叶大,味道又香,木质又好,是一种高雅的树。俗话也说:没有梧桐树,也就没有凤凰来,凤凰只停在梧桐树上。
不是练实(竹子的果实),鹓不吃;不是醴泉(最甘甜、最清洁、最高级的矿泉水),它不喝。有一次它飞着飞着正好遇见一只猫头鹰,古人对猫头鹰看得比较低。猫头鹰捡到一只已经腐败了的老鼠,正准备吃这只老鼠,看见鹓从高空飞过,就非常紧张,怕它抢它的食物,于是这只猫头鹰向着鹓怪叫一声,要吓唬一下鹓。
然后庄子笑着问惠子,是不是也要拿梁国来吓唬自己?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是何等自信、何等自傲,何等看不起这些世俗的、争权夺利的、蝇营狗苟的俗人,所以《庄子》一开头就出了一个大鲲鱼、大鹏鸟,而且用大小之辨说明其思想境界跟常人没有任何相通之处,根本就不用搭理,这可以说是思想的一级跳。庄子很清高,常人最热爱的那些东西,他看着和死老鼠一样,这又是一级跳。干的那些事儿,他都没有兴趣,常人认为有用的东西,他都认为没有什么用处。他可以在一棵大臭椿树下四仰八叉地好好睡觉,这就是他的逍遥,这就是他的幸福。他并没有野心,也不想跟谁挑战,只想过自己的逍遥生活,这又是一级跳。
而在《齐物论》里,庄子又反过来认为,其实大和小的分辨都是相对的,是和非的分辨也是靠不住的。你说你是,我说我是,你说他非,我说你非,这个都不一定是靠得住的结论,没有人有资格做这个结论。所以他根本就不认为非得把事情争个清楚不可。
庄子在很多地方举过这样的例子:一只乌龟是在泥泞里乱爬乱走好,还是被请到一个神庙里被当作神仙供起来好?在供奉之前得先把乌龟杀死,洗干净,加上各种的装饰,然后大家都来给它磕头行礼。庄子宁愿在泥泞里乱爬。
庄子是能上又能下,高的话,可以当鲲鹏,可以一飞几千里。中间的话可以找棵大臭椿树,找个谁也看不见的地方好好睡一觉。再低下一点,当一只在泥泞里爬行的乌龟也可以。可以当鹓那样高雅的鸟,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也可以过很低级、很穷困、很不像样的生活。
我认为正确的,从你那边看就是错误的,很好,也可能就是错误的;你认为是正确的,我认为是错误的,那也很好,也可能就是错误的。真实的,也可能就是虚假的;虚假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真实的。我这边姑妄言之,我暂时这么说两句;你姑妄听之,你就把它当作空话、胡说八道的话,你从耳边过一下,也就行了。
这些东西强调多了,又让人产生一种疑惑,这不成阿Q了吗?说了半天,庄子追求的和阿Q追求的,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精神胜利。我没有能力,也没有毅力改变我的生活环境、改变我的社会环境、改变我的家国命运。但是我可以把坏事都想象成好事,把倒霉的事都想象成幸运的事,我可以把穷想象成富,你认为我穷,我认为我得到的够了,多了没用,多了自寻烦恼,因此我就是富的。你认为我级别低,我认为我最高,因为我有这学问,我的思维能力,你们连摸都摸不着,更够不上,这个有点阿Q的味道。
但是庄子不是阿Q,庄子是思索的大师,是思维的奇人,是精神的巨匠。他之所以什么事都能凑合,并不追求真正的改善,也不准备为改善做出什么贡献,是由于他太看不起这个世界了。庄子看不起这些俗人,他们认为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庄子都看不上。
他是三级跳,再接一个三级跳,越跳越高,以至于视万物如无物,视争论如犯傻,视一般人的计较和追求为做梦。正是他有这种高瞻远瞩,才把有些事情看虚了、看假了、看空了,也就满不在乎了,这也是中国古代的圣人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思想方法。 王蒙讲孔孟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