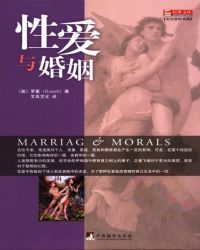第11章 卖淫
第11章
卖淫
既然我们把正派女性的道德看成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我们就必须有另一种制度去辅助婚姻制度,而且我们应当把这种制度视为婚姻制度的一部分,这就是卖淫制度。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那就是莱基所说的,娼妓是家庭神圣和妻子女儿清白的保障。这种情操是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它的表达方式也是陈旧的,但其事实却是无法否认的。道德家们都贬斥莱基,因为他的话引起了他们的怒气,而他们又说不出所以然,他们无法证明他所说的与事实有误。那些道德家指出(当然,他们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人们遵循他的说教,那就不会有娼妓了。但是道德家们很明白,人们不会听从他的谬论,至于人们听从了他的话之后的结果,那是无关紧要的。
在一个具有传统道德的社会中,许多男人难以找到称心如意的正派女人,或是由于其他原因,他们无法满足自己的性欲——这就是他们需要娼妓的必然因素。因此,社会就产生了另一种女人,来满足男人的生理需要。对于这种情形,社会虽然没有勇气承认,但又不敢完全置这个问题于不问,让人们得不到满足。娼妓是有她的有利一面的,她不但可以召之即来;而且极易掩饰自己,因为除了这门职业,她并没有别的生活;而且那些曾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仍可不失尊严地回到妻子身边或家庭和教会中去。尽管娼妓有她无可否认的贡献,尽管她保全了妻子和女儿的道德,以及教会会员的表面道德,但她仍是一个可怜的女人,为世人所不齿,被当成社会渣滓,而且不允许与普通人来往,除非她们在卖淫的时候。这种极不公平的状况,开始于基督教获胜之后,并且从此延续下来。娼妓真正的罪过,在于她把道德家职业的虚伪戳穿了。所以,她应当和那些被弗洛伊德学派的检查官所压制的思想一样,被流放到无意识中去。然而,在那里,她和其他流放者一样,发出一种自然的复仇之声。
大概是在午夜时分,
我听见街道上妓女的咒骂,
它引起新生婴儿的哭闹,
且使结婚的彩轿降临灾祸。
事实上,卖淫的起源是极崇高的,并非历来遭人蔑视,而且曾经无须遮掩。最初,娼妓是献身于神或女神的女祭司。她们以服务于路人的需要为一种礼拜的行为。那时,她们是受尊敬的,人们既需要她们又敬重她们。后来,基督教的教父们写了大量诬蔑的文字,去反对这一制度。他们说,这制度体现了异教礼拜的淫乱行为,起源于撒旦的骗人把戏。因此,圣殿遭到封闭,于是卖淫在各地逐渐成为一种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制度(其实,当时许多地方已经有了这制度)。当然,这并不是为了维护娼妓的利益,而是为了其主人的利益。目前极为盛行的暗娼,在过去是极少的,那时绝大多数娼妓都是在妓院、澡堂和其他不名誉的机构中。在印度,这种由宗教性卖淫转向商业性卖淫的过渡,至今尚未全部完成。《母性的印度》一书的作者凯瑟琳·梅奥将这种残存的宗教性卖淫作为她指责印度的理由之一。
除南美洲外,其他地方的娼妓的数量都显然是在慢慢地减少着。毫无疑问,一方面,由于妇女的谋生手段较之以前增多了;另一方面,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是根据于兴趣,而不是根据于商业动机,与男人发生性关系。然而,我并不认为卖淫制度可以从根本上完全废除。现以长期航行之后初登海岸的水手为例,他们不可能耐心去等待一位只是出于爱情而找上门来的女子。再以众多婚姻不幸和惧怕老婆的男人为例,这类男人离家时总要寻求舒适和自由的生活,而且希望这种生活尽可能没有心理上的责任。当然,把娼妓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愿望,也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反对卖淫的主要理由有三个:第一,对大众健康的危害;第二,对女人的心理危害;第三,对男人的心理危害。
对健康的危害位居这三种理由之首。很显然,花柳病的传播主要是因为娼妓的缘故。那种通过娼妓注册和国家检查来解决这一问题的企图,从纯粹医学上的观点来看,是不会有成效的,甚至容易产生一些弊端。因为这使得警察不但有管束娼妓的权力,有时甚至还有管束那些不打算以卖淫为职业,但无意中误入这法律定义的妇女的权力。其实,如果我们不把花柳病当成一种对于罪孽的应有的惩罚,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更有效地防治这种病。这种病经过预防完全可以归于灭绝,但我们却认为这种预防方法不应使一般人知道,理由是这种知识会助长卖淫。那些花柳病患者由于认为这类病是可耻的,羞于启齿,往往拖延治疗。现在,社会对于这类事情的态度较之以前无疑要好多了。如果社会的态度能够进一步改善,那么最终我们就能将花柳病控制在最低限度。但是,只要卖淫制度存在,它就会提供一种途径来传播比任何疾病都更危险的疾病,这是无可否认的。
现存的卖淫制度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所必需的。仅就感染疾病的危险而言,卖淫也是一桩危险的行当,就像在白铅工厂中工作一样。此外,卖淫生活是一种堕落的生活。这种生活极为懒散并且导致酗酒。对娼妓非常不利的情况是,她们普遍被人所轻视,甚至连她们的主顾恐怕也看不起她们。娼妓的生活是一种有悖本能的生活——与尼姑有悖本能的生活十分类似。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现存于各基督教国家的卖淫制度,是一种极不理想的制度。
在日本,情况却截然不同,在那里卖淫得到许可,并被视为一项值得尊敬的事业,而且有时她们成为娼妓甚至是因为父母劝导的缘故。卖淫是获得嫁妆的普遍通行的一种方法。按照一些权威人士的说法,日本人对于梅毒具有某种免疫力。因此,日本的娼妓并不像那些拥有严厉道德的地方的娼妓那样,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显而易见,如果卖淫制度必须存在,那么它应当按照日本的方式存在,而不是按照欧洲所盛行的那种方式存在。由此可见,如果一个国家的道德越是严厉,那么娼妓的生活越会堕落。
如果嫖娼成为一种习惯,那么很可能会对一个人的心理产生不良影响。这个人会形成这样一种习惯:性交无需得到快感。此外,如果他是重视一般道德准则的,他会对任何与他性交的女人产生一种蔑视感。这种思想对于婚姻的影响十分不利,因为他不是把婚姻和卖淫等同看待,就是把二者视为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甚至有些男人不能与他们喜爱和仰慕的女人进行有激情的性交。按照弗洛伊德派的说法,这就是所谓伊底帕斯式的变态心理。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人们在所喜爱和仰慕的女人与娼妓之间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的缘故。许多男人,特别是保守派男人,即使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也会过分敬重自己的妻子,致使她们在心理上成为处女,以至感受不到性的乐趣。如果一个男人在想像中把他的妻子和娼妓视为等同,那将会产生完全相反的不良影响。这会使他忘记,只有在双方都愿意时,才可以进行性交,而且在性交之前必须有一段性唤醒过程。他会因粗暴地对待他的妻子,以至使她产生一种难以消除的厌恶感。
如果我们使经济动机侵入性关系中,无论如何都是有害的。性关系应当成为相互间的共同享受,而只有完全根据于双方自发的冲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否则,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会消失。把亲昵的行为强加在另一个人身上,将会丧失真正的人生,而真正的道德只能源于真正的人生。对于一个感情敏感的人来说,性行为不会产生十分迷人的效果。如果性行为的产生仅仅出于肉体上的冲动,那么性行为很可能会导致自责,而且在这种自责中,一个人对于价值的判断将会变得十分混乱。当然,这不仅是对卖淫而言,婚姻也基本如此。婚姻是女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婚姻中女人所忍受的不情愿的性关系的总和,比在卖淫中恐怕要多得多。性关系中的道德如果摆脱了迷信,则主要由对他人的尊重构成,所以不能不顾他或她的欲望,仅仅为了个人的满足而利用他人。卖淫违背了这一原则,所以它是不值得提倡的,即使我们消除了花柳病的危险。
我认为,哈夫洛克·埃利斯赞成卖淫的论点是不正确的。虽然他对卖淫做了极有兴趣的研究。他首先提到的是早期文明中存在的秘密宗教仪式,人们借此可以把平时受到压制的蓬勃的冲动发泄出来。按照他的说法,卖淫起源于祭酒神的秘密宗教仪式,而且具有和以前秘密宗教仪式完全相同的目的。他说,许多男人由于传统婚姻和礼节的束缚而得不到充分的满足。于是他们偶尔踏入娼门以求发泄,因为娼妓不像其他事情那样为社会所反对。然而,从本质上说,这种论点和莱基的论点毫无二致,尽管其形式新颖一些。性生活空虚的女人也会像男人一样,产生哈夫洛克·埃利斯所说的那种冲动,所以,只要女人的性生活一旦解放,男人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无需寻找那些纯粹以金钱为目的的娼妓。这的确是从妇女的性解放中有望得到的好处之一。据我观察,如果妇女对于性的观念和感觉不为过去的忌讳所束缚,那么她们就能从婚姻中得到并给予男人比维多利亚时代更大的满足。所以,旧道德一旦取消,卖淫现象也会逐步消失。那些以前不得不偶尔踏入娼门的青年人,就能够和他本阶层的女人建立关系。这是一种两相情愿的关系;一种既有身体因素又有精神因素的关系;一种时刻充满双方热情的关系。
从理想的道德观念上看,这对于原有的旧制度实在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道德家们对此深感遗憾,因为这种制度不利于隐瞒。其实,那些道德家所应提倡的第一条道德原则,就是诚实。我认为,青年人中间的这种新自由,完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它正在造就一代没有粗暴行为的男性和不过分挑剔的女性。既然那些反对这一新自由的人,认为卖淫是抵制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严酷法令压迫的惟一安全途径,那么,他们就应当坦率地承认,是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卖淫制度的这一事实。 性爱与婚姻(经世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