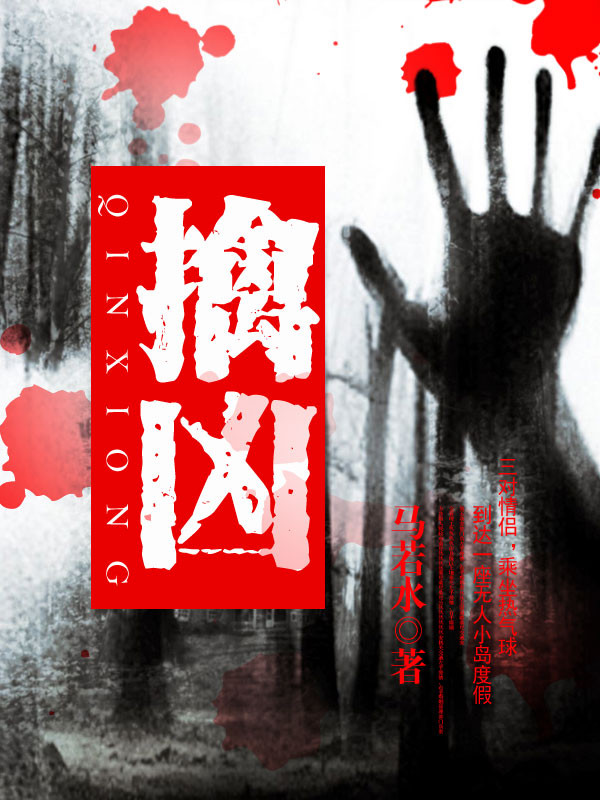季玩暄最近在躲沈放。
虽然已经尽力做得不那么明显,但就连神经粗如宁则阳也多少觉出异样,在午休时间跑过来挤开小季的前桌,伸出手指戳了戳趴在桌上安然午睡的男生:“季玩,最近状态一般啊。”
季玩暄:“……”
他趴在小季面前,语重心长地劝说:“我知道,你痛失第一宝座,心里有所不甘,但也不能因为沈放成绩好就不理他了啊。玩儿,咱要大度,你最初难道是觉得沈放是个学渣才和他玩的吗?”
季玩暄:“……”
宁则阳苦口婆心一番,没能得到半句回应,季玩暄仍然把脑门搁在手臂上熟睡如橘。
班长叹了口气,站起来抑扬顿挫地感慨:“人,永远无法叫醒另一个装睡的人!”
顾晨星搭着路拆的肩膀从后门走进来,一脸纳闷:“大中午搞什么诗朗诵?”
班里剩下的同学稀稀拉拉地笑了起来,宁则阳涨红了脸想解释,余光却敏锐地发现季玩暄轻颤的肩头。
他有些慌张:“季玩你别哭……”
“季玩暄”捂着肚子坐起来,脑袋上顶的赫然是郑禧的脸。
宁则阳:“???”
体委笑得前仰后合,断断续续蹦出来一句完整的话:“难怪季玩叫我吃完饭趴他桌子上装睡,说有笑话看。班长,过分好笑了吧!”
真相大白。
路拆懒得和他们打闹,去教室后排取了篮球就往外走。
顾晨星本来只是陪少爷,没想到却被宁则阳的智商吸引,便多留了一会儿。
“你把我们季玩缠成什么样了?他这么躲着你。”
宁则阳挺委屈:“我没缠他啊,就是一下课就过来聊聊嘛。季玩连小希的兴趣爱好都帮我打听来了,我当然要回报他,帮他排遣压力啊。”
郑禧快笑吐了:“我看季玩好得很,他的压力全是你给的。”
宁则阳怒火转移,恶狠狠地瞪着他:“你是不是在撒谎,想挑拨离间?我怎么会把你这个小矮子和季玩弄混,当我真的傻吗?”
郑禧:“……”
顾晨星:“……”
郑禧:“是,是我撒谎,对不起。”
宁则阳满意地点点头,又看向准备开溜的顾晨星:“季玩最近真的不太对劲,别当我傻看不出来,他怎么了?”
顾晨星遁走不得,索性直接走过来。星星从季玩暄桌筐里掏出糖盒,顺了一根巧克力棒,干脆利落地掰成三份后才撕开包装分给大家。
两人被他流畅的操作唬住,竟也忘了问偷都偷了,干嘛不直接偷三根巧克力棒。
顾晨星将包装袋团成小疙瘩丢进垃圾桶,慢悠悠地给了一个真假不明的标准答案:“他最爱的邻居姐姐去邻市了,季玩心情不好,都别揪着他问了,也许过几天就好了呢。”
这话初听起来挺让人沉默,但细究一下却没什么道理——邻居姐姐走了,跟他躲沈放有什么关系?难不成姐姐还是沈放逼走的吗?
宁则阳还想继续追问,顾晨星却已经消失在门口,下楼去打球了。
男生们口中“心情不好”的季玩暄,此刻正在学校后山的大草坪上惬意地享受午休时光。
耳机里放的是德云社的年度相声,季玩暄躺在铺开的校服外套上,闭着眼睛,偶尔笑出声来。
小山顶上有一棵几人合抱的高大橡树,据说年纪和信雅中学一样大,前段时间漫山遍野都是成熟的橡果,最近却也开始凄凄惨惨地掉叶子了。
沈放抱着手臂倚在粗糙的宽大树干上,目光沉静地注视着远处少年纤细的身影。
如果从实验楼那晚算起,他们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好好说过话了。
季玩暄每天排练节目忙得晕头转向,起初只是彼此默契地互不打扰,但期中考试之后,沈放却后知后觉地咂摸出不对劲来。
他和季玩暄分属不同的年级,纵然竖向位置上直线距离最短,但如果不是双方刻意的话,根本不会有任何交集的机会。
之前是小鸡半残,沈放才每天帮他提书包送他到车站。
但校庆之后季玩暄就重归健康青少年行列,每天蹬着自己心爱的单车上学放学。
消息不回,篮球场他也不怎么来了。
沈放去过几次东校舍,楼主蹭着他的手喵喵时,好像也在问另一个撸猫机器怎么那么久不见。
好不容易找了理由上楼,季玩暄不是不在教室,就是趴在桌上睡觉。
沈放每天放学参加校队训练,门外每进来一个人他就要走一下神,最终连宁则阳也看不下去,问他要不要休息一下。
是发生了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吗……沈嘉祯难道来找他了?找他干什么?
沈放皱了皱眉,仍旧没想明白这个困扰了自己一周的问题。
到底发生什么了,季玩暄。
季玩暄听着相声睡着了,回答不了他。
沈放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离开自己倚靠的树干,走向随意躺在草坪上的少年。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的睡颜看起来都很乖。
沈放无声无息地蹲在季玩暄身边,目光从少年人认真打理过的乌黑碎发一路向下,经过光洁的额头,滑向山根低谷,顺着高挺的鼻梁到达山顶,一个突然的起跳,落在了他晶莹饱满的唇珠上。
沈放:“……”
他可疑地停顿了一下,视线在慌乱之下草草滑到男生被风吹开的衣领里,瞥见了那对若隐若现的精致锁骨。
季玩暄真的很瘦,看起来一折就断了,有种极为脆弱的美感。
沈放轻手轻脚地坐在他旁边的草地上,按着额角打断了自己在危险边缘徘徊的想法。
这么纤弱的一具身体,究竟是怎么做到条件反射帮他接住致命一击的?
沈放轻轻叹了口气。
他当时还觉得这个人多管闲事。
季玩暄的想法他总是猜不透。现在是,很多时候都是。
但无论如何,会好起来的吧。
午休时间还有一段,幸运的话还能做个好梦。
沈放放慢动作,拿起了草坪上仍在放着相声的手机。
密码季玩暄告诉过他,0001——小季相信,最简单的,就是最难的。
但沈放还一个数字都没输,右手拇指刚刚放到home键上,手机就自动解锁了。
他把密码取消了?
沈放有些困惑,但也没深究,只是把耳机声音调小后又设了一个闹钟,便锁好屏把手机放回了季玩暄身边。
他走得无声无息,在逗哏捧哏一句接一句的包袱下,连草叶窸窣的声响都听不见。
只留下了一件被洗衣液泡得非常好闻的校服外套。
后山又只剩下了季玩暄一个人。
他的左耳是郭德纲,右耳是于谦,也不知道是被哪一句笑话戳到了神经,少年伸出右手,小心翼翼地捏住了校服边角。
两根手指慢慢地将外套向上拉,直到遮住了整张睡颜。
他依旧闭着眼睛,像婴儿在母亲体内那样缓缓缩成一团。
阳光很温暖,白色的校服笼罩之下,是他明媚的一整个世界。 潦倒者的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