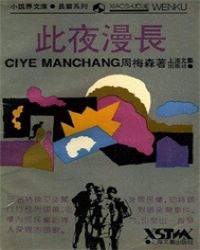两间屋子和一个小客厅都空空荡荡的,司徒效达的心也空空荡荡的。电视大开着,画面不停地变幻,司徒效达呆呆坐在电视机前,却不知电视里在说什么。开初的新闻还有些印象,似乎说苏联的事,后来全记不住了,耳边响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话,眼中看到的是一片飞旋的色彩,唯有空虚的感觉是真实的。司徒效达觉着,自己像一片干瘪的蚌肉,正可怜地萎缩在这套房屋构成的巨大蚌壳里。
自从3天前为老伴方碧薇开过追悼会,司徒效达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明天了,他的明天和老伴的躯体一起化作烟雾,升上了天空。属于他的,除了无休无止的空虚,便是一个个苟延残喘的长夜。人生的壮剧在经过长达67年的演出之后,现在已进入尾声,就要谢幕了。他再没有什么可牵挂的,老伴已经走了,他和老伴的学生们如今都是成年人了,他们将自己担当起他们要为这个世界担当的责任,再用不着他们为他们操心费神了。
追悼会上来了不少学生,花圈堆满灵堂。学生中,年岁最大的已是到知天命之年,最小的也有二十几岁了。有几个还是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哀乐声中,他们一起垂下了头。好多学生都说:“老校长,方老师不在了,我们照应你!我们都是你的学生,也都是你的儿女。”有两个学生还要接他到家里去住些日子的。他谢绝了,他说,他得静一下,得想想,好好把这一生都想想。
他的儿子,他和老伴唯一的儿子早已离他远去。现在,他没有儿女,没有可以向世人炫耀的权力、家产,他一生的财富就是宝贵的回忆,这财富谁也夺不走,只属于他和老伴。老伴走了,这财富将伴着他度过生命的残余岁月。
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站在灵堂里,司徒效达就想起了重庆沙坪坝的校礼堂,那礼堂中央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民党党旗。德高望重的校长在讲话,讲民族的危亡,讲国难时代青年的责任,讲得许多流亡学生热泪盈眶。
就是在那次时局演讲会后,国民政府发起了青年学生从军运动,蒋中正委员长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大后方的高中学生和在校大学生纷纷参军,都准备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和青春的血肉之躯去共赴国难。司徒效达正上大二,他几乎没加考虑,就和许多同学一起,集体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并第一批穿上了军装,一个月后被分配到中国远征军驻印度新一军服役。
这时,缅甸还大部被日军占领着,中缅公路——就是那条著名的史迪威公路,在日军的日夜轰炸中时通时断。司徒效达和同学们无法经中缅公路去印度,就乘了飞机。这是司徒效达第一次,也是后来一生中唯一一次乘飞机。在飞机上,他几乎把胆汁都吐出来了,到印度下飞机3天后,地面上的营房还在他眼前飘飘乎乎转,闹得同学们都笑他。
就是在印度认识了方碧薇——今天过世的老伴。那时老伴只19岁,正是女孩子最值得骄傲的年龄。方碧薇在新一军医院当护士,每逢周末总有一大帮中国军官和盟国军官找她跳舞,司徒效达记得很清楚,他正是在盟军顾问处主办的一次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她的。她和他跳了支华尔兹,让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躁动,那唯有年轻的生命才可能生发出的躁动。
他开始给她写信,找她约会——尽管在当时这是被禁止的。他还在野外操练中故意摔伤了脚脖子,住进了她的医院。是的,是她的医院。在医院的一周中,他想方设法找寻机会,终于在一个同去散步的晚上,冲动地拥抱了她,带着几分鲁莽吻了她。
这一吻是历史性的,不论是对他,还是对她。这一吻决定了他们今后注定要生生死死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后来的苦难离他们那个幸福的晚上还很远,他们看不到它的影子,也嗅不到它的气息。两个纯情的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在一片平静的蓝天下,发誓相爱。他们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唱着《毕业歌》开始了后来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
在印度短暂而甜蜜的岁月一眨眼就过完了,接着而来的是中国远征军的全面反攻:光复密支那。占领曼德勒。中缅公路被打通。盟军攻克仰光。没多久,《波茨坦公告》发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日本的投降,1945年夏秋之交,驻印军新一军带着全套美式装备班师回国。
司徒效达和方碧薇都可以不回国的。方碧薇一家都在印度,是华侨,父亲还是新德里有名的侨领,方碧薇是在印度参军的。当时,方碧薇的父亲已直接找过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要他们俩留下来结婚并定居印度新德里。然而,司徒效达不同意。方碧薇为了司徒效达,也为了她胜利了的祖国,回绝了父亲已作好了的安排,随军医院的军医护士们跳上美式十轮大卡,踏上了缅甸的国土,经中缅公路回了国。
车队驶抵怒江边,远远看到祖国的钢铁惠通桥时,司徒效达和方碧薇都哭了,这种对祖国的感情是任何语言都道不出的。后来,当许多苦难向他们袭来时,正是那怒江,那惠通桥,给了他们以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他们从没有因为1945年跨过惠通桥而后悔。
回国以后就是学生军的复员。大学生活重又开始了。司徒效达在联大继续他的中国文学专业,方碧薇则考取了中央大学。这一来,原定回国完婚的计划推迟了4年。而在这4年中,中国大地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司徒效达和方碧薇是带着无限欣喜欢迎这个新时代的,为了这个新时代的到来,他们都在共产党员学生的领导下,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和那些党员学生们一起跳跃欢呼。他们并不明白这个正迎面向他们走来的新时代将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天真地认为,祖国从此以后将永远摆脱灾难的深渊,他们可以好好干一番无愧于后人的事业了。渡江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入伍,他们带着这种美好的梦想,在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华东军政大学当文化教员。
应该说1949年的5月还是美好的,这份美好一直延续到1956年的春天。在这段日子里,他们是军政大学文化速成班的老师和课外辅导员,那些用枪杆子打出了这个新时代的将军们却是他们的学生。按年龄,这些学生们几乎个个能做他们的父亲,然而,这些父辈学生们对他们都非常尊敬。今天回忆起来,司徒效达还认为,这些父辈学生是他一生中教过的最好的学生。那时候,政府和社会都是尊重知识文化和文化人的。那些急于摘掉文盲帽子的将军们人前背后都称他和方碧薇老师,连小鬼都不能喊。记得有个山东籍的副师长和方碧薇开玩笑,在课堂上喊她小鬼,就受了批评,还在党小组会上做了检讨。
后来发生的一切却糟透了。1956年春天,整编和授衔开始,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双双从部队转业下来,脱下军装,从南京来到本市东方中学教书。到东方中学没多久,便赶上大鸣大放,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奉命鸣放,就学校的教学问题提了些中肯意见——具体是些什么意见,现在已记不清了,可那份真诚和中肯却是记得清的,他们尽管已脱下了军装,骨子里还把自己看作军队中的文化人,在东方中学的同事中谈起军政大学的生活和工作,还不免有几分傲气。恰是因为那份真诚中肯,和掺杂其中的傲气,司徒效达和方碧薇先后被打成右派,司徒效达是1957年头一批划右的,是极右,方碧薇则是1958年补划的。
校党支部书记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说,这叫老账新账一齐算。说他们原就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分子,上大学时就参加了三青团,其后又在重庆加入最反动的青年军,为蒋家王朝卖命……
事情就是这么滑稽,一腔报国的热血在这新时代里竟会变成一盆污水!
司徒效达和方碧薇都不愿生活在污水中。在方碧薇的支持下,司徒效达从1958年初就开始四处申诉,然而,正因为申诉,又落了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罪名,当年底被收审,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5年徒刑。
生活道路从此变得满是荆棘,被强制改造的过程开始了。司徒效达在劳改农场接受改造,方碧薇戴着右派帽子在单位接受改造。历史问题和右派言论像两条巨大的锁链将他们牢牢套住,使他们再也摆脱不了无边的苦海。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他们都免不了被批倒斗臭的命运。
刑满释放后,司徒效达曾以自嘲的口吻和方碧薇说过: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我们正相反,我们得到的只是锁链,失去的恰是整个世界。”
方碧薇却说:
“世界并没有失去,只是世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司徒效达苦笑道:
“其实对你来说,世界可以变得比想象的还要好。当年在印度你是有多种选择的。你可以和追求你的某个盟军军官结婚,这样,你今天可能就定居美国或英国了。你也可以不跟我回国,留在新德里父母身边,继承父母的事业和家业……”
方碧薇淡淡地道:
“真那样,也许我会有另一种后悔。”
“后悔什么?”
“后悔失去了祖国和你。”楞了片刻,方碧薇又说:“人生可能的选择会有无数种,真正完成的人生只能是一种,当年我们共同选择了跨过惠通桥,今天我就决不后悔!”
方碧薇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也没丧失对生活的信心,这让司徒效达为之感动。这感动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在哀乐回旋的追悼会上,司徒效达还不由自主地忆起过她的这段话。站在方碧薇遗体旁,司徒效达耳边一直响着她那自信自尊的声音……
老伴不悔的一生完结了,她骄傲的生命已化作了永恒。她无疑是对的,不管是在1945年的印度,还是在那困难痛苦的日子里,她的生命从未失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甚至还是他生活和精神的双重支柱。如果没有她,他的人生将是不可思议的,他可能会死在1961年饥饿的劳改队,也可能死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中……
司徒效达思绪纷乱,昏花的双眼湿润了,面前的电视画面因此变得更加模糊,他觉着很乏,很累,遂从沙发上站起来,想关掉电视。可不知咋的,手伸出去却没按开关键,倒按了频道键,也不知是哪个频道。这个闹不清的频道在播《渴望》这部电视剧,老伴看了一遍还要看,最后一遍是在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看的,只看到第十五集就去了。现在电视里播的大约是四十几集。
剧中的悲欢离合尚未了结,老伴却不在了,司徒效达心里一酸,泪水从脸上滚落下来……
正伤心时,有人敲门。
门敲了许久,司徒效达才揩去脸上的泪水,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司徒效达觉着脸很熟,却想不起是谁了。这一阵子他的记忆力总是很坏,有些熟人的名字就在嘴边,偏叫不出;还有些常到他们家来的学生他也会认错。
年轻人口口声声叫着老校长,进了屋。
司徒效达精神恍惚,一边给年轻人倒着茶,一边还在想,这小伙子是谁?是他从前的学生,还是方碧薇的学生?看样子,这小伙子不像他的学生,他从1978年起就不代课了,先做教导主任,后来又当了副校长、校长。
小伙子发现了司徒效达的恍惚,怪拘谨地坐在沙发上,对司徒效达说:
“老校长,我是方老师的学生,过去常到你们家来的,我的第一篇散文,还是老校长您给我改后发表的呢!”
司徒效达还是记不起。
小伙子又说:
“那篇散文叫《墓草青青》,是方老师推荐给您看的,您看后很喜欢,找我谈过,还熬了一整夜,给我修改……”
司徒效达问:
“这是哪一年的事?”
“1979年3月。这篇散文发在省报副刊上,开头那段话几乎都是您添的,不知您还记得么?”小伙子轻轻背诵起来:
岁月冲走了我的童年,童年的记忆却印在我的心中。母亲离我远去,母亲早生的白发却永远在我面前飘荡。墓地上的草岁岁枯荣,多少时光流逝了,我的心却……
司徒效达记起来了:
“你是邓……邓代军同学!现在在报社当记者?”
“是编辑。”
“好,好。当记者,当编辑都好,都好……”
司徒效达追忆着:
“做学生时你就有出息,我当时对你们方老师说过,这个小邓将来能做作家。你那篇文章发出来后很轰动呢,就是我们省里的《伤痕》么!你们方老师拿着报纸四处送人,比……比她自己写的还……高兴……”
邓代军很动感情地道:
“我再也忘不了方老师的。许多同学也忘不了她。方老师的追悼会我们能联系上的同学都来了。也是巧,就在大前天,我搬到您楼上来了,在503,听说您就住这座楼,便来看看您。”
司徒效达想了想:
“503住的不是军区哪个干部的儿子么?好像姓张吧?人家的房子咋会让给你?”
邓代军道:
“房子是张副司令儿子、媳妇的。不过他们一个出国留学了,一个在深圳做生意,又在深圳买了房子,这边呢,没人,就把这套房子先借给我住了。这也是等价交换,我在给张副司令写回忆录呢!”
司徒效达点点头:
“是呀,如今都兴这个!”
邓代军脸红了下,说:
“老校长,我……我是开句玩笑,其实,就是不借给我房子,回忆录我还是要写的。帮张副司令写完回忆录,我还可以用这些素材写小说”。
司徒效达没再做声,他觉着自己无权指责邓代军,世界既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那么,我们就不能以理想主义的借口去指责一个年轻人的选择,不管这选择是十分自私还是部分自私的。
邓代军却又说:
“老校长,您也该写写回忆录,您学识渊博,一生经历又这么丰富,若是写下来,对自己是个总结,对后人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司徒效达摇摇头道:
“有什么意义呀?我和你们方老师都是这个时代最平凡的人了,不像你要写的那个张副司令。”
“不能这么说,世界正是由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为主体构成的,因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便是这些平凡、普通人的人生际遇。这不是我的话,老校长,这是您的话,是您在12年前给我改稿的那个晚上和我说的,后来,我就再也没忘记。”
司徒效达一怔:
“我?我说过这话么?”
“您说过。是就我的《墓草青青》说的。”
也许是说过的。司徒效达想,那时候正是他和方碧薇人生第二个春天的开始,他可能说过比这还要深刻的话呢!小邓的《墓草青青》正是因为记述了一个普通母亲在那动荡政治岁月中的苦难,才打动了他和方碧薇的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赞赏这篇作品是为小邓,也是为自己。
不知不觉又想起了老伴,就仿佛看到老伴拿着小邓的作文本在对他宣读。那时这座楼房还没盖,这里还是一片大杂院,他们住在一间20平方左右带地板的屋子里,老伴一边读小邓的作文,一边在屋里来回走动,破旧的地板在脚下咯咯发响……
司徒效达眼圈红了,长叹一声转移了话题:
“想想人的一生也有意思,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都是突然发生的。记得1946年在重庆,我父亲突然去世了,从接到电报那一瞬开始,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大人了。到川北老家奔丧,母亲和弟弟妹妹什么事都问我,我……真惶惑呢,可我不敢在脸面上露出来。我知道,从那时开始,我是一家之主喽,我得镇定,得有主张……”
邓代军深有感触地说:
“是这样,我母亲去世时,我也觉着自己大了……”
司徒效达继续道:
“第二次变化就是前几天了。退下来几年,我都没感到自己老,你们方老师一走,我……才突然感到自己老了,一下子就不行了。我……老想起从前的事,没日没夜地想,就仿佛人已去了,只有魂魄在这里浮动……”
邓代军点点头:
“老校长,这我能理解。这要有个适应过程的,过些日子会好些。这段时间我常在楼上,会经常米看您。”
司徒效达摇摇头道:
“不必了,你们都很忙。”
说到这里,两人都无话了,司徒效达和邓代军就在那儿静静地坐着。窗外,月影在厚厚的云层中飘移,屋里的电子钟在叭哒、叭哒地响。楼下不知哪家突然放起了录音机,声音很大,把这夜晚的沉静打破了……
是一首早几年的流行歌曲——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么熟悉?
我一时想不起…… 此夜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