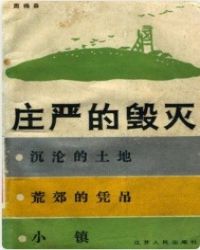当夜,老人失眠了。
年轻镇委书记的出现,搅乱了他那已逐渐趋于平静的心,给他单调而枯燥的生活投下了一道希望的光亮。
“他来了,他终于来了!”
老人在心里默默念叨着。
“他要请我当矿长,当矿长哩!他不是开玩笑。他和我素不相识,不会捉弄我这个老头子的。可是,他喝得太多了,脸颊和脖子都红了。不,不,他头脑清醒得很哩,说话不打哽,有条有理,放开量,他能喝八两!”
老人索性从床上爬了起来,摸摸索索在铁案子上抓到火柴,点起了床头柜上的煤油灯。
“他要请我当矿长哩!唔,这不是醉话,他讲这话时表情严肃着呢,就象三十四年前军代表刘方讲话时的模样。‘我的同志哥哟’,唏唏,‘同志’还‘哥’,有趣!他不是在和我打趣,他不知道咱的过去。其实,知道了又怎么样?咋能以成败论英雄呢!”
老人缓慢而有力地挖那只油腻腻的烟荷包。
“英雄?屁英雄!老脸皮厚,没羞没臊!老了,老了,还这么不值钱,动不动自卖自夸,作兴么?呸!”
老人将一口黑痰用力吐到灶旁,咳嗽了半晌,又吐出一口。离开煤层五六年了,他的肺叶里还蕴藏着这么多煤哩!
“可我为啥一听到‘矿长’两个字就这么惶惑?我为啥要一口拒绝呢?难道我就不能象模象样地做一回矿长给他们看看么?我就这么蠢,这么笨,这么扶不上墙么?这么多年的思虑,难道没使我认清一些浅显的道理么?人,不能自轻自贱!”
老人噙着烟杆站了起来,慢慢走向门口,在门外的木墩子上蹲了下来。
正是繁星满天的时候,一弯残月象只折断了桅杆的小船,在茫茫夜海中慢慢漂荡。夜色掩没了废墟上的满目荒凉,额伦戈壁象一个睡熟了的巨人,变得无声无息。七八里外,隐隐约约透出一些灯光,这灯光很弱,象萤火虫发出的微小的光斑,在遥远的地方和繁星连成一片。
老人在黑暗中抽着烟,烟锅上现出一明一暗的光亮。
“老了,老了。”
老人自言自语说出了声。
“干不动了,你呀,小伙子,你来晚了。”
老人心头升起一丝哀怨,一些往事象烟云一样,轻轻拂过他的脑海。老人又象以往的每一个不眠之夜那样,静静地回顾自己一生中走过的路,艰难地辨认自己留在大地上的每一个足迹。他象在看一部循环往复永远看不完的电影。这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和黑圪垯沟有关…… 庄严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