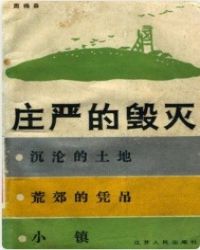下雪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洁白的雪花羞羞答答、扬扬洒洒从高远的夜空投入了大地的怀抱。一会儿工夫,大地便被松软的积雪遮严了。一些地势低凹的地方,积雪约莫有半尺厚。一时间,这个灰蒙蒙的小镇也变得洁静高雅起来,仿佛一个素衣姑娘,颇有几分妩媚之色。路灯亮了,明亮的灯光下,那沉重的、铅一样的灰暗,那无所不在的粗俗,全消失在一片白皑皑的雪景之中。
樊福林家,八仙桌上的洋河酒启封了,小小的斗室里聚齐了这栋房第三世界的三首脑。桌子上首,坐着岁数最大的刘福寿,左边,是主人樊福林,右首,是钱书呆子,他是被樊华硬拖来的。空手做客总不好意思,且为小镇俗成的礼节所不容,刘福寿的老伴儿为宴会供奉了满满一碗炒鸡蛋,钱书呆子也夹了一瓶红葡萄酒来。
每人面前的杯子里都倒上了酒,诱人的酒香开始在空气中弥漫。樊福林红光满面,以主人的身分举起了杯子。
“眼见着要过年了,大伙儿都没啥事,请你们来叙道、叙道,开开心。来,干,干完再说话!”
酒杯送到唇边,未及倒入口中,至少樊福林手中的那杯没倒入口中,门响了,有人砰砰敲门。
“老樊在家么?”
樊福林放下酒杯开开门。
门外立着一个高高的雪人。
“你找谁?”
“我找老樊,樊福林!”
“你是——”
“我姓赵,赵双!”
“什么?你……你是赵……赵书记?”
“咋?不认识了?咱们还是难友哩!一块儿在牛棚里呆过三个月,忘了么?唵?”
不太可能。樊福林使劲挤了挤眼,又把面前的雪人打量了一番。雪人高高的个子,身宽体胖,左脸颊上有一条若隐若现的褐色伤疤,两只凸凸的眼睛里躲藏着一股捉摸不透的光亮,宽厚的嘴角挂着一丝嘲弄的微笑。
是的,恍惚是他。可他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这个刚上任的小镇父母官,会对他治下的一个小小的臣民这么多情么?樊福林心里很有些疑虑。
“嘿嘿,屋里坐!屋里坐!”
赵双抖抖身上的雪,走进了屋。
对门坐着的刘福寿慌忙站了起来,瘦腿在慌乱中撞到了桌腿上,他顾不得痛,在咧嘴吸气的同时,把一个热情的笑及时推上了脸颊。
“哎呀,赵书记,快,这里坐!这里坐!”
“哦,老刘,刘师傅,你也在这里?咋?身子骨还硬朗么?”
“还好!还好!亏您书记想着!我正说哩,赶明儿过了年,伙着老樊去看看您!”
说着,刘福寿殷勤地把赵双往上首的座位上拉,仿佛他是这里的主人。
赵双立着没动。
“赵书记,嘿嘿,您,嘿嘿,您还喝点么?”
“还喝些?啥意思?来到这个小镇,我可是连一滴酒都没捞着喝!”
樊福林有点窘。
“您……您不是从阮……阮部长家来么?”
“我到他家去干什么?拜土地?我这个书记不是替他当的!”
樊福林一怔,马上便反应过来,脸上的笑益发动人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趁他难得的下凡,得把房子的事提提。他娘的,有枣没枣揍一杆子再说。
“嘿嘿,我了解您赵书记,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么?你从来不吃姓阮的那一套!您,咂咂……大伙儿……嘿嘿,都敬着您呢!所以,我一听说您又回咱这儿工作了,马上便到镇委找您,心里揣摸着,咱镇上可来个青天大人了!哎,老刘哥,我可是这么说过不?”
“是的!是的!您直夸咱赵书记清明哩!”
刘福寿给樊福林一个顺水人情。
赵双笑了,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动。
“想来缠我的吧?唵?!老樊呵,你现今可是咱刘洼镇的闻名人物喽!”
赵双在钱书呆子身边的床上坐下了。刘福寿强忍着腿上的疼痛为他摆上了酒杯、筷子,那酒杯还当着赵双的面,特意用热开水烫了两遍,以暗示自己的虔诚。在他看来,樊家来了这么一位天子般的贵宾,自然也是他的光荣。
钱书呆子却有些麻木,淡漠的脸上没有多少表情,激动,自然更谈不上了。赵双在床沿上坐下时,他连屁股也没挪一挪。
不料,赵双偏偏认识他。
“你是小钱吧?打火机厂的技术员?”
“是的,你咋知道的?”
“许多人向我谈起过你,说你为了不使打火机厂关门,正研究改造现有设备,搞转产哩!好,小伙子,有能耐!”
书呆子眼皮一翻。
“有能耐有啥用?在咱这儿可是奴才比人才吃香!”
“哎,哎,小钱,可甭这么说,眼下可是赵书记来掌舵了,您等着吧,有你大显身手的时候!来,我们喝酒!”
“喝酒,喝酒!”樊福林也跟着嚷,“赵书记,嘿嘿,您看,咋喝?”
赵双看了樊福林一眼,立刻在他瘦削的脸上发现了许多虚假的东西,这种虚假的东西也同时共存于刘福寿的脸上。他感到一阵阵难堪难受。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小镇的世风堕落成这个样子,人们对权力的敬畏达到了这种刻骨铭心的程度!几天来,当他以一个镇委书记的身分出现在这个小镇社会上时,几乎处处看得到这种虔诚的虚伪,做作的热情,硬性挤压出来的笑脸。
他点燃了一支烟,把酒杯往边上推了推:
“老樊,甭喊我书记,你还把我看做在牛棚里,咱们是平起平坐的!”
“嘿嘿,书记,您,嘿嘿,您开玩笑了。我也知道当时您是冤枉的,嘿嘿,您,千万甭误会,当初,我可没打过您的小报告。打您小报告的是猪头!他娘的,现在我还不理他哩!”
赵双想哭一场,想好好哭一场!我们的人民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上任仅仅三天,他心里便象塞了一块铅。三天来,他走遍了小镇的每一个角落,看到的听到的,都使他触目惊心。粉碎“四人帮”几年了,这块土地的上空依然笼罩着浓重的阴云。打砸抢分子,造反分子,依然掌握着这个小镇上的一部分权力,他们自恃有阮士杰这个树大根深的靠山,甚至敢在公开场合明目张胆地攻击三中全会而不受处理。在邮局门口的扑克摊前,在大洼子里的说书场,粗俗,依然象无形的君主,统治着这块土地。望着那些风烛残年的退休老工人坐在太阳底下捉虱子、顶鞋底,他眼圈红了,他觉着内心有愧。
他摇摇头,端起杯,一饮而尽。
“老樊,你的事我都听说了。其实,十年前他们就知道搞错了,至少知道你不是什么上校,从那张照片上是看得出军衔的。可他们出于政治需要,硬是将错就错,冤枉了你这么多年!”
“哦?有这事?”
“三中全会后,他们抗不住上面的压力,给你平了反,可生活上却没给你任何帮助。这是不对的,我今天下午已正式通知房管所,重新给你分配住房。你是个建筑工人,七级瓦工,为咱们小镇盖了一辈子房子,就凭这一点,也该分给你一套象样的房子!”
樊福林愣住了,一口菜含在嘴里竟忘记了咀嚼。这……这是真的么?这是共产党的镇委书记说的?难道这个世界真的要变变样子了?难道这个小镇要有真人出世了?他半信半疑,将信将疑,他把眼睛微微抬起,紧紧盯住赵双的脸,试图从那张脸上找出一些破绽。然而,没有,那张脸上充满真挚、深情。
“赵书记,不,老赵,这是真的?”
赵双点点头。
他心里一阵潮热,象窜过一团火,滚过一股电。眼眶有点发湿,眼睫毛有点发粘,视觉渐渐模糊起来,赵双的面孔一时间分化成两个,两个赵双都在平等地向他微笑。
“老樊,我的老同志呵,别这么瞅着我,我心里也难受!”
赵双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嘴角有些抖。
“不让你正正经经、堂堂正正做人的,不是共产党,至少不是真共产党!‘四人帮’被粉碎了,可他们的基础还没有彻底消亡,我们可要把咱们的党和他们划划开,甭把自己的脑袋搅糊涂了!”
两滴老泪,不知不觉从眼眶里滚了出来,顺着鼻根,缓缓向嘴角淌。樊福林一把揩去了,使劲点了点头。他觉着自己在做梦,在做一个期待已久的梦。
“我也要批评你!”
“你说,老赵,你说!我……我听着哩!”
“过去,社会待你是不公平的,可这不应该是你自暴自弃,玩弄社会的理由哇!咱们静下心想想,这几年咱是怎么过来的,愧不愧?咱自己就一点责任也没有么?做人就那么容易?!”
樊福林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扯住赵双的手。
“老赵,你……你……你骂吧,揍吧,揍我一顿吧!你看我这个样子,哪还象个人!连一个好端端的儿子都让我教瞎了!我……我……我也悔呀!”
赵双叹了口气,又道:
“是呀,咱们的生活再也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咱们该为昨天那不死不活的日子划个句号了。这回重到镇上主持工作,我有个打算,要把咱这块地方根治一下,把历史遗留下来的所有粗俗不堪的东西,通通扫到垃圾堆去!咱要为这小镇的编年史写下值得骄傲的一页,让后人知道,咱没白活着,咱干了些事情!老樊呵,你这个七级瓦工也站出来贡献点力量吧,带着咱上百口待业青年搞个建筑队,为咱刘洼镇盖座象模象样的俱乐部,再也不能眼见着我们的老前辈在大街上光着脊梁捉虱子、顶臭鞋了。我已和团委讲了,团员青年业余时间也来工地打突击!”
“这可太好了!”刘福寿道:“真这样的话,我也算一个。”
“老樊,你干不干?”
“这……这还用问么?老赵,只要是你说的,我……我都干!”
“好!我们喝酒,来,举杯,这叫同心酒!”
几只装满酒的杯子同时举了起来……
几杯酒下肚,樊福林有点昏昏然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恍恍惚惚。可他的心还是极清醒的,他又想到了阮士杰,善良的心里不由的有些担心,替赵双担心:不买阮士杰的账,他在小镇上能站住脚么?……替别人着想,不太符合马虎哲学,马虎哲学的基本定义是以自我为轴心的。而今天,他却想到了别人,这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进步。
“老赵,你真不去看看阮士杰么?他就在这栋房的头一个门!”
“改天再去吧!我手头接到不少告他的群众来信,得找他好好谈谈哩!”
“咋?有人敢告他?”
“不信么?你们这里就有一位!”
“谁?”
“小钱!”
樊福林激动了:“来,小钱,我敬你一杯,你比我老樊强,都学我这个样,咱大伙儿永辈儿成不了人!”
钱书呆子接过酒一饮而尽:“我早就说了么,要有信心!我就不信咱们党不能收拾他。对他拉帮结派,反三中全会的言行,我早就注意了,心里记下了一笔帐!”
“好!好!早该和他们这帮人结结帐了!”樊福林带着三分醉意,摇摇晃晃站起来大喊,“樊华,放炮!放炮!咱们提前过年了!”
“叭!叭!叭……”
炮竹在夜空中炸响。一串火光,一串笑。带着火药味的纸屑伴着飞舞的雪花,在空中飘荡……
炮竹的响声,惊动了这栋房子的所有居民,刘福寿的老伴,钱书呆子的老婆,都从自己的家门探出头来。
阮士杰也推开门看了一下,他的脸依然那么威严,只是多了点疑虑和困惑。猛然,他在爆响着的火光中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庞,一个今晚应该出现在他家里的面庞,他心中一阵紧缩,恍惚感到,这个小镇似乎要发生点什么变化,不,已经发生了点什么变化……
“老阮,到这边坐坐!”
似乎是那个面庞在说话。他没理睬,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多想把这变化永远关在门外呵!炮竹的爆炸声消失了,一时间静得吓人,他歪倒在沙发上再也不想起来了。一丝淡淡的哀伤袭上他苍老而可怜的心头,他觉着自己老了,真的老了,甚至眼睛一闭就会死过去。
不!他挣扎着坐了起来,把威严重新摆到脸上,以不容反驳的口气,向老伴儿命令道:“去,给我收拾一下东西,明天,我要到市里去!”
…………
雪还在飘,从深远的高空往坚实的大地上飘,纷纷扬扬,悄无声息,仿佛给安睡中的小镇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小镇安睡了,它在做着一个关于明天的梦……
一九八一年三月初稿于徐州
一九八二年七月修改于南京 庄严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