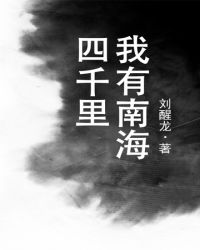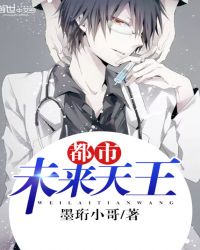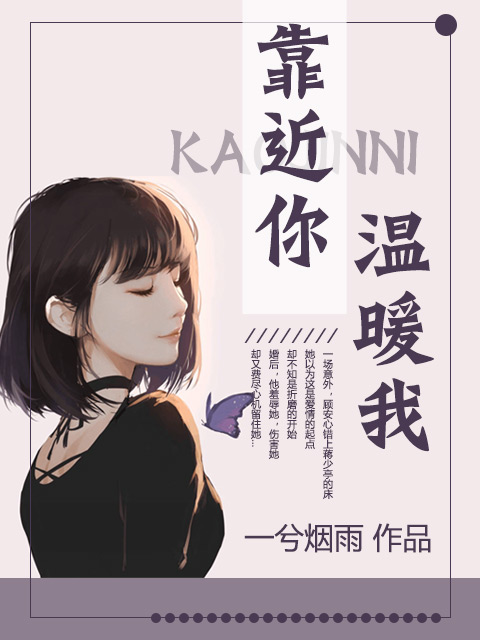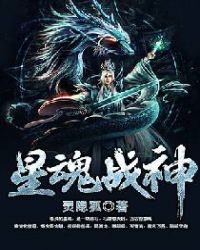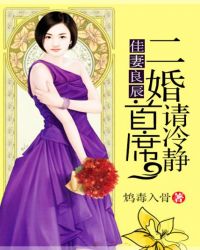整整十年了。那一年,也是这样的夏天,头一回与共和国的军人们产生不仅是正面而且还是全面的接触。那一年的故事是在青藏高原上发生的,足迹所至,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亚热带谷地,到世界上最高的国防哨所,一幕幕的军人军事让人整日整夜地沉浸在无边无际的感动与感慨之中。
十年后,重新走进军营的第一天,与一群共和国的导弹兵面对面坐着,刚开始,大家似乎都没找到共同的话语。沉默之际,我突然想起十年前听来的一个故事,于是就说,要给他们讲个故事。
在过去的某年某月某日,共和国的军事情报部门,监听到邻国边防部队下级官员向其上司报告,说中国军队已在毗邻边境的连级哨所秘密部署了防空导弹。一时间邻国的军事部门感到分外紧张,一再电令其下属迅速查证。不仅是在邻国,在国内,这种奇怪的情报,也让我们的军事首长们觉得莫名其妙,不得不命令下来,火速查明真实情况。在我方,尽管那时候,边防通信远不及当前发达,但是查起来也一点不难。实际情况是,因为地处高原,在种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就连当初从美国引进的黑鹰直升机机翼长度都要比在内地自然增加几厘米,所以,除非万不得已,就连民航飞机都不敢在海拔高度还算不上太高的拉萨机场过夜。而在那离蓝天更近,离内地更遥远的高原哨所,共和国的军人所配备的只能是最常见的轻兵器。与之相反,因为当年吃过败仗而一直心存敌意的邻国,由于地理条件的优越,哪怕是最普通的飞行器,也能从他们的平原上起飞,迅速抵达由两军分而据守的高原上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那些从山那边平原上起飞的苏27歼击机,看准我们的空军驻扎在数千里之外,便蓄意地飞临我们的哨所上空,反反复复做出各种战术飞行动作。实际上,在那种条件下,不要说一挺机枪,任何一种可以连发的轻武器,都可以将这架非法入境的军用飞机像飞鸟一样击落。哨所里的尉官们早就气炸了肺,一次次地向上报告,从请示如何处置,到请求有限度的还击,然而得到的答复,总是强调要以国际外交战略大局为重。唯独那一天,情况有了小小的变化。那位中尉连长,于激怒之下,急中生智,从营房里推出一只铁架子,就在他一把掀开上面遮盖的油布时,那架一直在哨所上空盘旋的苏27歼击机,猛地一个拉升,转瞬之间就飞得不见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露面,把那一片共和国的蓝天还给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白云,以及白云下面的共和国哨兵。那位连长在向上级汇报时,还免不了发牢骚说,我又没有走私军火,从哪里弄得到导弹,你们配备给我的最先进的武器不过是一只放在铁架子上的氧气瓶。
导弹兵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或者在他们心里还藏着更加精彩,因为军人纪律而无法示人的故事,我不得而知。他们只是对我的故事轻轻一笑,还不忘相互看上一眼。那几位中尉,正与那个将氧气瓶当作防空导弹,吓退骄横的苏27歼击机的边防军官相仿。让人很难不作联想:这些年轻的笑容里蕴含着多少战略导弹抑或战术导弹的底气?我在情不自禁中,反复打量着这些导弹兵的手指,难道就是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甚至还不够成熟和不够有力的手指,在某个关键时刻对着红色按键的轻轻一击,就成了关键的力量?说起来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希望这些肩负重大责任的军人,应该与普通人或者普通士兵有所区别。眼前的这群导弹兵,从哪个角度观察,所感觉到的仍然是一群耳熟能详的邻家男孩,笑的时候很阳光,不笑的时候也很阳光。一个人心里的阳光灿烂,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方法去补充的,它是一种日积月累,是一种仿佛天成,甚至根本就是一种人生素质。相比之下,这种素质比起技术因素,应当是更为紧要的。要达成这一点,没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积沙成塔、汇流成河的过程是根本不行的。一旦达成了,其威力就会比在某个时期倾尽全力所造成的“卫星”式的东西要强大不知多少倍。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将一个人锻造出各种各样的异质。有一支部队号称铁军,还有另一支以猎豹作军魂的部队,两支部队的指挥官在国防大学读书时,就是各自班上的班长,上军校时两人就开始暗里较劲,毕业后又在相隔不远的各自驻地中隔空比武。与他们分别相处的那几天,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只要一提及对方,在他们的脸上就会出现一种显著变化。指挥铁军的那位,正如他之治军,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狠到底。一如他的那句让人闻之色变的名言:我只要第一。显然,这句话是有出处的,这支部队最早的指挥员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塔山阻击战打得最惨烈时冷酷地说过:我只要塔山,别的我不管。所以,在“和平使命——二〇〇五”中俄军演中,才能以比俄军领先一分钟的优势,抢占战场主要高地。以猎豹作军魂的那位,在我们到来前几天,刚刚下令,让下属的一支刚刚完成演练任务的部队在原地坚守三天,并不等下属指挥员说完给养如何解决的话,沉静地打断说,我只要你守三天,如何守那是你的事,我不管。曾经亲眼目睹高速行驶的九六式坦克蛮横地从卧倒在泥泞中的士兵们的头顶上轰轰隆隆地辗过,演练场边的指挥员却心如止水地告诉我们,如此为了让士兵们克服战场上对坦克的恐惧心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的很难想象,每一次实战演练,这支部队的营连排长们总是亲自操枪操炮,用一次次的首发命中带头打响。如此才有那一天,那群高速行进的九六式坦克,无论地形有多复杂,都能够将一发发炮弹极为精准地命中两公里的靶标。
眼前的这支共和国军队,于我一点也不陌生。当然,他们并不是从青藏高原上撤下来的,虽然他们中有某些军兵种曾经多次进入青藏,投身各种各样的军事或者民事演练。对他们的熟识正好也是发生在十年前,那时我刚刚从青藏高原上下来,整个人还处在严重的醉氧状态中,即便是那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洪水也无法完全唤醒我。就在我们的城市被滔滔洪水围困之际,《解放军报》的一位朋友空降而来,邀我一道去到千百年来无人知晓,却在一夜之间闻名于世的簰洲垸采访。我是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日来到这支部队的,这个日子离他们开始整编的预定时间只有六天。但是一场跨世纪的洪灾,彻底夺走了他们为自己的明天与未来思考的机会。这支部队从原驻地出发昼夜兼程赶到武汉,然后又马不停蹄地独自赶往嘉鱼。刚进县城,命令就下来了:拦阻江水的护城大堤出现两处重大险情,数百名官兵连安营扎寨的地方都没看见,便跑步冲上江堤,一口气干了十一个小时。八月二十一日上午九点整,我们正在采访团长和政委,突然来了紧急命令,五分钟内五百名官兵便登车直赴发生险情的新街镇王家垸村。面对他们的又是一个罕见的管涌,直径达零点七五米,流量为每秒零点二立方米。发现时,它已喷出一千多立方米泥沙。在这场与灾难赛跑的全过程,在水深齐腰的稻田里,士兵们用自己的身躯铺成了两条传送带。有两个连队已在附近江堤上突击干了一天一夜,正要轮换休息,早饭都没吃,便又赶来抢险。陆续赶来的部队达两千余人,泡在水中的这些最早到达的官兵直到将两百多吨堵管涌的沙石料,徒手运到现场才上岸休息。
之所以想起来这支在共和国军队序列中已经消失十年的部队,是因十年后的今天,在所到之处的部队纪念馆里,不断地见到我所在的省份中,各级政府,还有人民群众自发赠送的锦旗。那时候,隔着一条无意让两岸无数生命涂炭的却又不理解生死两茫茫偏偏总是悬于一线的长江,堵罢管涌归来的一位军官,指着对岸的洪湖一带,充满妒忌地说出正在那里抢险的另一支部队的番号与历史。那一年险过刀刃的洪湖大堤,在成为一段英雄史后,才以对过去充满感慨的形态出现在我的眼前。有当时在长江南岸的亲历,我当然晓得,那时的长江北岸,洪湖之水不是浪打浪,而是能惊天地泣鬼神,很难说多少倍南岸的险情,都被十年之后我才认识的这支铁军一一化解了。所以我才情不自禁地怀想,他们的指挥官在当时一定很冷血地说过:我只要大堤在!那时他们的每一个士兵一定也对自己说过相同的话:我在大堤就在!
十年来,军营中有变的,也有不变的。回到当初,在举世闻名的青藏高原上,有一座查果拉哨所,哨所里有一位士兵,从上山之后,直到退伍时才第一次离开海拔五千三百一十八米的战斗堡垒。在日喀则一处有些规模的军营里,那位士兵下车后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闻之揪心的事:身为男子汉,他却抱着一棵大树哭了半个小时。在他的高海拔军旅生涯中,除了一些苔藓类的小草,随风飘扬的就只有军旗与白云。告别铁军后,来到某潜艇支队,我曾经戏称,干作家这行,本质上也如潜水员,到处晃荡时,别人才看得见,没日没夜地写作时,却谁也不清楚。一位水兵却认真地说,每一次执行训练任务回来,上岸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宿舍,也不是打电话,而是跑到球场上,抱起篮球没命地玩上大半天。当我们有机会进到潜艇机舱后,才明白士兵们的这种感受。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其他各种艰难也许都可以通过训练逐步适应与克服,即便是一团冷冰冰的钢铁,也会被憋出欲望,渴望好好地伸一伸腰,踢一踢腿。
虽然军人不好当,虽军事游戏不得。军人军事却又与每一个生命过程相似,任何的轰轰烈烈,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享受人生中最美好的安宁。这一次,在离开军营之前,我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拥有这支军队写了如下一段话:和平是一种崇高的人文精神,又是一种普遍的幸福境界。作为和平年代的军人,需要比金戈铁马血雨纷飞时期更为强大的意志力。人之为铁在于战胜自己,军之为铁在于战胜对手。我为这个时代,能有如此强悍的铁军作为和平捍卫者而深感欣慰。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九日于东湖梨园 我有南海四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