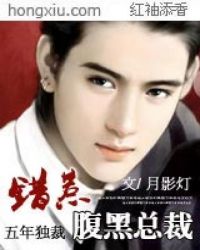1 罪
我接到大哥去世的消息好半天没有缓过神来。倒不完全是悲伤,还有震惊。一个多月前我回老家看他,他的状态还非常好,赶集、下地噔噔的,中午吃捞面比我吃得还多。三天前侄女打电话来,还说她父亲的身板儿忒好了,整个麦秋没闲着,刚帮着老儿子收完场。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
生死的转换难道可以如此迅捷、突兀?平时听到什么人猝死的消息,虽然也要惋惜一番,但跟自己的亲兄弟突然故去大不一样。骨肉连心,疼到深处,于是生出许多疑问……
一个人可以毫无缘由地就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要死去则必须有原因。如果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就撒手走了,会把亲属坑一下。但那也许正是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福,叫“善终”。“善终”比“善始”更难得。
“善终”是有条件的,要活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是俗话说的已经“活够了本儿”。死的时候要干净利索,没有受罪。
对许多人来说,死可不是简单的事,更不容易。按现代医学的解释,人的死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要忍受极大的痛苦才能最后告别这个世界”。“善终”就是没有这种痛苦,或极大地缩短了这种痛苦的过程。
于是人们把活到古稀之年再去世称为“喜丧”——把“丧”和“喜”联系起来,是中国文化的高明。办“喜丧”和一般的治丧感情的投入不一样,表面上是办丧事,心里却把它当喜事来办。明明是死了人,又喜从何来呢?喜的是生命已经不亏,到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自己不再受罪,也不会给活着的人添罪了。
这几年我可真是见过几位受够了大罪之后才闭眼的人,他们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家属的亲情、孝心也被折腾得到了最后的临界点,嘴里不说,心里恨不得快点解脱,病人解脱,别人也跟着解脱。人人都希望能健康长寿,但肉体凡胎是由碳水化合物构成,活的年头太长了,怎么能够健康?最常见的是没有力气控制屎尿,干净了一辈子最后却陷于屎尿阵之中,失去了排泄的快感和做人的尊严。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有些宗教里关于“原罪”的理论……死是对一个人所有罪愆的总惩罚。
所以能够预测自己圆寂日期的高僧,提前许多天就不吃饭了,或者喝一点能清理肠胃、让肉身不坏的草药,让自己干干净净地脱离尘俗。
大哥走得这么干脆利落,自然不会受罪。他活了77岁,不算长,也不算短。我们的祖父活了74岁,父亲是77岁,他们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很清醒,走得干干净净。看来我们蒋家的男人大体都是这样的寿命了——正因为寿命不是很长,所以受的罪也少。我算了一下,自己还有20多年的阳寿。突然间对自己最后的结局看得清清楚楚,心里一阵轻松,感到欣慰,竟没有丝毫的恐惧或遗憾。这要感谢大哥,是他的去世提示了我……
有生必有死,人从一出生开始就被死亡追赶,或者说是追赶死亡。人应惧生,而不是惧死。村里蒋姓一族,长一辈的人已经没有了,我想大哥对死早有准备,也许等待好几年了。特别是一年多前大嫂去世后,对大哥来说,死就变得真切和迫近了……感到意外的只是我们。意外的理由就是他的身体还很好,这其实是很盲目的。
在身体很好的时候离世是不失尊严地自己走,身体被彻底拖垮后再去世是被动无奈地被拉走。
2 礼
我们共有弟兄四个,二哥死得最早。天津还有一个七十岁的三哥,他对家乡对大哥乃至对乡亲们的感情是我这个最小的弟弟所无法比的,他坚持要回沧州亲自为大哥送行,让我暗松一口气。我原来还担心,三嫂或侄子们怕他年纪大吃不住奔丧的辛苦,不让他回去。那样我就成了家中唯一的长辈,一个长辈在丧礼上应该怎么做我可是一窍不通。
老家治丧有严格的程式,极尽繁琐和铺陈,一切都得按规矩和乡俗进行。你说你有真情,很悲痛,但乱哭乱闹也不行,那叫“闹丧”;“闹丧”所表达的意思是对丧事办得不满意,对帮忙的人或侄子侄女们有意见,想找茬闹事。会说你在天津呆了几年,故意狗长犄角——羊(洋)式的。我可不想叫本家的晚辈和村里的乡亲们说闲话,最好是一切都做得中规中矩。哭要会哭,说要会说,站要会站,跪要会跪,走要会走……在治丧的全过程中,每一项程序都有许多人在围着观看,你做错一点就会惹得议论纷纷或被指指戳戳。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奔到兄长的灵堂前,是该跪着哭呢,还是弯着腰哭?
有三哥在,我就省心了,一切按着他的样子做就行。偏我有个毛病,性情急躁,说话快,动作快,走路快。到了大哥生前居住的门口,一大群乡亲在盯着我们,不说话,不打招呼,连做棺材的也停了手直瞪瞪地看我们怎样哭,有人扭头跑进院子,想必是给侄子们送信儿,院子里立刻传出爆炸性的哭声。这一紧张我就忘记等三哥了,也许是急于想见到大哥的遗容,自己腿长脚快地先进了院子,这时候侄子们哭着迎了出来,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先于哭声而流出来了。奔到堂屋,见大哥的身上罩着黄布,躺在一个玻璃棺材里。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是水晶棺材?没听说哪个侄子发了大财能给大哥买得起水晶棺材?门外边不是正在赶做木头棺材吗?怎么不让我们见大哥最后一面就入殓了?就在我走神发愣,手足无措的时候,两个侄子扶架着三哥号啕着进了屋,我赶紧小声请示:
“要不要跪下哭?”
“不要。”
“咱得见见大哥的面儿吧?”
“得见,”三哥发了令,“打开冰柜。”
原来那是冰柜,为了镇着大哥的遗体不会变坏。麦收季节,正是五黄六月天上下火的日子,没有生命的肉体很快就会腐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一碰上事就犯傻,常常露出一股呆气。
冰柜是两半儿的,有人开始撕揭封住连接处的胶布。要和大哥见面了,屋子里掀起一个痛哭的高潮,极富感染力,当时即便是木头人也会随着掉泪。侄女婿大声提醒哭泣者,他的声音高出所有的哭声:“不要把眼泪掉在死人身上!”这小子就这么称他岳父为“死人”……我又赶紧提醒自己,这种时候你就别挑字眼儿了。
冰柜掀开了,黄布拿掉了,我见到了大哥的脸。我对这张脸是非常熟悉的,现在却失去了生气,显得发黄,僵硬,怪异。嘴张着,眼也半睁着……莫非因走得匆忙,有些心事未了?小侄子用手掌帮着他父亲合眼、闭嘴,口中还念叨着:“爸爸,我三伯伯、老伯伯都回来了,你老牵挂着的人都在这儿守着哪,放心地走吧。把眼闭上吧,把嘴闭上吧,别吓着你的小孙女……”
小侄子的话又把满屋子的哭声催动得更为悲切凄厉。但大哥的眼和嘴仍不肯痛快地紧闭上,小侄子的手掌仍然极有耐心地在大哥脸上摩挲。人死了就该闭眼,所以人们把死亡又通称“闭眼”。死而不闭眼,是死得不安,也让生者不安。这时候哭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每个人都希望大哥快点把眼和嘴闭上。于是知道大哥心思的人,或者边哭边加以解劝,或者在心里默默地跟大哥对话,就仿佛大哥还能听得到大家的话一样。
我在清明节回来的时候,知道大哥有两件心事,一件是大侄子的儿子买房缺一点钱,另一件是二侄子的大小子还没有说上媳妇。其实这都不是大事,大侄子全家在天津,他是铸造业的能人,兼职很多,收入颇丰,他们既然想买房就一定会有办法弄到钱。二侄子的大小子才20岁出头,长得精精神神,身体健壮,尽管读书不多,在农村还能打一辈子光棍吗?我也暗暗地劝慰大哥,该闭眼时就得闭眼,该撒手的就得撒手。儿女都已长大成人,儿女的儿女就更用不着你操心了。
人死是高潮,所有的人都围着你转,哭你,想着你,念叨你,在三天的治丧期里你是全村人关注的中心,一个普通人不就是到死的时候才被人发现你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可缺少吗?是死成就了一生的辉煌,你已问心无愧,赶快高高兴兴地去找祖宗们和大嫂团聚去吧。
大哥的双眼终于慢慢地闭上了,嘴还微微地有点张着,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主事的人张罗着又用黄布把大哥盖上,把冰柜合拢,重新粘好胶布。我们从天津赶回来为大哥治丧的第一个程序就算完成了,大侄子把三哥和我让进里屋,要进行第二步:全家人商议丧事应该怎么办?
大侄子说:“我爸爸不在了,三伯伯、老伯伯就是我们的老人,丧事该怎么办得听您二老的。”这话说得我鼻子又有点发酸,大哥的丧事该怎么办,主要得看大哥儿女们的意思,我相信在我和三哥回来之前他们兄弟姐妹肯定已经商议过了。尽管大侄子说得很动情,很客气,表现了对还活着的长辈的尊重,但我和三哥却不该轻易发号施令。我让大侄子先说说他们的想法,他说:“我和三伯伯、老伯伯在天津生活,丧事怎么办都好说,村里还有三个兄弟,丧事要办得合他们的心意,该有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
大侄子说得合情合理,他的情绪也很冷静,到底是喜丧,哭归哭,哭过就算。我请三哥表态,他对侄子们的想法表示赞成,我也觉得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或另外再提出一些要求——除非我们是想挑刺儿。
三哥提了个我也很想知道的问题:“你们的爸爸到底是怎么没的?”
在老家的侄子们必须对他们父亲的两个亲弟弟有个交代。大哥和三侄子住在一起,就由老三来说:“昨天晚上,我爸爸到二哥家吃面条,前些日子有人给二哥的大小子介绍了个对象,媒人回信儿说,基本就算成了,大后天正式定亲。我爸爸高兴,吃了快两大碗,九点多钟回来先去了茅房,大概是想解完手就上炕睡觉。隔了一会儿狗叫起来了,我以为有外人来串门,出去看了看没有人,等我一回到屋里,狗就又叫个没完,我第二次出去把它喝唬了几嗓子。等我一回到屋,它叫得更凶了,我突然意识到不好,赶紧往外跑,我爸爸已经堆糊在茅房外边的墙根底下了。我喊您侄媳妇把我爸爸抬到屋里,赶紧叫孩子去把我二哥和老兄弟叫来,我去请大夫。大夫来了又打针又灌药,我爸爸就始终没有醒过来,到凌晨四点咽的气。”
如此说来大哥真的是“喜丧”——因喜而丧。成了他一块心病的孙子谈成了对象,一高兴就吃了那么多面条,老家的那种大碗,有一碗就够他那已经工作了77年的老胃对付的……大哥应该是死而瞑目的了!
3 吃
亲属将治丧的大原则一经确定,帮忙的人就开始忙乎了。其实就在我们一大家子人还在东屋商量的时候,治丧的领导核心已经自然形成并开始工作了。以我本家的一位兄弟为首,他在村里是个说说道道的人物,还有一位负责记账的,一位守着一个黑人造革提兜专管钱的出纳,一位掌握治丧进程、指挥和调度一切的“总理”,另外还有两个侄子辈的人当跑腿的,负责采买。他们占据了三侄子家最好的一间屋子,那间屋子就成了“治丧大队”的队部,治丧工作也就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了。
在当街一拉溜搭起了三个大棚,都是租来的,铁管一支一架,用印了治丧图案的白布一罩,里面摆上了几十张饭桌,大出殡的架势就出来了。这几十张饭桌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丧事的规格。主家想办多大场面,就看有多少张饭桌,将饭桌摆多少天。
治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吃,根据你的家底儿,你想把丧事办到什么规模,桌上的菜应该上几个碟几个碗,约定俗成是有惯例的,你太寒碜了就让村里人和亲戚们笑话,甚至会怪罪。大哥的两个兄弟和长子都在天津卫做事,侄子们又想把丧事办得好看,那就得豁得出去让人吃。再说人家来吊唁都不会空着手来,烧纸是必带的,同时还要随礼,少则10元,多则几十元不等,不交钱的也会送一块幛子(布料)。
在民间深入人心的“吃绝户”最早就是由治丧引起的:没有儿子的人死了,在办丧事的时候人们就会拼命地吃,主家如果不大大方方地让村里人张开肚皮大吃几天,就会犯众怒,遭到唾骂。因为他继承了绝户的家产,也是白捡来的。以后演化成凡是丧事都要吃,从吃的规模看丧事办得排场不排场。吃是给死者减罪,到阴间少受苦,也是给死者的后人免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治丧大队”的成立,火头军立刻行动,在院子里和大门口两边垒灶埋锅,一笸箩一笸箩的馒头蒸出来了,一大盆一大盆的菜炒出来了,一箱箱的白酒、啤酒从供销社搬来了……本家兄弟以及为丧事帮忙的人,理所当然要在丧事上吃,外村来吊唁的人随到随吃,流水的筵席就算开张了。所谓“流水席”就是指吃饭的人像流水一样哗哗流不断,前边的人刚吃完,后边的人又接上来。或者前边的人还没有吃完,后来的人已经在等着了。
但是孝子们——也就是我的侄子、侄女、侄孙子、侄孙女、外侄孙子、外侄孙女们以及我们从天津去的一帮人,吃饭要自己想办法,或者见缝插针地从灶上摸个馒头盛碗菜。找个地方三下五除二地划拉到肚子里去,或者到哪个侄子的家里让侄媳妇抽空给做碗汤喝。所有参与办丧事的人都是在帮我们家的忙,从情理上说我们应该照顾人家,人家没有义务还要照顾我们。可是整个丧事有自己的领导机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听从“治丧大队部”的号令,我们倒成了局外人。
“治丧大队部”的几位核心人物,他们坐在炕上天南地北,家长里短,说得开心,笑得痛快。三天里他们很少下炕,更难得出屋,灶上炒出了菜先端给大队部的领导,他们喝的酒也比外面那几十桌上的酒高一个档次,丧事操办过程中的大事小事都得请示他们以后才能办——办丧事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平时农村干部的权威性了。
其实,大哥也被冷落在一边了。这些人并不悲伤,无非是想借他的死热闹一下,大吃大喝,猜拳斗嘴,过过酒瘾,而且吃喝完了还不会感谢他。因为谁都知道,很会过日子的大哥,在他活着的时候是绝不会请这么多人到家里来十个碟八个碗地吃喝一通的。如此看来,与其死后被动地挨吃,真不如活着的时候主动请人来吃……
三天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寂寞的大哥的棺材旁边,和认识的乡亲说话,回想我在村里度过的童年生活,好奇地看着丧事乱糟糟地以吃为中心地在向前推进。
4 烧
第二天的主要程序是火化——这令我大为不解,已经拉开架势要把丧事办得热闹、堂皇,还做成了那么结实壮观的棺材,为什么还要火化呢?“治丧大队部”的头头向我解释:现在农村不许土葬,谁家死了人偷着埋了,让村委会知道后不仅要把人挖出来照样送到炉子里去烧,还要罚款。没有人敢惹那个麻烦,于是农民们想出了这么一招儿,死一次葬两回,先火化,后土葬。只要火化完了,你再折腾多热闹政府也不管了。
这才是农民的幽默,是无数“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中的一“策”。
人们之所以惧怕火化,是因为火化完了人就彻底地消失了。因此有些老人临死前只留下一句话:“千万不要把我烧了!”现在先把人烧了,还要埋什么呢?
外面阳光很毒,热风烫人。孝子们哭着把大哥抬出来放到灵车上。沧州火化场的这种灵车却令人难以忍受,它是在普通的面包车底盘下面开了个长抽屉,把死人往里面一塞,然后让孝子们坐到上面,把死了的老人踩在脚下……这时候已经没有人顾及这些了,好像火化就是这种规矩,既然不得不火化也就不得不遵守火化的规矩。
火化场在沧州市的西南角,离村子很远,正好可以让一群半大小子尽情地耍把。他们坐着一辆拖拉机在前面开道,喀嘟嘟开得很快,鞭炮挂在拖拉机的后尾巴上,一路上劈里啪啦炸得烟尘滚滚,同时趁风把纸钱撒得漫天飘舞。
在烈阳下,这支奇怪的车队把气温搅得更加燥热了,引得路两旁的行人都捂着口鼻看热闹。好像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火葬场。火葬场空旷而简陋。但生意不错,在大哥的前面还有两个人,大哥排在了上午的最后一炉。空荡荡的大院子里没有荫凉处,大家挤在火化炉外面的墙根下,有一位老太太在卖汽水,身边还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可以自由进入到火化炉跟前,在停放于炉口外面的死人跟前走来走去,不躲不怕,熟视无睹。这个姑娘长大了若分配当火化工,一定不需要别人再给她做思想工作……
在漫长的等待中,孝子们都躲到凉快的墙根底下去聊天,只有大哥自己孤单单地躺在火化炉前,排队等着化为灰烬的时刻快点到来。一送进火化炉,大哥就彻底消失了,这一刻应该是孝子们痛哭的时候,生离死别嘛。对死者多看一眼是一眼,多留一会儿是一会儿,希望尽量延缓把亲人送进火化炉的时间。可是,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希望快一点烧,烧完了快一点回去。天也实在太热,年轻人的肚子大概早就饿了。
我默默地对大哥说:你不要怪哟,现代年轻人的孝心作作表面文章还可以,却经不住大的考验。为你的死这样大操大办,看似奔着你来的,吃的是你,花的是你,折腾的也是你。其实是你的死折腾了活着的人,吃的是活着的人,花的也是活着的人,这些花样一概与你无关,是为了活人的面子,是折腾给活人看的,归根到底还是活人折腾活人。
5 唱
三哥还是发了脾气。不是闹丧,是冲着乐队。
三哥年轻的时候是村里的吹笙高手,逢年过节或赶上庙会,为唱戏的伴奏,谁家有了红白事儿,少不了也会被请去吹奏一番。那个时候他们在丧事上吹奏的是《无量佛》、《坐经曲》、《行经曲》,还有几支哀怨伤痛的悲调,乐器一响,沉痛悲伤的沮丧气氛立刻笼罩了治丧现场,也笼罩了全村。亲的热的会悲从中来,想起诸多死者的优点和好处,即使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会被音乐感染,心生同情,悲怜人世,都变得宽和友善了。
在那种乐队的伴奏下,孝子哭得格外悲痛,来吊孝的人也哭得自然。特别是到夜晚,《无量佛》的乐曲还让人生出一种庄严沉静的感觉,梵音圣号,送死者的魂灵升天。
谁料今天花钱请来的吹鼓手们,竟在大哥的棺材旁边吹奏起现代流行歌曲,一首接一首,《纤夫的爱》、《九妹》、《大花轿》……
乐曲一响,年轻人就跟着唱,其实是一种喊叫:“妹妹你看着我一个劲地笑,我知道你在等我的大花轿……”叽叽嘎嘎,打打闹闹。叫孝子们还怎么哭?叫来吊孝的人想做个哭的样子都困难。乐曲与治丧的气氛格格不入,让人感到极不舒服,难怪三哥会发火。
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一支蒋姓人家的权威,吹鼓手们怎敢不听,立刻改奏治丧的曲子,围观的老老少少也都跟着散了。二侄子找到我,悄悄地说:“别人不敢张嘴,您得劝劝我三伯,不能管这种事。”
“为什么?这是办丧事,还是办喜事?”
“现在办丧事都是这个样,光吹丧曲子大家不爱听,不爱听来的人就少。咱花钱请乐队不就是图个热闹吗?就得多吹人们喜欢听的,等一会儿还要点歌儿,还要跳舞哪……”
“还要跳舞?在你爹的棺材旁边?”
“对啊,怎么啦?改革开放嘛,怎么城里人倒成了老赶?既然想大办,就要求来的人越多越好,也显得我大舅一家人缘好。”
“不,你爹现在需要的是鬼缘,这样瞎折腾把丧事办成狂欢节,叫你爹的灵魂怎么安息?倒好像是活着的人在庆祝他的死,就不怕他的惩罚吗?”话可以这样说,但侄子们想把他们父亲的丧事办得漂亮、圆满,我和三哥只能成事不能搅事。我对侄子说;“你三伯管得对,你的道理也不错,我把你三伯拉到一个地方去休息,我们一走你就去告诉乐队,随他们的便!”
我把三哥安顿到距治丧现场还有老远的小侄子家歇着,把侄子的话去掉棱角向他学了一遍,劝他眼不见不心烦,耳不听不生气,随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有大事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我会来叫他。
等我再回到大哥身边的时候,乐队前面又围了不少人。围观者这回不是要求乐队吹奏什么歌曲,而是让一个手拿竹板,像女人一样忸怩作态、飞眼吊膀的男人给表演节目。直到有人从“治丧大队部”领来10元钱交到那人手里,他才给自己报幕:
“那我就给老少爷们儿唱一段《奴家十八恨》……”
四周响起了嘻嘻的笑声和拍掌叫好声。我心里骂了一句,这叫什么玩意儿,带色儿也开始上了。
6 哭
在办丧事的整个过程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哭。无哭不为丧。
现在的农村虽然爱赶时髦,把丧事办成了喜怒哀乐的大杂烩,唯独还缺一项——花钱雇人哭丧。因此大哥的丧事自始至终都得靠大哥的亲属们自己哭。
死了亲人要哭,这是很正常的。在亲人刚刚咽气的时候,你怎样哭都不要紧,却不外乎古人在《方言》里所归纳出来的三种方式:哭泣不止、无泪之哭和泣极无声。私人的悲哭一旦有别人介入,有了解劝者和观看者,或者进入正式的治丧程序,哭就变成一种责任,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更多的是一种艺术,一种表演。
记得1977年春天,一向身体很好的父亲突然无疾而终。从天津回家奔丧的人一下火车就开始哭,从火车站到村子还有7里地,中途被接站的人劝住了一会儿,到了村边上又开始哭。那是真哭,是大哭,因为心疼——父亲活得厚道,死得仁义,没有给儿女们添一点麻烦,自己悄没声地干干净净地走了,让儿女们觉得像欠了老人什么。哭起来就动真情,眼泪止不住,见到父亲的遗容会哭,想起跟父亲有关的事情会哭,听任何一个人谈起父亲也会哭……
到了第二天,我和妻子的嗓子都哑了,无论再怎样用力也哭不出声音来。但丧事要办好几天,孝子们无论白天黑夜都要跪在父亲灵前,一有来吊孝的就要陪着大哭,每天早、中、晚,要三次从村北头哭到村南头去报庙。
是孝子们的哭声支撑着治丧的全过程,治丧的悲哀氛围也要靠孝子们的哭声来营造。眼泪流干了还可以遮掩,没有声音可是非常难堪的事,甚至会被乡亲们误会为不孝。如果都像我和妻子,干流泪,干张嘴,不出声,那丧礼就变成了一幕幕哑剧,难免会被外人讥笑。
幸好大哥大嫂,三哥三嫂,侄子侄女,还有一大帮叔伯的兄弟姐妹、孙男嫡女,他们能哭会哭,哭声沉重动情,哭词滔滔不绝。直到治丧的最后高潮,出殡、下葬,他们仍能哭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让帮忙的人和村里看热闹的人无不动容。哭声是一种宣告,宣告死者生前有人疼,死后有人想,生得体面,死得也体面,生得功德圆满,死得无愧无悔。
转眼间就轮到哭我的同辈人了,一年多以前刚哭完了大嫂,现在又哭大哥。第一天哭得挺好,尤其是大哥的两个女儿,“焦肺枯肝,抽肠裂膈”,哭的时间长,且伴有形体动作,或扑天抢地,或捶胸撞头。她们的哭不是干号,是有内容的,一边哭一边说,诸如“我那苦命的爸爸”,“不会享福的爸爸”,“不知道疼自己的爸爸”,等等。总之是将大哥的种种长处当作缺点来抱怨,即便是不相干的人听到两个侄女的哭也会鼻子发酸,陪着掉泪。人要死得风光,就得有女儿。丧事要想办得感人,不能少了女人的哭。
或许由于先火化的缘故,再加上吹鼓手们制造的嘻嘻哈哈的气氛冲淡了应有的哀恸,到第三天出殡的时候,正需要大哭特哭了,孝子们却哭不上去了。或有声无泪,或只摆摆架势走个过场。
现代人是越来越不会哭了。特别是城里人,有些死者儿女一大帮,到需要高潮的时候,却哭不出效果。效果又是给谁看的呢?把内心的悲痛表演给外人看,这悲痛的味道就变了。哭是个人的事情,应该是动于中发乎情,自然放声。
但是,既生而为人,还要讲究“做人”。“做”——就有了表演给别人看的意思,哭也不能不讲究技巧了。
(1998年6月) 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