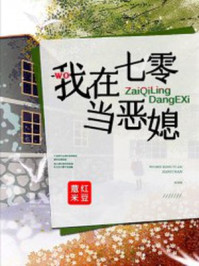§17.告别中条山
武桂兰晚上本来睡得就迟,当她觉着已经睡醒一觉了,发现屋子里的灯仍旧亮着,焦起周披着棉大衣还在埋头写着什么……她看看窗户,外面还一片漆黑,便趴过身子,用手将身体两边的被角掖紧,下巴颏儿垫在枕头上,轻轻地说:“怎么还不睡?”
“马上就完。”焦起周连头也没抬。他的身体遮住了灯光,多半间屋子都陷在一种不稳定的黑影里。武桂兰心疼:“世上的活儿是干不完的,我们的岁数都不小了,哪能这么拼哪!”
“完啦完啦……”焦起周放下笔,站起身子。屋子猛然亮堂了,刚才被挡在黑影里的武桂兰,被光亮刺激得眯起了眼睛。焦起周搓着两只手,边搓边放到嘴边哈着气,眼睛却还盯着桌子上刚刚写好的东西,神情甚是得意。
武桂兰催促他:“快睡吧!”
焦起周侧脸看看武桂兰,白天绾在脑后的发髻披散下来,睡眼惺忪,慵懒而绵软。他弯下腰,用两只冷手捧住她的脸。武桂兰激灵一下子睁开眼睛,盹儿也醒了,小声嗔道:“老没正形!”
焦起周嘻嘻笑着,把一张大纸拿到床边,飞快地脱光衣服钻进被窝,抖抖索索地抱住武桂兰温热的身子。武桂兰提醒他还没有关灯呢。他说再等一会儿,便将身子也趴转过来,左手搂着武桂兰的后背,右手伸出被窝拿过那张大纸:“你看,我把咱的新医院设计出来了。”
四开的道林纸上画着一片房子,有楼房,有平房。焦起周给妻子讲解:“正面这是门诊楼,你看样式如何?不错吧?先盖两层,地基要打得能够承受住五层的,将来儿女把医院干大了,可以再往上加高。穿过门诊楼进入院子,左边是住院部,一拉溜十四间平房。右边是职工住宅区。后面又是一栋两层小楼,是我们自己的住房。二楼是卧室,一楼是车库、药库、厨房……请你审核。”
武桂兰的眼睛并没有看图纸,却歪转脸盯着丈夫:“你什么时候又学会设计房子了?”焦起周颇为自得:“逼的,人被逼急了没有不会的。我们打算花多少钱,想盖个什么样的医院,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画出这么一个大概其的样子,明天交给工程局的设计队,花点钱就给你绘出标准的施工图来了……”
他讲得兴致勃勃,却忽然发觉武桂兰并没有认真听,看着他的眼神闪烁出一种渴念,一种诱人的风情。他的心也飘忽起来,身体开始发热,泛起一种饥渴,一种需要。双手把桂兰的身子扳到自己怀里,轻轻地亲着她的眼睛、她的鼻子、她的耳朵,嘴里还喃喃地胡数六数:“老头子正在干活儿,你却用一副睡美人儿的伎俩撩拨得他心猿意马……”
桂兰心里也痒痒酥酥,十分惬意,声音像夜一样温柔:“我是美人儿的妈了。”
“要不美人儿的爸怎会这么喜欢你呢!”
“你还没有关灯哪!”
“不关,我要看着你。结婚几十年,都是黑灯瞎火地干好事,对不起我的小美人儿……的妈!”
“你忙了一天,夜里又没睡,不要命啦?”
“你就是我的命,这时候有你我就有命……”
“怎么越老越馋,越老越厉害了?”
“这要怪你,谁叫你越老越有味儿,越勾人家的魂儿!”
“大坏蛋……”武桂兰的嘴被一团灼热的东西堵住,身体被丈夫的两条臂膀拼命往他的身体上拉,恨不得将自己的身子揉进他的体内。呼一下如烈火添油,她的身子随即也燃烧起来,在扭动中她被压住了,极其自然,又异乎寻常地疯狂猛烈……
焦起周很快就睡着了。武桂兰仍旧没有关灯,她细细地端详着丈夫的睡容,脸上还挂着笑,显得很满足,很自豪……这张脸她非常熟悉,此时却有点陌生。
她在枕席之上是良妻,行这种夫妇间的好事本是轻车熟路,奇怪的是她感觉越来越好,或者说是起周让她越来感觉越好……自从来运城后,起周渐渐强大而自信了。以前家里的大事小情,她都得拿一多半的主意,起周习惯于依赖她。现在就不同了,她只管给人看病,他才是院长,对内对外他说了算,有了威严,有了力量。就说要建新医院这么大的事,也没有用她操太多的心。越是这样,他对她倒越好了,她是他夜晚最安全舒适的停靠站,又能不断挑起他的欲望。
她是那种细腻敏感型的人,身体格外要受精神的支配,精神差一点身体都有反应。随着起周的变化,她精神上的压力轻多了,精神放松,身体也就越来越充实……这样的感觉真好。看来女人的福气就是自己的男人能扛得起家,而男人的兴奋剂则是权力和事业。
这一段时间焦起周就像中了魔一样,他心里想着的事就非得办成不可,不办成就跟心里有块病似的。他认定要自己建个医院,就怎么想怎么都觉得划算。现在的这个医院,虽然条件也不错,但终究不是自己的,要受制于人。人家乐意租给你你就可以用着,人家想赶你走你就得乖乖地搬家。特别是主管单位的头头经常换,换一个头头一套章法,说了不算,算的不说,谁能受得了?花钱租房子还得看人家的脸子,接长不短地得去走动走动,烧烧香上上供,又何苦来呢?趁着眼下地皮便宜,到处都有找不到活儿干的工程队,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小医院盖起来。它将永远属于自己,可以传辈,一劳永逸地再不为房子问题看别人脸色受别人气了!
他拉上三弟斌丹,看地,买地,找工程队商量价格,选建筑材料,找银行贷款……眼下的银行可真叫“人民”银行,贷款太简单了,你只要提出项目——有的人不想贷款银行还上赶着贷——贷多贷少全凭你自己一句话。何况焦起周还拿着一张副专员王尔品批的字条,自然就更省事了。但他和斌丹都是本分人,不敢多贷,用多少贷多少……每次焦起周从外边回来,都像讲故事一样说给她听。
她渐渐地学会了分享男人的智慧和快乐。当然,有时也难免会有些挫折和焦虑……焦起周睡得很沉,还忽高忽低地打起了小呼噜。
武桂兰笑了,越老越不添好毛病,年轻的时候睡觉死,倒不打呼,到老了睡觉轻了,却想起来就呼噜那么几声。她用手指轻轻地抚摩着起周的下巴、脸颊、眉毛……自己的眼皮也越来越沉,她伸出手关了灯,将身体扎进丈夫的怀里,感受着他呼吸的节奏,一会儿也跟着沉沉睡去。
人还觉得很冷呢,可树梢全都绿了,干工程就得狠狠地抓住短脖子春天。
新医院已经破土动工,焦起周不可能经常盯在工地上,只能一早一晚或有事的时候到工地上看一看。因此他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经常守在工地上,紧紧地盯住工程进度和质量,要不他哪能放心?医院里谁能干得了这件事呢?他想到了郝武长,不敢说他多么靠得住,至少还算个自己人,而且是医院里唯一的一个大闲人,于是就让他专门负责督促新医院的施工。
“负责督促”这四个字格外对郝武长的胃口,他早就盼着要“负责”点什么,要“督促”点什么了。许久以来他肚子里就憋着气,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焦家的人看看,建新医院恰巧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焦起周干不了这种活儿,武桂兰也不行,他那些弟弟、侄女们更甭提,只有他郝武长才能把新医院建起来。要想能镇唬得住藏污纳垢的包工队,就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行。他嘴损,多难听的话也说得出口,多脏的话也骂得出口,说翻脸就翻脸,说返工就得返工,他敢耍混混拼命,别人行吗?
可是,开工好多天了,工程全都铺拉开了,医院却还没有给施工单位拨款。施工队队长几次三番地找到焦起周,他就让郝武长找斌丹,按合同把工程款划拨过去。
郝武长大模大样地摆摆手:“别着急,啥时候给钱,一次给多少,都得听我的。”
焦起周更关心的是医院的工程质量:“咱跟人家是订了合同的,你不给钱人家能给你好好干活儿吗?”
“正相反,现在的人心太坏,拿到钱就不好好干活儿了,工程出了问题你也治不了他了!”郝武长居然说出了一通相反的理由,且显得胸有成竹,“就是喂狗,不还得要会喂嘛,要在它正饿的时候喂,它就会感激你、听你的。”
这家伙,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
但他说的似乎也有那么一点道理,既然让他负责这件事,那就先按他的意见试试。郝武长对施工队长竟敢越过他直接去找焦起周,心里窝着火。好啊,放着眼前的真佛不拜去拜假佛!他必须得找茬儿树立一下自己的权威,也好让施工队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要想对现在的施工质量找漏洞那还不容易吗?他选择了一个刚刚上班,人马最齐备的时候,站在地基沟的边上嚷开了:“停下,都给我停下!你们干的这是人活儿吗?”
“你是谁呀?工地上这么乱,施工的人还真没拿他当棵菜。”
“我看谁还敢不停下?你们干了多少最后都得给我拆了!”郝武长抡着铁锨跳到地基沟里,工人们想停也得停,不想停也得停了:“我是甲方的全权代表,快把你们队长找来!”
队长慢腾腾侧歪着肩膀,迈着方步过来了,矮个子,小骨胎,脑袋溜尖,一看就不是个善类。不然像他这样一副身板怎么能降得住一个鱼龙混杂的包工队!
工人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儿瞪着郝武长,有的拿着瓦刀,有的扶着铁锨,有的手里攥着半截钢筋……横的,恶的,蔫的,坏的,神头鬼脸,歪瓜裂枣,全都不怀好意地往郝武长这边凑合。
施工队长一副满不在乎、处变不惊的样子,故意不看郝武长,尖着嗓子问:“是谁让停工啊?”
“我!”郝武长跳上沟沿,弓着腰低着头盯视着队长。
“怎么啦?”
“你自己看。”
“我看不出有什么毛病啊?”
“哦,那就是你有毛病啦!”
“你这是怎么说话哪?”
“这样说话还是好的哪!你不会干人活儿,还想听人话吗?”郝武长声音瘆人,话也来得赶劲,把工程队长给噎住了,也许是他那阴毒的眼光让对方有所顾忌,不敢硬顶。其实毛病出在哪儿队长心里跟明镜似的,是他下的令,他能不清楚吗?郝武长也知道他装蒜,却就是不挑破,非逼他自己承认不可。
僵持了好一阵子,队长还想装傻:“是不是防潮层短了一点?”
“一点?三十公分!人长矮了三十公分就是残废,何况这是医院!”郝武长故意用眼睛上上下下地打量工程队长的身材,“将来让病人住在潮房子里,你们可是缺了八辈子大德了,绝不会有好儿!”
“你们的资金不到位,我垫不起这么多钱。”
“那就偷工减料?你们干的活儿这么臭,我能给你们钱吗?”郝武长拍拍自己的胸口,“钱就在我手里,黄不了你的,不信到老医院去看看,看病的排长队,每天少说也得收个几十张买药的汇款单,不光是国内的,还有美元、日元。再不够还有银行顶着,王专员的批条压在那儿,银行上赶着要贷给我款。”
“既然这样,那就先给我们打过来一部分。”
“不行,我信不过你们。我后边还有三个工程队盯着这活儿呢,他们的条件都是先垫付一半的工程款,等房子盖得有眉目了,甲方满意了再付款。”
工程队长知道碰上硬碴子了,开始缓和口气:“别呀,我们跟焦院长是订了合同的。”
“合同里有你们弄虚作假欺骗主家这一条吗?凭这一条我就可以废了合同,让你们这些天的人力物力全白费!”
“别别别,”队长惶遽,马上赔笑,然后吆喝他的工人,“全部返工,今后谁要再玩儿花活给我惹祸,我就叫谁滚蛋!”
队长掏出香烟递到郝武长眼前,郝武长阴沉着脸没有接。队长又觍着脸问:“您老贵姓?”
“免贵姓郝,焦院长是我岳父,我在医院专门负责基建,所有修修建建的项目都在我手里。”
队长按常规推理:“哦,您老是基建科的郝科长,失敬,失敬。”
郝武长未作更正,只是用别的话岔开了:“我岳父找你们的时候我正好外出没在医院,你们是不是欺负他老人家是知识分子,好糊弄?告诉你,我可是干包工队出身。你们这套花活我早就不愿意玩儿啦,现在是甲方市场,活儿少,干工程的人多,你光想糊弄人家,人家就再去找别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呀?”
“哎呀,老前辈啦!”队长再次敬烟,郝武长就没有拒绝。一看有门儿,那队长又紧跟着说:“郝科长,你看快到中午了,咱们一起吃顿便饭,请你务必不要推辞!”
刚才郝武长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实在镇唬不住,今天还真得出点血。有时在生活中掀起点血腥是很管用的,对自己这种死眉塌眼的日子也才能有所刺激。这个耗子模样的队长既然已经服软了,他也就借坡下驴,故意皱着眉心拿捏着说:“我知道你的意思,这饭不是好吃的,先套住点感情,然后就要钱,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不是得从我的口袋里出。那就不要太破费,在附近找个小馆儿就行。”
“哪能呢!”施工队长打岔,又喊上了几个工头、班长式的骨干人物,多几个人跟郝武长套上关系,将来在施工中也会方便些。有个工头凑到队长身边说:“苏队,一会儿你不得回家看看吗?”
队长阴沉着脸没有吱声。郝武长不高兴地问:“你有事啊?有事干啥还非要拉我呢?”队长赶忙解释:“郝科长,你别误会……咳,我也不瞒你,我的大闺女昨天离家出走了,他们是想让我回去看看有什么消息没有。”
“哦,还有这事……”郝武长看见两个工人抬着一根木头走过来,他灵机一动高声说道:“你不用去找了,你女儿两天内必定会回来。”
队长疑惑:“你怎么知道?”
郝武长卖个关子:“你抬头往前边看,看见了什么?”
“不就是两个人正在抬木头嘛!”
“这就行啦,一会儿到饭馆里告诉你。”
这群人走进马路边上的馆子,落座之后,施工队的人就急不可耐地要叫郝武长说出队长女儿必定会回来的根据,如果他说不出道理,就证明是个大白话蛋。
郝武长用手指蘸着茶水在饭桌上写了繁体的“来”字:“你们知道这个繁体的‘來’字是什么意思吗?中间一个木字,一边一个人,两个人抬一木是什么?是‘来’。不早不晚,偏巧就在我们正谈苏队闺女的时候,这两个人正抬着木头过来,不是告诉我他的闺女要回来吗?两天内你的闺女要是回不来,我去给你找回来!”
“哎哟,郝科长真有学问!”
“你是高人,我先得谢谢你啦!”
这顿饭本来就是以郝武长为中心,施工队的人都捧着他说,他也就毫不客气地抡起来大侃特侃:“去年春节前,我去看望一个当官儿的朋友,给他送礼的人不少,送不起重礼的就送鱼。我看到一个人手里提着两条活鱼,后面跟着一条小哈巴狗,就吓了一大跳,赶紧告诉他注意老婆的安全,过年期间千万不要叫他老婆外出。他不听,大年初二他老婆回娘家,走在半道儿就被汽车撞死了。”
其他人自然又是一番惊讶。
郝武长又用茶水在桌子上写了个“哭”字。然后解释说:“两条鱼张着口,下面一条狗,狗就是犬,上面两个口,下面一个犬,不是‘哭’是什么?你们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不断定我那个朋友死,而是说他老婆死呢?因为还有好多人给他送鱼,众鱼,就是鳏寡孤独的‘鳏’,说明是他要死老婆当鳏夫……”
不知真假,饭桌上的人都做出一副被蒙住的样子,纷纷向他敬酒。
他越发地得意了:“名字就是命运,盖了宣武门宣统皇帝完蛋,有了崇文门崇祯皇上死。‘文化大革命’中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打倒刘邓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只留下邓小平逃活命,刘少奇和陶铸都死了。‘荣毅仁’这个名字起得更好,那时候别的资本家都完蛋了,就容下了他一个……”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包工队的人却好像被唬住了。
其实,他哪里有这么大学问,全是到运城之后,整天泡在小酒馆里东一耳朵西一耳朵听来的。他小子还真聪明,就有这本事,过耳不忘。
有人又问:“郝科长,你这个名字有什么讲头?”
郝武长晃悠着脑袋:“我只要好武就能长寿,武运长久。所以我从小就练武术,眼下在大街上要是碰上三个五个的小流氓不够我打的。焦院长的大女儿,要医术有医术,要人品有人品,一看见我这个武人一下子就爱上了,谁能说这不是命!”
饭桌上都有了几分酒意的男人们发出一片叫好声:“郝科长,你真是好命呀!”
“来,咱们敬郝头儿三杯!”
郝武长喝得眼睛有点红了,越发地口无遮拦:“刚才净给你们讲文的了,你们不一定听得懂,现在给你们说点荤的,出几个谜语让你们猜。男人腿长——打一样食品。”
别说这还不像是谜语,即便是正规的谜语,这帮人也不像是能猜谜语的人,就都说猜不着,让郝武长快点说出谜底。
他得意洋洋:“男人腿长——蛋糕(高)啊!”
饭馆里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他又说:“男人的裤头——打一种外国饮料:雀巢。女人的乳罩——打一道菜:扣肉!”
酒喝到最后,郝武长已经和那个施工队长称兄道弟了。是施工队的人把他扶出了餐馆,他走路虽已脚底下发飘,头脑却还是清醒的,指着队长说:“你小子够鬼的,这就对了,狗急着要去的地方是它吃饱过的地方。你不给别人好处,还指望别人会对你好吗?”
施工队的人一愣,这是什么话!谁是狗?他是狗,还是骂我们是狗?请他又吃又喝最后还得挨他的骂!
从此,郝武长抽烟要由施工队供给,还要三天两头地要请他到饭馆撮上一顿。酒,不必是太好的,菜也用不着太讲究,郝武长本身就不是讲究人,也没见过太大的场面。但他喜欢这种架势,大家都哄着他、抬着他,无论心里想笑不想笑,都得向他赔着点笑。
郝武长成了医院常驻工地的真正代表。
原来他狗屁不是还能凭空使出三五分权力,现在真的有了三五分权力便使足了十分,在工地上吆五喝六,如鱼得水,俨然一个“大拿”。干出的活儿没有他点头不算合格,不追着屁股讨他的好就拿不到钱,施工队的人都知道他是顺毛驴,很少敢得罪他。
尽管如此,郝武长仍然在工地拿捏得住,因为他觉得自己抽的也好,喝的吃的也好,都是施工队从医院的工程上赚的钱,他并不认为亏欠了施工队什么,在要求施工质量上还真没有打马虎眼。
地基打好后大墙一露地面,就一天一个样,焦起周看着也高兴,翁婿关系进入一个黄金时期。
初夏,中条山里不冷不热,万木葱茏。这绿色宝库也是恋人的天堂。
焦安国利用歇班的日子又拉上欣运上山采药,他显得有些伤感,净向欣运提一些古怪的问题:“这大山里多好哇,如果我们两个人就在这山里终其一生,你乐意吗?”
“住在哪儿?吃什么?”欣运笑里含情,“你一进山就浪漫起来了,是不是想当野人?”
焦安国忽然叹了口气:“咳,咱哪儿有浪漫的本钱哟!”
欣运略感诧异:“浪漫只是一个人的感觉,还要什么本钱?连最完美的幸福也纯粹都是自己的感觉。”
“怕就怕感觉错了。”
姑娘眨了他一眼,心里暗自嗟叹。
接近中午的时候,他们来到一座荒弃的小庙跟前。焦安国不胜惊奇:“我还以为中条山已经被我爬遍了呢,想不到这儿还藏着一座庙!”
他估计在“文革”之前这庙里可能还有香火,庙前有一株能够几个人合抱的大树,铁骨青枝,安稳如铸。小庙极其破败,庙顶上有个大窟窿,庙堂里长着野草,神像已不知去向。只有庙门还相对显得稍微囫囵一点,尚能依稀辨认出两旁柱子上的字:
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
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
欣运问:“这是什么意思?”
“不很明白……”安国犹豫着,“佛家的禅机我们凡夫俗子怎么能参得透?”
“这字是佛写的还是凡人写的?”
“可以肯定地说这字是人刻上去的,却有不凡的智慧和气度。”
“神的存在真是不可思议。”
“如果没有神的存在就更不可思议。”焦安国放下肩上的药筐,“好啦,我们就在这儿歇一会儿,然后吃午饭,也来个见了便坐,坐下便吃。”
他们在大树底下的石头上坐下。
山间空阔宁静,灵气盘结,清新的空气饱含水分,庙后似有水流淙淙之声传来。焦安国从背囊里拿出毛巾,对欣运说:“你在这儿等着,附近有山泉,我去找一找。”
他转到庙后,见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色,千崖万壑,林涛吼响。他上攀不到五十米,便找到了一股清流,漱了口,洗了脸,顿时一阵清爽。最后又把毛巾蘸饱了水,双手捧回来,一点点拧到欣运的脸上。欣运一边用手撩着泉水拍打着自己的脸,一边嚷嚷着:“好凉,好凉,真舒服!”
不想,安国把毛巾里的最后一点凉水突然全拧到她的后脖领子里了。姑娘刺棱一下子站起来,夺过毛巾骂道:“你个缺德鬼!”
安国忘情地盯着姑娘那迷人的面庞问道:“美吧?”
“真美。”
两个人相互使了个逗人的眼色。安国说:“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上中条山采药了!”说完便观察欣运的神色,她却没有丝毫的不安或惊讶,就好像她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一样,静静地等待安国自己说下去。他尽力想读懂她目光中所传递出的信息的确切含意,没有再继续说什么,从口袋里掏出父母的来信递过去。
卓欣运读完信仰起脸,眼睛里依然流露着平静的笑意:“你可真沉得住气,这信来了有一个多星期啦!”
“因为我还没有拿准主意,自己还没有想好,讲出来不是白给你添烦吗?最难的就是做出选择呀!”
“现在已经做出来了吗?”姑娘的眼睛里闪烁出惊人的聪慧。
“就在刚才,我忽然觉得一阵轻松,我想是做出了决定。”两个人相互凝眸许久,还是焦安国感到好奇:“你好像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也不紧张不犯难。”
“做决定的是你又不是我,我有什么好嘀咕的?”
“啊?”焦安国大惑,“最难的应该是你呀,你好不容易顶替父亲在矿上有了一个铁饭碗,现在又要辞掉它跟着我去运城,跟你母亲怎么说呀?跟你的两个弟弟怎么说呀?要早知这样,就不如让你的一个弟弟来顶替了!还有矿上的人,会怎么议论我们俩?人家都是削尖了脑袋想挤到矿上来,我们却要辞职,人家说我傻,那是没有办法的事,父母之命不能违。让人家都说你傻,我可受不了。”
“傻人有傻福,人活着能落个傻名声可不容易。也只有在许多人都认为你是傻子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是最聪明的。”
“你真的就一点顾虑都没有?我可是要对你的一生负责呀!”
卓欣运的目光霍地一闪:“你不必对我负责,你只要对自己负责好,就是对我负责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呆子,我只做过一个决定,那就是跟着你。其他的事就不用我操心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好我跟着好,你坏我跟着坏。”
“你不用回临汾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吗?”
欣运摆摆头:“既然你受佛的指点拿定了主意,我现在也告诉你一句带点佛性的话,‘十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我跟你有百世修行的缘分,还犯什么愁啊?”
卓欣运两眼幽黑,温情脉脉。
焦安国兴奋得有点透不过气来,伸出一只臂膀把姑娘揽进怀里,在她耳边悄悄说:“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中条山,是这座山培育了我们两个人的情感。真想现在就跟你拜堂成亲,成全了我们的好事。如果你能在青山绿林中怀孕,将来一定能生个非常漂亮又有灵气的孩子。”
“嘿嘿,你就不怕亵渎了大自然,还有这不可思议的无处不在的神灵?”
欣运这样说着,身体却在他的抚摩下变得灵动起来,火烫的双唇也开始回应着他的热吻…… 蒋子龙文集.4,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