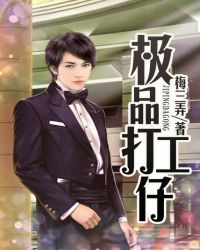“海怪”——戴喜东
“辽精海怪,×××是大脑袋。”——这首民谚似乎在辽宁流传有一个世纪了。其意是:辽阳人精,海城人怪,×××人的脑袋大。在东北话里脑袋大并不是聪明的意思,恰恰相反是讽喻呆笨。故隐去真名,免得伤害那里人的情感,甚或引起诉讼。
令人不解的是,此谚竟成了这些地方的一种宿命,不知过去多少年了,“精”的总是精,“怪”的还在怪,“大脑袋”的地方似乎也仍未摘掉脑袋大的帽子。在这三个地区里让我挑选采访对象,我选择了海城人的“怪”。
中国近三十年来,连续发生过两次地震的地方只有海城,只这一点就够怪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特立独行的海城人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他既是英雄又爱美人,口碑还挺好;既发动西安事变扣住蒋介石,又亲自送蒋回南京;他是现代世界上被关押时间最长的将领,又异乎寻常的长寿,把关押他的人都熬死了自己才走;带兵作战,杀人难免,最后却皈依基督……我想看看当今的海城人还能怪到哪里去?
不想海城之怪立即给我一个下马威,那年十一月三十日我从天津乘船到大连,正准备登车赶往海城,媒体报道海城刚刚发生了5.6级地震。专程来大连接我的海城朋友问我还去不去?如果害怕可以住到鞍山。
一个“怕”我又怎么能说得出口?
但心里却不免有点嘀咕,也有些丧气,这地震莫不是冲着我来的?是想提醒我,还是要阻拦我?虽然脑子里有这许多想法,嘴上却回答得很干脆:我是经历过7.8级唐山大地震的,难道还怕你们的5.6吗?
车进海城,仍能感受到几天前那场令关里人羡慕的大暴雪的气韵:四野一片洁白,天地清澈透亮,没有一丝地震的痕迹,更看不出震后的慌乱。进入“三鱼(泵业公司)王国”,简直称得上是一片喜气洋洋了……喜气是从两幢漂亮的住宅大楼里散发出来的,人们进进出出,兴奋而又忙碌,有人拉家带口一块来看新房,有人已经在往楼里搬运新家具,还有人正在装修新居,相互串门观摩,吸收别人的设计优点,或暗暗较劲要装修得比邻居更豪华……这竟是三鱼公司的职工公寓,即使把这样的楼房放到北京、天津,也算是不错的,公司却以每平方米低于五百元的成本价卖给职工,职工花四五万元就能买到一套上百平方米的房子。就是这点钱,还可以向公司借,不要利息,将来一点点从工资中扣除。
在房价高得吓人的今天,竟还有这么便宜的事!这哪看得出是刚刚发生过地震的,我来到了地震中心,对地震的那点惊惧感反而消失了。三鱼公司的创始人戴喜东,把我接进他的办公室,我说:“全国都知道你们这儿又发生了地震,可你们倒像没事一样。”
戴喜东全不在意:“现在不是三十多年以前了,我的厂房、宿舍都是用钢筋水泥堆起来的,这点地震就像给我挠痒痒,怎还把它当回事?即便再有特大地震把房子震倒了,它也不会散架,人在里面保证不会有事。”
刚一见面,正好借着谈地震让交谈自然流畅起来。我又问:“六十年代那次大地震的时候你在哪儿?”他看着我,嘴上在回答我的问题,心里好像在想别的事情:“那年我还住在土垒的平房里,地震的时候就像坐在疯马拉的木轮车上,整个人被颠起老高,四周就像山崩地裂。闪电是弯角的,铁硬死拐,常常有两个闪电同时出现,尖端共咬着一个火球,如神话中的二龙戏珠。那时孩子都还小,我倒是越遇到事胆子越大,就大声叫喊着地震了、地震了,还让他们别慌,快点往外跑。我先把小女儿抱到房子外面,随后大女儿自己跑了出来,紧跟着妻子抱着小儿子也出来了,我二次进屋把母亲拉出来,赶紧反身进去再把棉被抱出来。一看房子还没倒,又跑回去把孩子们的衣服抢出来,不然震不死也会冻坏的……”
到海城来似乎就不能不谈地震,我一边听着他讲地震,一边打量他的办公室:房子很大,但满满当当,杂乱无章。墙角、墙边堆放着一摞摞一包包的古版线装书,摆在最浮头的有汲古阁的刻本,武英殿的版书,清朝第一版的《康熙字典》、《石头记》等。窗台上放满古里古怪的瓷器、玉器,三面墙上都挂着古画,一幅挨一幅,有的一个钉子上挂了两三幅,一幅压一幅。地上还放着几个未打开的大包,里面也装满古玩。办公桌后面摆着两个直通到房顶的大书架,上面码满现代书籍,可大致分四大类:经营管理、历史、人物传记、艺术鉴赏工具书,如:《文物精华大辞典》、《现代美术全集》等。
这哪像是一个名牌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办公室,更像个杂乱的博物馆仓库。我们正说着话,一个年轻的文物商走进来,手里拉着一个大箱子,肩上还背着个大包,打开来全是字画。戴喜东拿起放大镜开始鉴定这些字画,绝大多数都是假的,他有根有据地说出自己的见解,指出假在哪里。
在这个过程中,文物商不时地从桌上抽出戴喜东的中华烟放在嘴上点着……这个年轻人是专门从丹东赶过来推销这些假字画的。戴喜东像检验产品质量一样,把假的剔除,凡是他想要的东西从不讨价还价,都是先让对方出价,然后在原价上再给加一百元,到最后又塞给小伙子二百元的路费,还把那盒中华烟也递过去让他路上吸。原来他在低头验画的时候并没有忽略文物商人的烟瘾。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很难相信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会对收藏古玩痴迷到这般程度。由此可见,现代海城人也的确有点怪。戴喜东办公室里的这些古玩,还只是他全部收藏品的一个零头,他见我对他的爱好过于大惊小怪了,便领我走进一所废弃的旧中学,在十几个教室里都堆满他购买的古书、古字画以及瓷器和古家具。光是线装书就装满两间教室,仅油画就有一千多幅。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癖好,原因却很简单:当年爱读书的时候没有钱买书,发达以后便拼命买书,后来扩而大之又开始收藏各种古代文物……如今搞到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怪得有点离奇?
我心里生出一个疑问,压了半天没有压住,还是说了出来:“你该不会玩物丧志吧?收藏古玩是无底洞,纵然你很有钱就能禁得住这样折腾吗?被创业者自己折腾垮的企业我可是见得太多了……”
他大度地一笑:“这没有多少钱,总共也不超过二百万,有不少是别人拿来抵账的,我真正花大钱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呢。”其实,我很快就知道了,当地人背后喜欢称他“圣人”,而有“圣人”的地方必有诸多传说……我在采访中先听到了他砸饭盒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他买下镇办电修厂,成立三鱼泵业公司的时候,曾搞了一次“砸饭盒运动”。饭盒——工人上班的必备之物,从“张大帅”时代工人上班就要夹个饭盒,日本鬼子来了工人仍然要带着饭盒上班,国民党当政更是不能没有饭盒,共产党让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了,上班还是少不了一个饭盒,家里做上顿得想着下顿,带到厂里却都成了剩饭剩菜。一人一个饭盒,在车间里到处乱放,各车间都得安上大蒸锅以解决饭盒加热的问题……戴喜东下令,谁也不许带饭盒进厂,见一个砸一个,上班期间由公司管饭。
听到这个决定,跟他贴近的人都吓了一大跳,立刻给他算了一笔账:公司里许多车间都是体力劳动,每个工人每顿饭不会少于六两米,一千五百人一天就净吃掉八百多斤大米,相当一亩高产田的产量,再加上肉呀菜呀,一年少说也得贴进去一百二十多万元,对一个私人企业来说,这可不是小数目!眼下的风气是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你怎么可以倒过来,砸烂小饭盒,重建大锅饭?
戴喜东不为所动,他才是“三鱼”的主宰,有一种令人敬畏又使人平和的力量。他喜欢的格言是:“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在砸饭盒之前他显然是仔细思虑过了,他经过思虑后决定的事不能更改。
于是,“三鱼”的职工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吃下来了。白吃白喝不怕,怕的是乱糟蹋,就因为不花自己的钱,有不少人眼大肚子小,盛的多吃的少,常常将整碗的白饭、整个的馒头,连同还剩下小半碗的菜,也不管里面有鱼还是有肉随手就倒掉了!别人倒着都不心疼,戴喜东看得心疼的慌,他疼的不光是钱粮,还有这人心的残缺,你对他这么好,他靠着这个企业吃饭赚钱,却仍然不把企业当成自己的……还是毛主席说得对,重要的是教育农民。
戴喜东小的时候,每天要起五更到邻村去上学,黑灯瞎火了才能赶回家,现在该结束村上无学校的历史了,他出资给村里建起了一所小学,名为“弘义书院”。不久又出资六百万元,给镇中学建了新大楼。
好事开了头就没个完,干脆好事做到底:海城有些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报销不了医药费,去年底,戴喜东拿出几万元为这些老人报账。然后又花了十几万元资助一些老同志去旅游,临行前竟然还向老同志提出“四要一不”:“要住好、吃好、玩好、休息好,不要光想着为我省钱。”
三鱼公司的干部就更美了,国内玩遍了,就轮流出国旅游,每人还补贴三百美元到五百美元。一九九九年公司花二百多万元为全体职工购买了人身养老保险。他支援灾区就更简单,给红十字会寄去一大笔钱,自己并不到电视晚会的现场登台亮相,也不让公开自己的姓名。他还因处理得当和抢救及时,救活过四五个因陷于绝境自杀或发生意外事故的外地人性命……
像戴喜东这样为别人花钱如流水的人,当今生活中还有多少呢?这大概是他被称为“圣人”的主要原因。
一桩桩一件件,办的都是好事,却又有点奇特,因此也有人把他当成“冤大头”,天天要他出钱资助的人挤破了门槛……原来善门好开不好闭,有些莫名其妙的人打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借口来找他要钱。诸如反腐败基金、厂长经理读书会、计划生育周、世界卫生月……
反腐败还要基金?厂长经理们能凑到一块去读书吗?中国一年之中有近四百个节日,如果这个节那个日的都来找他要钱,打死他也应付不过来。给了张三,李四又会找上来,还有个完吗?有些不该给的钱如果给了,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但有时,他磨破了嘴皮子也不管用,万般无奈就只有耍肉头阵:“我不是拿不出这笔钱,而是不能拿,你们如果实在不甘心就自己拿吧,看我这里什么东西值钱就拿走,要不就抢,反正从我嘴里不能说出那个给字。”
为此,他得罪的人也许比感谢他的人还要多。
说也怪,尽管他这么折腾,三鱼公司却越干越大,财源滚滚,这其中的奥妙比他大手大脚地花钱更让我感到惊奇。我端详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花白短发,面色红润,一身青色中式裤褂,脚蹬青布鞋,气度雅博雍容,苍然有智,无论怎样看都难把他跟他眼前的职务联系起来,倒更像个言方行矩的道学先生。这样一个人又怎样把偌大的三鱼公司经营得这么好呢?
我请戴喜东带我下去看工厂——那才是制造和支持他这个“圣人”的地方,他所有资本都来自工厂里的生产,要我相信种种关于他的传说,就得让我看到一个真实的不同凡响的企业。工厂是崭新的,机器设备是新的,甚至连工人也大都是年轻人,给人一种新异的生气。每个车间都整洁有序,各道工序井井有条,“三鱼”明明是个创出了名气的老企业,怎么会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呢?
戴喜东告诉我,他重新为企业设计建造了厂房,刚刚更新了生产设备,所以像个新企业一样。工厂才是他的根本,既然他在别处都敢那么慷慨地花钱,在改造企业上就更不会疼钱。最让我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新厂房包括刚刚落成的新办公楼,竟然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根据需要和自己的心意画出图样,建成自己喜好的样子……
这是个心智奇巧剔透的人,凡是需要的他自己就能干,似乎已经进入了一种随心所欲的境界:他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变成真真切切的现实。有个“工头”模样的人追上我们,向戴喜东汇报,新办公楼的顶部套灰粘不住,抹了三次掉了三次,施工队想先往上面喷一层胶,然后往胶上抹灰。
戴喜东略一沉吟,断然否定了“工头”的建议:“所有化学胶都有污染,其黏度也是有期限的,过不了几年就会爆皮、脱落,我们的房顶还要不要?套灰粘不住是因为太干,你先往上喷水,把表皮喷湿后再抹灰。”
他容貌随和却不失威严,行动缓慢又充满自信。“一喷水就能粘住吗?”干了多半辈子泥瓦匠的“工头”半信半疑地走了。我也有些疑惑,但没有做声,跟着戴喜东又走进铸造车间。车间主任向他反映,新冲天炉的铁水流不出来,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就下了指示:“把炉膛加高,向炉口倾斜三度。”
我一直惦记着想知道他的这些主意灵不灵,在工厂转了大半天之后,回去时又绕到铸造车间,等了一会儿便看到了出炉,铁水被烧得红里泛白,溅着火花一泻而下,欢快顺畅,光芒刺眼。戴喜东不知是看出我对他在技术方面的权威性有怀疑,还是他也想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否会奏效,领着我走进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的新办公楼,顶部套灰的工序已经完成,“工头”欢欣鼓舞地迎过来:“喷水的法子还真灵……”
我不解,戴喜东怎么能对自己企业里的各个环节都无所不通呢?他原本只是个小学教员,一九六二年在举国度荒的中期得了肺结核,被学校辞退后给生产大队看水泵。几年后他便成了当地知名的修水泵、修电机的专家,被四村八乡请来请去,人们先是称他为“能人”,当他把事业干大了并做了不少好事,就又被人们称为“圣人”。有些好事办得不被人理解,很容易又成了“怪人”。最后还是回到了一个“怪”字上。
做人也是一种艺术,能达到“怪”也许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我们回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他直奔自己的办公桌,桌上放着几张表格,他逐张地看了一遍,嘴里轻声嘟囔:“今天进账一百九十七万元,周转资金还有二百四十万……”我也凑过去看那几张财务报表,这些表格也都是戴喜东自己设计的,将公司一天的生产、销售以及财务状况一目了然地都反映在上面。他抬头看着我说:“这是最低的了,销售旺季每天可进账二百多万元,公司每天的周转资金是三百万,如果低于二百万,警灯就会亮。”
我似乎对他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别看他被古版书和古字画包围着,买古玩、看古书、陪朋友参观聊天,在他脑子里真正惦记着的是公司的经营情况,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不由脱口说道:“你是外表大大咧咧,好像花的比挣的多,其实内存精明,心里有本大账。”
他调子很低:“干企业不算账怎么行?我花得多是因为我觉得该花。一个人的资产超过千万就应该属于社会了,必须不断地回报社会。该我想的我尽量想周到,该我做的我尽量做周全,可你知道好心不得好报的古训吗?别误会,不是我自己希望得到什么报答……”
我问他,在海城像他这样的富翁多不多?他说资产高过他的至少有百家以上。
我大为惊异:“海城人到底是怪啊,还是富啊?”他解释说:“海城人的怪跟富有关。海城人的富也跟怪有关。自古海城人的经济意识就很强,重商轻官,其他地方的人读书是为了做官,海城人读书是为了经商。所以清朝分配秀才指标的时候都格外卡海城,跟海城相同的地区可以得到二十五个秀才指标,海城却只能有八点五个。那个时候只有考取秀才,将来才有可能当官,当秀才是获取功名的第一步。也许正是由于朝廷在仕途上卡了海城人,才逼得海城人不得不在经商上寻求发展。你到沈阳、鞍山的大街上去看,穿戴时髦的年轻人往往是海城的,在高级服装市场门口的一辆辆奔驰车也大多是海城人的。”
如果富就叫怪,那谁不想怪呢?戴喜东并没有说清楚,海城人是因富才怪呢,还是因怪才富?我倒是发现了戴喜东的另外一怪:时下富翁们都兴养狼狗,雇保镖,建高墙,拉铁网。戴喜东就在“三鱼”职工公寓的二号楼里买了一个门洞,一家大小都住在里面。无论早晚,他一个人出出进进的还从未碰上过想打他坏主意的人。
看来“圣人”能辟邪,吉人自有天佑。
其实,光是对付社会上的要钱大军还不算难,眼下最让戴喜东头疼的还是自己企业里的“世纪病”。由上个世纪传下来的最大的一种病就是平均主义,穷了要搞平均主义,富了也会滋生平均主义。他说:“按目前的分配状况,公司里很快就造就出一批百万富翁,眼前他们每年的收入可达到十五万至二十万,即使是一个中层干部的年薪也有六七万元。来钱太容易,不明不白地发财,就会使私人企业得国营病,重新再吃大锅饭。体现在工作上就是等靠要,挑肥拣瘦,松懈懒散,敷衍塞责,糊弄老总。拿钱多的认为老子该得,拿钱少的心里不平衡。我可不想当什么‘圣人’,也不是慈善家,我的责任就是让自己的企业不停地创造更高的效益。”
从交谈中我感觉到,戴喜东在酝酿着一场变革,想搞一次“凤凰涅槃”——将企业员工身上的坏毛病统统烧掉。同时也能从他的话语中深切地感受到一个被称为“圣人”的成功者的孤独……无论是社会上还是企业中,人的关系永远是个变数。你给大家以很好的福利待遇,发很多的钱,或者让他人永无后顾之忧,却并不能让大家就永远地知足和保持积极上进的干劲,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不能不为企业的未来焦虑……
别人都以为戴喜东已经是一方名人,应该算活得很风光了。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干企业并不是一件风光十足的事,它需要作出无数冒险甚至是看似荒谬的决定,既要决策跟企业生存跟自己的身家性命攸关的大事,又要处理太多细碎的琐事,而且老是寝食不安,很难有真正放松的时候,一步走错很可能就被竞争的激流所击败。这实在是一种劳心伤神的事,且具有让人一旦上瘾就难以自拔的诱惑。
所以,他要收藏线装书和古文物,享受一种与历史和文化的和谐感。这是他生存的需要,是先天的人性所不能免的,借以中和自己的人格,协调自身的矛盾和痛苦。变换心境就是变换生命,沉浸在自己喜欢的故纸堆里,会有一种灵性的抒发,使心胸空蒙灵荡,清洗大脑中的沉积物。戴喜东说,真要能“玩物丧志”倒好了,“玩物”的时候常常想的是企业,触发的是办企业的灵感。
他只有在谈到自己的收藏的时候,脸上才现出顺畅的线条,有了与年龄相符的安详和笑意。这时候我忽然觉得,戴喜东这个“老海城”其实也古怪不到哪里去……
2003年夏 蒋子龙文集.12,人物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