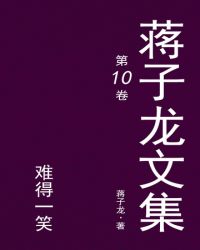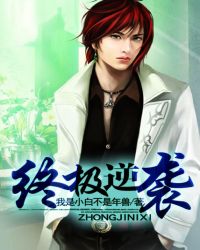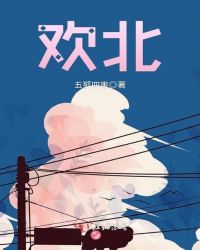§为城市招魂
古希腊哲学家曾说过,幸福的第一要素就是出生在有名的城市。我们的祖先就有过这样的幸运,因中国曾经是世界上城市最发达的国家。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包括唐代的长安、宋代的汴梁和临安、明代的南京、清代的北京,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现在呢?由世界著名旅游杂志《C0NDENAST TRAVELER》评选出的“世界现代新建筑奇观”的排名榜上,没有一座中国建筑。相反,建筑学界倒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一种现代城市病正在蔓延,致使许多中国城市失魂落魄,找不到北。用成都规划设计所所长郭世伟的话说,八十年代,中国在建筑设计规划领域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始了大规模建设,迷失了方向,中国城市在建设中丧失自我,变得很难从外观辨别它的历史和文化了(见《参考消息》2002年10月24日)。那么,这种城市病有哪些症状呢?
病症之一:不研究历史,缺少文化品位,却急功近利、喜新厌故,毁坏了城市文脉。比如北京,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贡献,却把钢铁、化工等大工业都建在上风头,渐渐地污染就开始覆盖全城。
往好里说是某些官员想在自己的任上大有作为,把能看得见抓得住的好事、大事都做完,剧烈地改变城市面貌,不给后人留下空间,企图有口皆碑、功德圆满地被载入史册。结果是拆了建,建了拆,先是建起一片片的“工人新村”、“干打垒”,随后又拆掉“新村”建“大板楼”。现在该拆了板楼建小区,早建的小区又过时了。二〇〇四年初,我见到天津红旗南路东侧和河北大街的旁边,有些刚建成的楼,甚至是所谓别墅式的小楼,还没有住人,就又开始拆掉。前任官员题的字,后任就得铲掉,铲掉前边的后边还照样有人再往上题。所以,我们建了半个多世纪,也拆了半个多世纪,城市就从来没有消停过、干净过,老是尘土飞扬,处于地道战状态。
为什么我们的许多建筑物,落成之日就是落后之时?
真正的繁荣应该是重建多于毁灭,欧洲保护城市早有现成的经验:你想创造政绩建新的,到别处去建,不许毁我老城,它说不定比你那个新的还值得珍惜。像北京的城墙、城楼,当年不动脑子就稀里哗啦地都拆了,现在想起来还令人心痛,追悔莫及。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北京天文馆等一批著名建筑的设计者、九十二岁的张开济老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极力呼吁保持城市的历史命脉。他说第一次到北京,先进入眼帘的是宏伟的东南角楼,角楼上面是碧蓝碧蓝的天空,下面是城墙和城楼,一队骆驼正缓缓行进,真是好一派北国风光!到北京后看了那么多美不胜收的文物古迹,一下子傻了,我这个上海人才头一次晓得我们中国有多么伟大!有这种感觉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有一次我正在天坛欣赏祈年殿,旁边有位外国妇女情不自禁地说:“我能站在这里看上三天三夜也看不厌。”(见2002年12月11日《羊城晚报》)
城市的建筑应该像树的年轮,一圈一圈凝固住不同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要靠它的历史和文化所浸润、所托显。幸好当年还没有连紫金城也一块给拆了,否则,没有故宫了北京还能成其为北京吗?就像埃及,如果没有金字塔也是不可想象的。法国之所以是法国,因为有别处无法比拟的大教堂、博物馆……伦敦引以为荣的则是大本钟、议会大厦、白金汉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等等,几乎都是十八世纪以前的建筑。这些优美的古建筑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历史和文化的熏陶。还有罗马、巴黎、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驰誉世界的名城,其辉煌都无不来自历史文化的投光。就连爱丁堡这样的小城,当你走进去也如同走进了历史的圣殿,它完好地保存着自十一世纪以来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建筑,让人无法不被震撼,不对它充满敬意。也正因为它自身有丰厚的文化氛围,才能连续几十年举办盛大的国际文化节,并把它办成了世界的名牌文化节,成为爱丁堡的象征。甚至连历史短暂的美国,随便走进它的城市,也能感受到强烈的历史感、文化感和地域感。如万国建筑博览会般的芝加哥,彩虹般的金门大桥则是旧金山的历史绶带……这就足以说明,靠历史和文化的长期积淀,培养了城市的精神气质,反映出城市的本质。所以人类文明越是现代化、国家越是发达,就越重视自身的历史。
城市的灵魂,是由当地的历史风俗和地域文化所铸造。甚至可以说,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文化现象。地理风貌、建筑特色、历史遗迹、文化景观、众生心态、市井沉浮,以及生产和交换、扬弃和诱惑、生机勃发的繁衍发展、博大恢宏的无穷蕴藉……都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强势生命。但养育文化的,却是人的心灵。是人的心灵不断对城市加工翻新,心灵是印章,城市不过是印迹。反过来,现代人的心灵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染,也首先来自城市。由此可见,城市丢了魂儿,人的精神就会涣散,城市很可能就将变为卢梭所说的“人类的垃圾堆!”
我们不是经济大国,但至少还是一个历史大国吧?曾经有过悠久而灿烂的文化传统,或许正因为我们的历史太长了,传统资源太丰厚,反而不重视历史。大量的城市建设以失去历史感和砍断文化根脉为代价,换来的是一些不伦不类、半土半洋的玩意儿,甚至是在重复西方几十年前的错误。如果说历史是一个城市的记忆,我们的城市病患的是失忆症,已经到了不能不为之招魂的地步。灵魂散失已经找不回来的,就得考虑重新为自己的城市铸造灵魂。
有人也意识到了这种浅薄,却图省事想在数字上做文章:吹嘘自己的城市已经建城几百年乃至千年了,要劳民伤财地搞一系列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靠大轰大嗡的虚张声势抬高城市知名度。这只会反衬出缺少历史文化的无奈,徒使自己和城市更加尴尬。
病症之二:贪大求多,城市急剧膨胀。实际是一种浮肿,如同抽自己的脸以充胖。
当今世界上有几个国际大都市?获得公认的似乎就只有纽约和伦敦。皆因要成为国际大都市须达到一些约定俗成的指标,并非只靠一个“大”字就行。可只在我们中国,就不知有多少城市都提出要争当国际大都市!似乎只要按中国习惯性的表态方法,敢于“争”,就真的能够当上。有的城市自觉个头已经不小,干脆就自说已经是国际大都市了。反正这种大话又没人跟你较真、跟你对质,自己爱吹什么就吹呗。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当上国际大都市,当上如何,当不上又如何?关键是这种“贪大求洋”的心态。
青岛、大连、天津、上海、成都、重庆……老祖宗给我们的城市留下了多好的名字。可有些人老想在城市名称的前边再加上个“大”字:“大××”、“大××”……听上去像结巴嘴,真不嫌绕舌头。什么都要大,喜欢当老大,城市便像摊煎饼一样漫无节制地向四外扩展。二十年前,我骑着自行车可以很轻松地穿过天津市,无论是从南到北直着穿,还是自东向西地横着过,都不费什么劲。为了买到一件紧缺的东西,骑着自行车在全市转一圈是很自然的事。近二十年里城市人口并未增加一倍,相反,倒有许多国家大企业萎缩和被拆散,可城市的规模却扩大了不止一倍。楼比草长得还快,见缝插针有块空地就盖成房子,时时处处都能感到建筑物对人的挤压和蔑视,空间在缩小,活动受局限,城市像注水的肉一样膨胀起来,可惜这种膨胀不过是水肿。
不仅城市要大,广场也要大,道路更要宽大,而且越宽越不嫌宽。尽管中国人多地少,却恨不得把所有的土地都变成通衢大道,似乎只要大道通畅,大家就都能奔小康了。仅是从天津市区到塘沽,就有两条高速公路、一条轻轨,还有一条不比高速公路窄的一级公路。“要想富,先修路”,已成了中国尽人皆知的“致富经”。但什么事都不能极端化,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为什么塞车现象却越来越严重?城市效率真正提高了多少?我不禁想起过去的农村多用独轮车,乡间小路网络化,土地利用率极高。现在是高速公路网络化,其作用无须怀疑,但也不能不看到大量的土地,甚至像川西平原那种世界上最好的土地,正渐渐地被混凝土覆盖……进步也可以隐含着倒退,一阵风刮起来就不顾一切,这方面的教训我们经历的还少吗?城市建设也一样。
好吧,既然什么都大起来了,房子就更不能小,楼要又大又高,有些机关的办公楼有意建在高台阶上,高高在上,傲视群民,谁想从正面进入,不爬几十级台阶就甭想摸得着大门。人需要象征性的东西,单位大、权力大或者金钱多,似乎房子就得大。财大气粗,也要在建筑上体现出一种霸气,一争高下。有些单位甚至因建大楼而被拖垮,不然哪来那么多烂尾楼?在天津最繁华的南京路黄金地段就裸露着两座三十层灰污污的高楼框架,每次陪外地朋友在它跟前经过,无论我把天津说得再怎么好,人家也晃悠着脑袋心存疑虑。
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骨子里却从没有把城市当成自己的家,潜意识老觉得城市不是自己的。这或许跟我确实来自农村有关,于是就有意识地询问一些在本市出生的人,他们是不是理直气壮地认为城市是自己的?没想到他们的回答也都很迟疑:哪会有那样的感觉,城市这么大,这么杂,什么人都有,怎么可能认为是自己的?
这就怪了,外来人和土生土长的城里人都不觉得城市是自己的,那城市是谁的呢?
城市属于欲望。它集中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品质:激烈地竞争,疯狂地追逐,冒险的机会和偷懒的机会一样多,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可能性一样大。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阶层居住在城市里,可是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数字,目前全球有十亿赤贫人口,其中七点五亿是生活在居无适宜住所也无基本福利设施的城市地区。
你看看,“大”的东西暗影也多。任何“大”,也必有其“小”的一面。
城市现代病症状之三: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照抄照搬,千城一面。前不久,天津一位朋友乔迁新居,请我去温居,进门后感到非常熟悉,竟跟珠海我儿子的房子一模一样。这令我恍然大悟:原来中国的建筑设计是批量生产的,从南到北,无论城市大小,建筑物基本上是用标准件、复制品组装起来的。难怪现在的城市千篇一律,都像用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楼房差不多,街道差不多,广告招牌差不多,连那个惨白的麦穗灯都是一个型号。
像刚建市不久的阿尔山市,位于大兴安岭腹地,有着绝佳的自然环境,却建了一些在哪里都能看得到的俗楼,令人无比痛惜。“养在深闺人未识”,至少最宝贵的东西还保留着,保持着自然的清新、美妙、纯洁和质朴。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没有规划好就急于开发,如同把一个少女丢进了欢场,涂脂抹粉,忸怩作态,世面是见过了,可自身最大的优势、最宝贵的东西也丢掉了,而且再也找不回来了。还有一些著名的古城,也弄得面目模糊了,比如成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真被它的气韵迷住了。而现在再走在成都的大街上会产生身在天津或郑州的错觉……城市的特色在一个个地消失,全成了“拙劣的堆积物的拙劣复制品”。
历史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地方产生这样一个城市,是因为每一个城市都是不可替代的。差异即美,有差异才有丰富,每个城市的自然条件不同,界定的空间不同,城市理念和行为形象也不同。建筑构成了城市的视觉景观,建筑个性是城市精神最直观的表达,是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风格、时尚及技术条件在建筑上的反映。抛弃了这一切,完全不顾自己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天下建筑一大抄”,粗制滥造,俗不可耐,轻而易举地就抹杀了城市的个性。
而个性恰恰是城市的精气神,是主心骨,是一个城市的信心之源。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城市的个性,个性体现了本地人的意识和性格。但,城市建筑的个性,又必须是从生命内部放射出来的,是从灵魂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东西。或者说个性也是一种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成果,它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及价值取向。
给建筑艺术下任何定义,都必须从个性出发,否则就与艺术不符,跟创作无关。真正的建筑艺术是绝不重复,一切都独一无二。正因为建筑有个性,城市才有活力,会形成自己的氛围,使整个环境显得独一无二。去年在一个全国性的文化论坛上,一位广东学者嘲笑浦东的东方明珠是“上海的睾丸”。我倒认为这是对上海最好的恭维。世界上有些名头非常响亮的城市是得益于有个不一般的塔。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伦敦将塔和桥结合起来,东京和多伦多的塔也成了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而中国,各大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高塔,还不都是一根圆柱子支着一个球,毫无创见。你不能不承认上海的东方明珠塔不仅是全国最奇特的,也应该能排进世界名塔之列。
彼得·波特所说的,在宇宙的中心回响着的那个坚定神秘的音符“我”——就是个性。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建筑风格,不管外表多么张扬,骨子里也是失魂落魄的。没有个性、没有灵魂的建筑就是死建筑,塞满了死建筑的城市,表面上张狂,骨子里却有股子穷气,谁有钱谁就是大爷,想在哪儿建楼就在哪儿建,房地产开发商就是设计师,他们想盖个什么奶奶样的玩意儿谁也管不着……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欲望的膨胀导致了城市病态般的膨胀。
我前年去英国时听到伦敦市民在讨论伦佐·皮亚诺大厦该不该建,据说到现在还没有发给它建筑许可证。这是一座三百米高的尖形建筑物,建成后将给伦敦的天空中增加一个“漂亮的锥体”,成为又一座标志性建筑。但伦敦的天空不是属于政府或某个开发商的,它属于整个伦敦和伦敦市民。尽管大厦的开发商一再许诺,这座大厦“绝对符合环保要求,建成后将直接用泵从地下抽水,利用太阳能光板为楼内供暖,还要修建一些花园改善自然通风……”但不获得伦敦民意测验的赞同,就甭想动工。这就是对城市的尊重,有了尊重才会珍惜和保护,才会小心翼翼地规划和建设。
而造成现代城市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过热,商人们看重的是自己的利润,只顾在城市大桶掘金,至于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哪管得了那么多。当今社会各种人的各种欲望都想通过城市实现,城市怎么能不得病?于是规划和建筑上的城市病,又带来了城市人口剧增、就业困难、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热岛效应、交通拥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犯罪率上升……
既然是谈病论因,我可能就说得重了一些,甚或有危言耸听之处,这就请读者诸公自己掂量了。城市病也因城而异,因人而异,轻重各不相同,但意识到城市建设有毛病的人多起来了,这就有了治愈城市病的希望。唯愿别再重蹈覆辙,猛下虎狼药,掀起新一轮的大拆大迁热。 蒋子龙文集.10,难得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