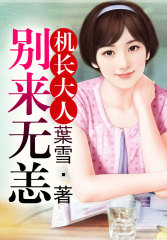§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文学
——《崔椿蕃小说集》序
出书难,几乎成了当今文学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为死去的作家出书更难。
近几年,相继有作家去世。据我所知,莫应丰去世后湖南文艺出版社立即出版了一本他的小说集,既是对死者的纪念,也是对生者的抚慰。路遥去世后,陕西人民出版社用最快的速度推出了他的四卷本文集……
这体现了一个地区的温暖,让人觉得文学还有情。湖南和陕西的文学界也因此受到全国文坛的羡慕和敬重。
在崔椿蕃去世两周年的时候,百花文艺出版社将出版他的小说集。这也是一桩义举,成为天津文坛的美谈。
两年前老崔刚离休,死亡对他是突然降临的。没有活到他该活的岁数,更没有活到他想活的年龄。然而他没有表现出惊慌和惧怕,平静地走了。
可是他的同事,他的亲人,他的朋友,却觉得不能让他这样走,应该让他留下点什么。否则对老崔,对还活着的他的同事和亲友,都是一种缺憾,一种遗恨。
他十几岁就来到长芦汉沽盐场当扒盐工,中国解放后被提拔当了干部,多年搞宣传和编辑出版铅印的《盐工报》。他执笔创作的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和三十多万字的盐场场史,都出版了精美的精装本,然而他署自己的名字发表的大量的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却从未结集出版过。
他是中国第一个以文艺形式反映盐工生活的作家。他喜欢盐滩和工友,热爱生活,在他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励、有了很大名气以后,也从未想过要离开盐场,要当专业作家。人品文品互为表里,质朴地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憬悟,写常情常态,不矫情做态。不追求大红大紫,不追风赶潮,也不妄自菲薄。始终满足于当个“业余作者”,不趋炎附势,宽厚正直,泊然处中——而人生最好的路正是正直,岁月更迭,风云轮回,他能安稳如铸,堂堂正正地走过来,言行皆碑。
所以人们喜欢他,敬重他,为他的突然谢世痛惜。要编一本他的作品集,想留住他,留住他的品格,留住他的精神,留住人们对他的怀念。
汉沽盐场的领导愿意玉成此事。他的家人甚至想过要自己拿钱出这本书。一些朋友东奔西走,不遗余力地促成这件事。出书不再是他的事,而是变成了他活着的亲友们的事——这个过程本身已经证明了他的价值。一些专业作家去世后也未带来这样的效应……
“良友想着你,九泉为天堂。”死亡没有阻断朋友情谊,没有抹杀他对文学所付出的心血,在当今这个商品社会尤为可贵。
崔椿蕃的作品无愧于他所处的那个文学时代。
人们可以对已经过去了的时代指指点点,却无法否认那个时代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事实。即便那个时代“用瓜菜代粮”,责任也不在作家和读者。有“瓜菜”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你可以说那个时代的文学是“下里巴人”,是已经过时的“工人文学”。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下里巴人”,当前也一样。“工人作者”没有必要为“工人文学”脸红,“工人文学”属大众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发挥过重要的影响,承担了文学应该承担的责任。一大批像崔椿蕃这样的“工人作者”,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文学。即便是当下的“新潮文学”或“新潮人物”,过多少年以后再来看,或者眼下就用外国人的眼光来看,还会有“新潮”的自信吗?有新就有旧,有生就有死,大家都有过时的一天。
所谓永恒的存在,也只是存在于文化宝库里,而不是存在于以后的社会上、文坛上。用否定大众来突出高雅,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是文坛的恶习。
许多业余作者,利用工作之余勤勤恳恳写了很多作品。当今世界什么出版物没有?
为什么业余作者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出版自己的书?有人正在筹备一个基金会,帮助老业余作者出书,显然是一桩功德。业余作者们不必都像老崔这样,等到作古以后再办这件事。
借《崔椿蕃小说集》问世的机会说了以上的话,也是对椿蕃兄的祭奠。
1993年8月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