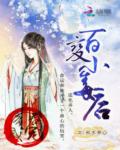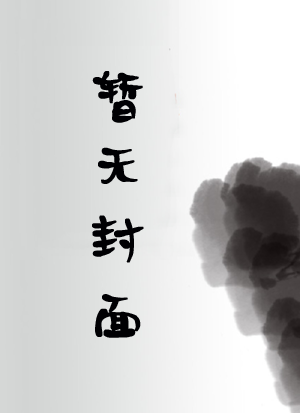§世界和人
——夜读《大林莽》
札记“坡上有个女人,正绕过寨子向森林走去”。
“这个人每年这时候都来的,种上四棵树就走啦。”
…………
我读完《大林莽》的最后一行,心里的波澜仍无法抑止。再把这部中篇小说的“尾声”重读一遍,仍不能长出一口气。而且出现了在我来说很少有的现象——眼睛发潮。我自知这不是悲,也不是怜,更不是怒,似乎也不是壮。那么是什么打动了我,使我如此激动不已?我要想一想……一部作品让人读后心里难以平静,而且要按自身的感受来领略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和情节,它靠的是什么?现实主义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人格的力量,绝妙的技法……不止这些,还有从字里行间放射出来的巨大的心理能量——这才是足以穿透心肺、征服感情的艺术“核放射”。孔捷生也许是动用了自己的全部(或者是最珍贵的)心理能量,升华为艺术创作,才使《大林莽》如此清新,如此壮美,充满奇想和幻觉,把读者紧紧缠住……
我关了台灯,屋内一团漆黑,窗外极静。眼前却时时飘动和变换着亚热带大森林的种种影像。忽而是千姿百态的热带植物群落,芬芳怡人的森林气味,闪着白光的雾岚,到处都倾泻下“百鸟无忧无虑的歌瀑”……忽而这远古洪荒的莽莽野林,被死神的黑色巨翅所笼罩,“空气中充斥臭氧的刺激气味,电光闪处,战栗的林木变得青蓝可怖”。巨雷炸响,地动山摇,乾坤崩溃。五个年轻的文明人,在大自然的蛮力面前,毫无自卫能力,像落入洪流中的蚂蚁……
得了,我知道今晚的睡眠非得卖给孔捷生不可了,这就是读他这部小说的代价。我披衣坐起,扭开台灯。一般情况下,我不敢轻易评论别人的作品。因为我知道每部小说都好像是一个梦,各人有各人的解释,谁也不要把自己的解释强加于人。但是今晚我非得把自己的读后感写出来不可,不必构思,信笔涂来。为了探索孔捷生在思考什么,也为了驱赶眼前这奇特冷峻的幻象……
应该说,《大林莽》的情节编排并无宏伟的规模,人物也很单纯:四男一女共五个知识青年(严格地讲还有一个自称是“坏蛋”的混进知青队伍的“大陆仔”),闯进原始森林勘察,准备主宰和荡平这莽莽热带雨林,根据“革命路线的需要”改种橡胶树。他们最终却未能毁掉森林,而是被森林毁灭了他们。只有那个女知青侥幸存活了下来。
多么简单的故事,却又多么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复杂的人生。读后让人觉得作者是站在人生的制高点上,裁判人生,裁判生活。
组成五人小分队,进军大森林,这行动本身就是荒谬的。在荒谬的年代所有荒谬的行动都是正常的、顺理成章的。如果不荒谬,倒是反常的。女指导员谢晴,是个从灵魂到肉体都包裹着“严实的外壳”的人物,她怀着崇高的信念——改造世界、造福于全人类,才率领自己的队伍杀进大林莽的。伟岸雄奇的邱霆,迷恋着谢晴身上的革命光圈,其实就是那“外壳”,却死看不上另外的三个男人。他一心想建立开天辟地功业,勇敢正直,无私无畏,是小分队里唯一革命到底不回头的硬汉子,是动乱年代里以正面形象出现的“阿Q”。他愈正经,就愈可笑;愈忠勇,就愈可悲。壮硕刁蛮的冼四海,是个鲁夫,有点江湖义气,专爱跟邱霆作对,还打过简和平。受压抑而牢骚郁勃的简和平,是作者精雕细刻的“理想人物”,能够用理性观察世界,从人的现实存在和生活的现实出发。他看不起所有的人,却又能谅解所有的人。至于“大陆仔”,是个“干尽了坏事”,赌输了钱逃避流氓的追杀,自造假证明,投奔到小分队想避难找出路的。
五个人,五个心眼儿,五条肠子,心不相通,隔阂重重,却硬要凑到一起去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孔捷生摆出这支队伍,就是向生活捅了一刀子——每个人在社会中的面目都不是真实的,没有自我。
他们一陷入森林就迷了路,前进无门,后退无路。饥饿、疾病、虫咬蚊叮、雷暴飓风的袭击、死亡,无穷无尽的灾难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他们吞咽着脏兮兮像一团烂泥般的蚂蚁蛋,嚼着看一眼都会呕吐的各种能有助于维持生命的东西,他们变成了“杂食性动物”。比起他们的生活来说,他们外形更像野兽:衣服被荆棘撕扯得只剩下几条布丝儿,粘在身上。身上长满鸡蛋大的脓疮,流着脓血,爬着臭蛆。指甲脱落,头发稀稀拉拉往下掉,脑袋肿得分不出眉眼……
大森林把人变成了兽,也许这外形更像兽的人,更接近真实的人。
小说借助大森林的威力把人撕开了!各样人的理想、信念、本能、欲望、超凡的一面和粗俗的一面,均暴露无遗。这就是生命!
我以为这是《大林莽》的一个重要收获,撕去假象到人类本性中去寻找人生的答案,探索人的本质。孔捷生通过象征手法和变形技巧,找到了自己的表现形式。他不仅一次次把人物推向绝境,充分表现心理和物理的对应现象。人生的无限空间在大林莽中却显得极其窄小。人生无涯,人生无常,借以表现人生从来是“在短暂中求永恒”、“不懈地蜕变更新”的过程。而且作者的目光直接渗入到人物的意识层。笔锋由人的表象进入人的意识深处。客观世界大林莽与人的对立,自然意识与人物的自我意识的对立,促成人与人的对立,灵魂之间的抗衡。作者从容不迫,步步紧逼地把各样人物心理上的不同层次(这五个人每个人都有一部灵魂的历史,而且层次分明,前后有致,实为难得),个性分裂,性格里隐秘的内在本质,都赤裸裸地揭示出来。这种解剖有时甚至达到残酷的地步,令人毛骨悚然。那恐怖绝望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
《大林莽》独特的风骨就在于它的高潮不是靠故事情节推上去的,而是靠对人的内容和质量的揭示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领读者登上了生活的制高点,鸟瞰人生的各种风光——这就是孔捷生运用成功的又一手法,把庄严的理想和严峻的现实交织在一起,从而表现人格的美。
如果作者只写人和森林的较量,那还有什么新意?小分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能否战胜自己,在残酷沉重的现实面前,获得心灵的解脱、人格的新生并升华到完美的程度。
被困在密匝匝黑苍苍的热带雨林里,呼救无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生死是一瞬间的事。面对死亡和分裂,小分队的首脑和灵魂谢晴,也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无依无靠,孤独可怕。抽象的概念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空洞的人生大道理也不顶用,难于用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控制小分队,她的全部理想和知识都不能解释眼前的生活现象。荒诞的处境,人对客观世界的无能为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人的本质,这本质真实得近于残酷。她从信仰的圣殿上跌进信仰破灭的深谷,摔碎了裹着她的“严实的外壳”。她开始从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内心感受出发,看待周围的一切,过去没有力量解释的社会现象突然清晰了。以前的生活中充满了假话,那虚假的信念却很有力量,挣脱不了,看来每个人也不一定真正能认识自己。她重新思索:衡量人的价值标准是什么?人的真正价值在哪里?什么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她要根据物质现实和直接经验,决定自己的行为。他们宣誓:“要活下去!”这和出发时的雄心壮志相辉映,是多么意味深长的一笔!
大森林净化了他们的灵魂,使良知回到人的基准线。从意念走向现实,又从现实走向意念。探索“灵与肉倏然分离”那一刻人物心里的奥秘。他们“在这杳无人迹的老林深山所经历的一切,实质上是很多人曾经历过或者将要经历的……”
作者打开了观察人的复杂性的大门,然后有意把生活现象、潜意识活动、人物行为打乱,搅在一起。再加上他笔下的大林莽本身就给人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现在、过去、未来交织在一起。空间、时间忽而封闭,让人窒息,忽而又跳动很大。现实与想象、真实与幻境、永生与死亡,交替出现,纠葛成一体(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不再枚举),读者自会理出头绪。我甚至觉得作者还留下了不少空白,尤其是小说的后半部分,让读者去思考、求解。
小说表现“文化大革命”年代的单调生活,却没有把人生简单化、贫乏化。意境深邃,笔力峭拔,写得骇世警俗,令人叫绝。这都表现了作者创作生命力的勃发。
冼四海死得糊涂、委屈。简和平死得明白。邱霆死得勇烈,他为自己的信仰全忠全节。大陆仔死得快乐、高尚,他背出谢晴,看到了生的希望,又跑回去为救简和平而死。人格是多么美,多么可爱。死得却是多么可惜,多么不值得!错误的远征,荒诞式的悲剧,唯其把愚蠢当作神圣,才更显出那个年代的生活是无秩序的,缺少理性的,好像是一堆偶然事件。尽管它表面上有铁板一块的思想,有班排连营等严密的组织形式,一到大林莽就暴露了它的荒诞。真是入木三分!一方面写出了产生悲剧的社会生活环境,一方面写出了人物思想性格中的悲剧因素。这一切都为了表现强烈的真实的人生。
尽管作者的艺术观念是现代的,写作手法也多用现代技巧,但决定这一切的是作者的生活观念。孔捷生的生活观念是严肃的、进取的、中国式的。他在《大林莽》中得出了与西方现代派的生活观念大相径庭的结论——人是善良的多,人与人之间是愿意相通的,也是能够相通和相容的。不论简和平还是邱霆,他们死前的幻觉是何等感人至深!在绝望中每个人谈自己的身世、希望、苦恼和追求,简直是趁活着为自己开追悼会!正是那次会才沟通了灵魂,使简、谢的爱情在灾难中成熟了。
有些喜欢用题材圈定作品和划分作家的同志,在呼吁知青题材的小说需要突破。往哪里突破?怎样突破?我以为“突破”年年有,而且不可能顺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去突破。前年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是突破。去年孔捷生的《大林莽》更是突破,而且是在表现人的社会历史内涵上的突破。这样的小说只用“知青题材”是不能概括其认识价值的,它近似所谓的“超题材小说”。表现知青生活的作品,如果在认识人类的总命运和探索具体的人生上,达不到新的高度,我不知还往哪里突破?
不管孔捷生算不算“被痛苦养大的一代作家”,无疑他是把人的心理、情感、追求、痛苦、渴望看作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他尽力追求一种完美的形式来表现这种痛苦——知青的痛苦、一代人的痛苦、历史的痛苦。因此才使《大林莽》蕴藏着新意和丰富的想象力,有一种精神和道德的魅力。《大林莽》之所以让人觉得富有哲理因素,原因也在于此。
小说的哲理性只有在与它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中才能表现出来。《大林莽》中的神秘色彩,作者调动各种应手的写作技巧强化艺术感受。从容地驾驭了人物和情节,自由地进入他笔下随便哪一个人物的内心,还可以把外部世界移置到这个人物的内心屏幕上。再加上作者的视角像大森林的色彩一样变化多端,有时从主观角度进入小说,有时从人性角度进去,有时从人物的心理角度,有时也从客观世界的角度……意境骤然宕开,想象大开大合,使整部小说斑斓多姿。
我和孔捷生在文学讲习所同过学,也喝过他的结婚喜酒,他的大部分作品我都读过。他在创作上似乎不是举重若轻的,不属于轻松愉快、多产多销的作家之列。但每年都扎扎实实地迈一大步,不后退,也没有滑过坡。这两年,从《南方的岸》、《普通女工》到《大林莽》,简直是“三级跳”。
孔捷生还有一点令我惊叹:他找到了自己人物活动的世界——大林莽。就像曹雪芹找到了荣、宁二府,施耐庵找到了水泊梁山,肖洛霍夫找到了顿河地区一样。文学的庄园不能没有自己的领地。
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是个封闭的社会。同时也是时代的交界处,人生的检验台,死亡的网口。把人物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就搞不成以自我为中心,任何思想都显得软弱无力,可笑和渺小。人的精神失去平衡,找不到生存的依据和意义。作者光靠传统的技法显然是施展不开,因而可以充分使用象征、梦幻、想象等现代手法。带领自己的人物尽情体验原始密林中神秘、恐怖、庄严和疯狂的种种感受,探索奇特、怪诞的人和物。也正因为是在这样一个壮阔的大森林里,才更便于打破人物形象的社会局限和心理局限,让读者想得更深更广。所以我才说它具有某种“超题材”的味道。
作者用浓墨重彩描绘了大林莽中各种各样的景物,有时甚至用主观意念去强化自然物象本身的多义性。保持这种自然现象的多义性和暧昧性,是为了达到真正的真实,衬托人物心理的真实。我读着作者那些关于大林莽时雨时晴、喜怒无常的描写,脑子里就产生过这样的联想:大林莽其实是变态的时代的复制品,是人类命运的象征,当时我们民族的命运就好像挂在大林莽的树梢儿上……
天早就亮了,连早饭也错过了,我也该走出《大林莽》了。奇怪,读完这部小说,我怎么有这么多话要说?
1985年1月13日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