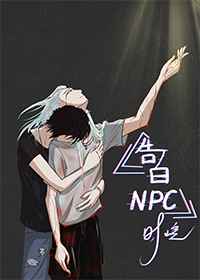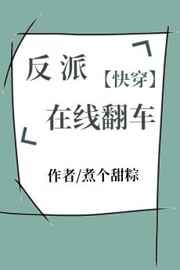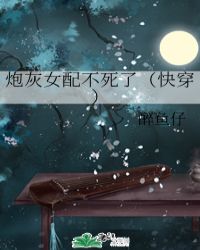§好一座白门楼
接到姜天民的系列小说稿《白门楼印象》,责任编辑很兴奋。二审、三审编辑也叫好,决定新年伊始在《天津文学》隆重推出。小说似乎又有了生气,气温开始回升。我感激他对《天津文学》的鼎力相助,更祝贺他的“起死回生”——是身体和精神上的,也是文学创作上的。
对《白门楼印象》最精彩的解释是作者本人给编辑的信,上期已经发表。姜天民把文学搞得更神秘了!
他大病不死,却因此“聆听了死亡的教诲”,对人世的一切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深切地“体验和感受了生命的意味和生命的痛苦”。小说写得新鲜而精致,不是那种玩死亡、玩痛苦、玩深沉、玩永恒。一个到死的王国里转了一遭又死而复转,人生的经验和智慧突然变得深刻而丰富了,这不足为奇。令人惊奇的是他这么快就“重生再造”出完全属于自己的全新的文学门楼。他充满自信,关于这“门楼”的构想是大气象大规模的。他似乎找到了自己永恒的主题。
作为这大主题前奏的一组短篇写得深刻有才气,富于一种强烈的生命感和独创性。有现实的真实也有非现实的真实。凡属于自己对生命的独特感受,不论多么稀奇,多么怪诞,都是真实的。表现现实的文学,多注意人和环境,往往会忽视人的生命的“本真”。姜天民的笔尖却集中表现生命的困惑,生命残酷,生命与环境的对立,生命的存在方式的荒唐。每个短篇都想雕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用荒天下之大唐的命运体现生命的苦难和真味。他的小说有了一种气魄,是艺术的,也是人格的。
他笔下的“本土文化”和“生命行为”,是一团闪烁的光亮,一片沉重的色彩,一群晃动的魂灵,一种苍凉的声音。确是神秘而又真实的“现代神话”。活着就没有脱离生命,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和感受生命。姜天民一下子拥有了这种奇特的感觉,仿佛真是死过一回给了他太多的启迪和自由,心理世界和外部世界全变了,对生命的感觉有了自由,对社会生活的揭示有了深刻的自由,有了鲜活的经验,思想抛弃了贫乏,创造性的想象自由了。
生命本身太繁复太奇怪了。姜天民发现了自己丰富的心理资源,能够自由地开掘自我无穷无尽的潜能。他的主要工具有两件:意念和语言。
我宁愿把他这一组短篇叫做“新意念小说”,或者“感觉派小说”。他写点子,每篇都有一个绝妙的令人玩味无穷的好点子。德高望重的教书匠终生只教出了两种人,强盗和奴才。臭老九的瓷眼珠能洞穿人间一切因而为世人所不容。权高位重的土皇上五毒攻心,做气功竟使周围的土地寸草不生。以及土地爷只能一眼睁一眼闭,等等。这样一概括便没有意思,索然无味了。姜天民《白门楼印象》的力度在于超越了作者的意念和故事。故事超越了意念,作者要故事却又不刻意追求故事的曲折惊奇,只是单纯地直入深境。小说里的每个生命及灵魂都是他制造的,按照他的认识制造。小说太精致了,精致得无可挑剔。也不是这精致限制了它,有时意念的精巧代替了感觉的深刻。
所以我不完全相信是病魔帮助他跨过了看来是平常无逾越的疆界。文学需要魔鬼帮忙,假如没有神助的话。死亡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权利,死两回却是少有的幸运。姜天民有优等的智慧和意念,把这幸运作用于文学,让自己进入一个创造生命的万有之链。要成功必须走进自己的世界,并成为自己艺术心灵的主宰。
应该说《白门楼印象》吸引了读者的不是它的故事和人物,而是姜天民的语言。机智奇诡的语言载负着独特的个人感受。他想创造“一种全新的语言机制”,以带动自己的“小说艺术质的飞跃”,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有些美妙的长句子是精辟的哲学绕口令,妙语如珠,常出意外,完全靠聪明的语言把读者引进他感觉的迷宫。就这样,精瘦、坚韧的天民兄,凭他新近推出的小说成了当代“造句运动”的先锋人物之一。“造句运动”这个口号是我提出的,绝无贬意。当代文学前进最快的就是语言,不管怎样评价这几年的文学,语言是不会再退回去了。不会造句子,或者造不出好句子,写小说就难了。所以我才把它称之为“造句运动”。
然而,有“永恒的主题”却没有一种永恒的技巧。天民找到的完全属于自己的感觉模式、语言模式、结构模式,能不能营造宏伟的“白门楼”系列呢?
愿天民多加珍重。
1995年冬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