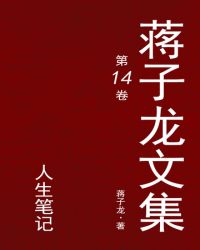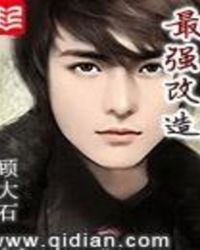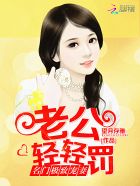§致《读书》杂志编辑部
——兼答鲁和光同志
《读书》杂志的编辑同志:
谢谢你们寄来的杂志和打印的信。我在未见到贵刊前,已经从《人民日报》社编的《文摘报》和上海的《报刊文摘》上,看到了鲁和光同志文章的摘要,许多同志也向我谈起这件事,并接到一些不同意鲁文观点的读者来信和来稿。现选了两篇寄上,我想贵刊应该有勇气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
鲁和光同志说:他接触过许多工厂的厂长,他们几乎都知道乔光朴,有些厂长甚至把这类文艺作品当做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在研究,但“管理工作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简直无法工作下去”。
把小说“当作企业管理的教科书”,把“乔厂长的管理方法当作样板”,这合适吗?看了《陈奂生上城》就去做小买卖,看了《阿Q正传》就去学“精神胜利法”,看了《水浒传》就学李逵抡起板斧将头砍去……那不乱套了吗!如此效法当然会在生活中碰壁,碰壁后便大骂文学,以此否定小说,这是很痛快的。因为对文学发怒,比去改变生活容易多了。
那么,鲁和光同志也许会问:你塑造的正面人物不是叫人家学习的吗?我说:你要学习,咱欢迎。但要学精神,学做人的风格,做人的力量。如果你只是喜欢看一点小说,并不向其中的某一个人物学习,作家决不怪你。生活中,说某人是诸葛亮,指他足智多谋,并不是说他也会装神弄鬼借东风;说某个小伙子像武松,也不是指他真去景阳冈打过虎。
鲁文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在他的周围似乎掀起了一个“学习乔光朴运动”。这使我甚感惶恐。作家力争写出活人,而活人不等于完人。活人身上有好也有坏,有长也有短,倘你只学他的缺点,叫作家怎么办?乔光朴不是雷锋。乔光朴的父母是生活,他的血肉是笔和墨。鲁和光同志所“接触过”的“许多工厂的厂长”,开展学乔运动的结果“并不理想”,最后甚至“无法工作下去”了,这不能责怪乔光朴。如果追究法律责任的话,鲁和光同志倒应该对小说的作者起诉。
我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不仅“接触过许多工厂的厂长”,还接触了一些更高一点的工业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他们已记不得乔厂长具体干了些什么事情,但喜欢把能打开局面、敢作敢为的干部统称之为乔厂长式的人物。其实,这些人物比“乔厂长”还要乔厂长!报纸上报道他们的事迹时,用的标题是:《生活中的乔厂长》、《欢迎乔厂长来上任》等。但他们要比我笔下的乔厂长高明多了,他们并不照搬乔光朴的那一套。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些人到后来“无法工作下去”了,岂止是“效果并不理想”,甚至被调走,被免职或明升暗降,那是另外的问题,责任并不全在他们本身。更不能把这种责任全加到乔厂长头上。即使鲁和光同志从西方借来了“Y理论”和“Z理论”的先进武器,就保证能奏效吗?
近年来,国内介绍行为科学的文章很多,这是一件好事。鲁文用主要篇幅重复这些内容,也无可厚非,借鉴一种新东西,反复宣传也有必要。为什么非要拿文学作品开刀?文学好像成了一个破鼓乱人捶!乔光朴从一出世就十分倒霉,屡遭磨难,人家要介绍行为科学,一开头也先把他骂几句,岂不冤枉!这到哪儿去说理?鲁和光同志趸来的理论当然比乔厂长那一套先进多了,也许能包治百病,并且“行于长久”。可是怎么能要求作家也按他的理论写作?用国外管理理论审判纯属文学形象的乔光朴,这“行为”符合“科学”吗?
鲁文把乔厂长的办法概括为“靠的是规章制度,办法是惩罚”,然后加以批判。自己立靶,自己射击,是最便当的了,保证百发百中。鲁和光同志还不喜欢乔光朴的性格,说他“表情严肃,很少对工人露出笑容”。读者有权根据自己的喜恶取舍小说中的人物,但不能把自己的喜恶强加给小说中的人物及其作者,何况还是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乔厂长上任记》不是成熟之作,正像乔光朴这个人物一样,小说本身也有不少缺点和失误。但不抱偏见的读者,是不会得出鲁和光同志的那种印象。纵然乔光朴“表情严肃,很少对工人露出笑容”,又犯了哪家的王法?难道非要老乔温柔可爱,见人三分笑,就符合“行为科学”吗?
鲁文还为文学创作指出了方向:“吸取行为科学的科学原理”,“正确表现企业管理现代化题材”,文学才能“迈出新的步子”。
要想“迈出”这种新“步子”,说难也真难,在作家对行为科学的理论还没有达到像鲁和光同志那样精通的地步之前,是很难动笔的。说容易也很容易,今天外国人宣扬“Z理论”,作家就叫人物口口声声不离“Z理论”。到明天外国人又想出了“K理论”,作家又叫人物按“K理论”行事,把文学变成洋杂碎。外国人发明一种新玩意儿,我们就拿过来搬到作品里去,图解一番,赶一番新浪潮,时髦倒也时髦。这样的作品也未必就能“行于长久”,只怕连“行于一时”也办不到。
怎样看待文学作品,这本是一般读者都知道的常识。可是,鲁文在一个指导人们怎样“读书”、学术性很浓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之后,就我所知道的全国两家“文摘报”都很快发表了鲁文的摘要。记得去年《上海文学》也发表了一篇文章,把三篇小说中的厂长的管理办法拿来做比较,评定优劣。可见这不单是如何看待一个乔厂长的问题,而是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的问题。以前有人同小说中的人物对号,已经使作家哭笑不得,如今又有人“按图索骥”,到小说中寻找改革方案,把小说中的人物当作企业管理的样板加以效法,岂不悲哉!
文学不能倒退,不能退到“方案文学”、“事件文学”、“跟中心文学”的旧路上去。文学要表现当前的社会生活,就不可能回避方兴未艾的经济改革。但作家不可自作聪明,给经济学家出主意、提方案,而且认为自己的方案是“最佳方案”。这样容易使一些热心改革而一时又没有找到好办法的人产生误解,把文艺作品中的方案当作“样板”和“教科书”,拿去实行,一旦碰壁,回过头来抱怨作家。作家徒有热心,却给人帮倒忙。文学要表现现实生活,并不等于就紧跟某种事件或描写具体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作家的着眼点是探索现代人的心灵的奥秘。表现人物不能没有细节,细节来自现实生活。也请读者诸公不要把作家用来表现人物的细节,当作改革的方案加以模仿。
当然,作家也不必在小说里玩花活,将经济学、哲学、心理学和种种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名词像开药方一样成串地塞进自己的作品,赶国际浪潮,追洋时髦。变态、怪异,不等于跟上了“时代潮流”。创作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劳动。
读了你们的信,信笔写下这许多,请批评。
此致
敬礼
蒋子龙
1983年1月30日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