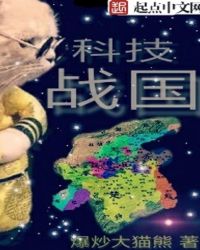§秦岭访谈
秦岭:我注意到,最近,您的长篇力作《农民帝国》因为涉及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民的现实命运再次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像当年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主的“开拓者家族”那样,似有波及并燎原到社会学界的态势。事实再次证明,您是一位有着鲜明唯物史观、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注的作家。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工业题材还是农村题材,您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一种现实忧患感和对现实改革的迫切渴望。作为文人,这种强烈的悲悯情怀和深重忧思是个性使然呢,还是源于心灵与现实社会的激烈碰撞之故?
蒋子龙:每个作家跟文学结缘的过程都不同,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及命运,决定了文学观。我读书时喜欢历史、数学,是学校历史组的成员。但走上写作的路,是被现实所捆绑,甚至可以说是被胁迫。那缘自一九五七年,因同情一位教古典文学的老师,在全校被批判了几个月,最后竟背着处分毕业。就这样文学作为一场灾难进入我的人生轨迹。而现实的灾难又促使我跟文学结缘。这样的文学之路,以后想摆脱现实都难了。再加上我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在社会的“五花三层”里沉浮穿行,多少知道人间是怎么回事,大半生走过来,全部感觉都用在关注现实上,而现实的重击也更容易触动我文学的兴奋点。局限是在所难免,但也成全了我的写作。我自觉正是这样的思想和文风,才使文字没有钝化和圆滑。
秦岭:在我看来,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创作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拜年》、《赤橙黄绿青蓝紫》、《阴差阳错》等系列作品,有的为新时期工业改革题材提供了全新的改革者形象,有的提出了当时经济体制下干部制度改革的问题,有的关注工厂青年的思想和生活,有的笔锋陡转,直指改革中的困境,由此可见,您始终在对当时的中国工业改革进行解剖式的、跟踪式的、梳理式的纵深思考,并凭借诸多“领先”元素构筑了后来同类作家作品难以超越的模式。二十年来,中国工业改革今非昔比,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派生出了二十年前从来没有过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作为工业题材的领军人物和改革文学中最有影响的艺术家,您是否仍然在进行纵深的解剖、跟踪和梳理,是否仍然对这一领域充满创作的激情和思想准备?
蒋子龙:当今世界简直无法预测无法规划,人们老爱说“多元”,其实多元就是无元。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作家总要有点坚持、有点操守和立场,才能够定得住魂儿、守得住心。守住了自己的心也才能观察,有观察才会有自己的感受,创作至少会有真诚,不至流于空泛和浮躁。注视着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还会逼迫作家去读好多东西,研究许多现象,文字也会充实。不管是否真的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作家存在的价值,至少应该是追求有意义的写作。特别是赶上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期,现实催赶着你不多看不行,不多想不行,灵魂得一次又一次地蜕皮。就像蛇一样,不蜕皮长不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当代文学乃至每个人的生活都跟这场改革绑在了一起,波澜起伏,丰富而充实。但,像你所说的,“进行纵深的解剖、跟踪和梳理”,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我是做不到的。比如《农民帝国》这部书,断断续续、写写停停地磨蹭了很长时间,但不是“十年磨一剑”,是“磨洋工”。准确地说是放下、拾起,再放下、再拾起。虽然很看重这个构思,也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该写这部小说,可开篇后常常感到驾驭不了它。主要是对现代农民的命运把握不准,不能完全参透他们灵魂的脉络,以及现代农村变革的得失……于是便几次知难而退。可丢掉以后心又有所不甘,过一段时间手又痒痒了,便再拾起来。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一个道理,对农民的命运和近三十年农村生活的变革,参不透就不参,把握不了就根本不去把握。我只写小说,能让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就行。于是一鼓作气终于把小说完成了。
秦岭:我在甘肃天水老家上中学的时候,就拜读过您的第一部长篇《蛇神》,那是我拜读了您大部分工业题材小说以后的一次十分惊讶的阅读,这部小说使我进行了一种全新的与改革无关的精神遨游。重情崇美的主人公邵南孙对花露婵的至爱至情在经历了“文革”后,成为融善恶美丑于一身的人物,其人性的裂变和性格的多元使所有的情节都变得扑朔迷离,异彩纷呈,催发了我们对您此类创作的更多期待,可惜在后来的跟踪阅读中,您似乎在这片由自己开发的自留地上消失了,期待您解开这个谜。也许您认为根本算不上什么谜,但事实上,我们再也没有在您的其他作品中读到类似于《蛇神》的另类表达。
蒋子龙: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人的兴趣多种多样,文学的感觉也多种多样,写作的动因也各有不同。有的是思想被触动而萌发写作欲望;有的是被人物或故事所感染;有的是出于一种责任或公共意识……《蛇神》则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我小的时候痴迷于戏曲,堂嫂是沧州京剧团的头牌须生,一有机会我就跟着剧团到处跑。久而久之便装了一肚子戏内戏外以及演员的故事。加上我在农村长大,喜欢乡野,性格中有一种天生的野趣,继《蛇神》之后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长发男儿》。当时若不是工业题材强拉硬拽,我很有可能就沿着《蛇神》的兴趣写下去了……那现在我的小说家族,又将是别一番景象。你把《蛇神》比喻成我的文学“自留地”,让我觉得有趣。今后我有条件可以更多地顺从自己的兴趣,或许会更加勤奋地耕种自己的这块自得其乐的“自留地”。
秦岭:我在德国的洪堡大学学习考察时,有位汉学家告诉我,中国的新时期作家由于思想的局限和人文意识的淡薄,最容易受到题材的局限。但是喜欢您作品的读者会发现,“改革文学”的花环没有笼罩住你,笼罩的恰恰是读者的判断,因为您涉猎的题材十分宽泛,《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农民帝国》等小说的表达直抵城市、农村、知识分子、商界、官场生活的精神纵深地带。您的十多部随笔集,如果不是在人世间的开阔处览胜,就是在隐秘处探幽,甚至多见对天文地理、神灵鬼蜮的感悟,文笔恣意处,乱花必迷眼,几乎看不出有什么题材的限制。除了阅读、阅历和悟性,还与什么有关呢?
蒋子龙:现实生活会按题材划分吗?普通人的命运会被题材框住吗?我从来就对“改革文学”之类的命题不以为然,在字面上就不大通顺。是“改革文学”?文学又如何“改革”?还是反映“改革”的文学?我当年写“乔厂长”时,脑子里还没有多少关于“改革”的意识。以题材划分文学,甚或区分作家,恐怕是中国文坛独有的特色。我一向都不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会被题材所局限。但也大可不必刻意地为“突破”而突破,有一条恐怕是所有作家都不能违背的,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写自己熟悉的,包括通过资料间接熟悉的。学者有学者的特长,杂家有杂家的优势。我很看重“识”。古人讲知识分子的智慧和修为体现在三个方面:“才、学、识。”而“识”才是灵魂。没有“识见”,即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难以发挥,不知该怎样发挥。诸葛亮未出隆中,便断定将来必定是三分天下。于是他为刘备制定的奋斗目标就是“三分天下”。这就是“识”。
秦岭:一九九六年我刚从甘肃调到天津的时候,厚重的行囊中就有您的随笔集《我是蒋子龙》,不仅因为少年以来的文学情结绵伸到了津沽大地,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一段话不得不使我负重赴津,此话曰:“小说无疑是作者更深刻、更丰富、更高水平的自白。”自白很容易让人想到思想、灵魂的呈现和再现,想到作者本身和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某种勾连和关系。后来在我们作家签约仪式、颁奖大会上频频与您接触,似也发现您卓然、生猛的性格与您笔下的某些人物有着某种交叉点。您觉得,至少现在,您的那部作品是否更好地体现了您的“自白”?
蒋子龙:我以为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说是作家的一份自白,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他完整的自白。比如我的诸多随笔杂感,所袒露的思想,就跟填写调查表一样直白。而性格、情感,则在小说里表现得更为丰富曲折。但生命不断发展,人在每个阶段的感悟也不一样,他的“自白”也必不完全相同。一九七六年我最真实的“自白”是《机电局长的一天》,而眼下最能代表我的自然是《农民帝国》。
秦岭:作为从西部农村庄稼地里走出的山里娃,我无时不在密切关注着中国农村社会变革对农民精神层面带来的变化,并野心勃勃地试图把这块蛋糕做成秦岭式的模样。您的《农民帝国》给了我新的启示和反思,它与您八十年代另一农村题材名篇《燕赵悲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原本善良、勤劳的郭存先暴富以后,却无法抑制自身欲望在权力和财富中的无限膨胀,终成“农民帝国”中的“帝王”,直至彻底毁灭。这似乎是农民的宿命,似乎又不完全是,那么到底是什么?我发现我遭遇了思想的局限。我想,您要表达的肯定不光是金钱、欲望、权力对人性的冲击,其深刻性至少可以追溯到对国民性、民族文化、民族社会心理的追问和思考上来。您十四岁就离开故乡沧州,在浮华的津门待了五十多年,而《农民帝国》所表现的时代,恰恰是您在城市生活的阶段。您是否怀疑过小说与当代农村现实本相、本色切合的程度和精度?
蒋子龙:你真的认为现代城市与农村现实在“本色、本相”上有根本的或者是天大的差异吗?我不这么看。我认为从文学意义上说,目前中国没有城市,只有农村。所谓城市不过是个大村子。前两天媒体公开报道,某大城市里一个只有九十个人的单位,却在一座二十层高的豪华大楼里办公,平均四五个人享用一层,吃饭的睡觉的打牌的玩球的喝酒聊天的地方一应俱全……当下有些钱多的人和单位的这种“烧包”,是不是“很农民”?所以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被邓小平称做是“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三十年之后又回到了农村,农民像以往一样又成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人们该怎样估价这种情势?农村在害城市病,城市在害农村病。没有比金钱更能体现商品社会的“本色和本相”了。现代人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农民活不下去会出事,钱太多如果压不住钱,也会被钱烧得难受。当今世界不是钱很多、大富翁也很多吗?于是钱就在闹事,金融居然也形成大的“风暴”,而且比自然界的大风暴对现代人类的摧毁力更大。“农民帝国”确实不只在郭家店,并不是只有农村才有“土皇上”,城里有些很“洋”的人,甚至是留洋回来的人,也有这种情结。不信看看那些被曝光的贪官,他们中一些人的言行活脱脱就是“土皇上”。身份不是农民,骨子里比农民更农民,而且瞧不起农民的人,更容易闹出“帝国”的悲剧。
秦岭:您在随笔中多次谈到您的故乡河北沧县,并有诸如“我常常身不由己地躲进去,如果能不出来我愿以牺牲现有的一切为代价”等等令人扼腕的故乡情结。显然,古老厚重的燕赵大地给了您乡村叙事乃至洞悉世事的更多理由。就燕赵和津沽两种地域,您觉得哪种文化对您文学观的影响大一些?
蒋子龙:我的文学气脉中的理性、态势,可能得益于我所在的工厂。而性格和情感,或许更多地接受了家乡的营养。总之,“燕赵和津沽”缺了哪一块,我都不会是现在的我。至于哪个影响大一些,哪个影响小一些,很难说清,也没有必要说清。燕赵文化给了我根脉,津沽的工厂生活浇灌了我的文学小树开花结果。
秦岭:您不光是作家,还是体制内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担当、责任和义务必然驱使您对当代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前途进行思考。巨大的社会变革、变奏不仅能够成全崭新而广博的思想,更为经典文学作品的萌发乃至成长酿就了丰厚肥沃的土壤。当前中国社会的变革进入一个纷繁复杂、充满挑战的发展与阵痛相互交替的时代,但是,时代并没有呼唤出多少不负于这个时代的作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蒋子龙:我不知道这两者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一个纷繁复杂、充满挑战的发展与阵痛相互交替的时代”,就一定要出现“不负于这个时代的作品”吗?我倒觉得现在的文学已经够“纷繁复杂”和“充满挑战和阵痛”了。这样一个很不规范的商品社会,跟这样一个人人都可以指责的文坛现状,不是很相称吗?如你所说,文学还有“体制”内外之分,能干到这个份上就不错了。我相信一个事实,一个作家能够在社会上立足,就一定有他存在的道理。现在还有这么多人有兴趣谈论文学,而且也确有可谈论的东西,就说明当代文学还是有生气、有希望的。如果真像有人说的那样文学已经死了,谁愿意搭理它?事实似乎正相反,当今文坛活跃得很、热闹得很,有国内对骂,有“粗口事件”,还有国际间的对骂,诸如“垃圾论”等。于是乎当今文坛出现了一个怪现状:并没有因骂声多、骂声高而冷清。相反,被骂走的人微乎其微,不断进来的人很多,包括“体制外”的也申请进到“体制内”来。文坛越骂越热闹,越骂越拥挤。文学成了一碗肉,五花三层,肥瘦全有。以前有俗语说“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现在是端着碗边吃肉边骂娘。这也看出,当今文学有一种散漫的强大。松拉呱唧,老说“被边缘化了”,可谁要真想“消化掉”它,却并不那么容易。
2009年7月 蒋子龙文集.14,人生笔记